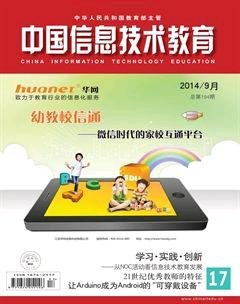国际视域下的STEM众筹式学习行动初探
刘党生
主持人寄语:从本期开始,我们将抛砖引玉,连载来自2015中小学STEM教育论坛筹委会的长文:《国际视域下的STEM众筹式学习行动初探》,并热忱欢迎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这场讨论中来,期待社会各界对STEM的中国特色实践建言献策,乃至实验探索。我们的初衷只有一条,让STEM成为连接学子成长和教育进步的阶梯。
还在今年四月份的常州会议期间,我们就已经在酝酿下一届的主题,经过论证,一致确认以“STEM+”作为我们对STEM结合中国国情的一种诠释;“STEM+”意在基于STEM的基本定义,结合国情、区情、校情和学情的不同,融合进多元的相关特色元素,使得STEM得以嫁接更广泛的资源形态,形成对课改、教改的快速植入。
会后,我们透过各种渠道向外界披露了这一决定,由此引发了社会各方面的更多思考和响应;也使得不少热心人士希望我们给出原创的诠释版本“以正视听”。我们认为,提前启动对中国特色的STEM教育讨论,实际上是倡导对STEM成长生态的救赎,对STEM教育理念的重构,对STEM现代办学的众筹,对STEM未来学习的孵化,对STEM国际趋势的同步……最后才有可能营造出对“STEM+”学习系统的召唤。
● STEM成长生态的救赎
在论证“STEM+”这样一个概念时,我们之所以引用“救赎”(Redemption)一词,主要有四点考量。
(1)对STEM本源的某种回归。2007年美国公布了“美国竞争力行动”America COMPETES Act of 2007,明确指出,美国如果在今后的经济领域竞争不过其他对手,应该归咎于今天对科学、技术、工程学的忽视和这一领域的劳动力发展的投入不足。因此,将奥巴马政府推动的STEM教育加以落实的,是由美国国家自然基金提出的“STEM field”即STEM领域,它不仅重构了对科学分类的新的认识,更主要的是把STEM行动计划,演绎成培养专业—复合型人才的推进抓手。在实施过程中,采用了自上而下的推进模式,即首先在高校系统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领域全面落实STEM战略,而后再逐渐渗透到K12层面。期望通过课程的再开发,引入各种显性、或潜在的社会资源用于课程设计之中,并最终落实在学生的学习能力拓展上。
(2)对STEM战略模式的某种清偿。大陆在议论STEM之时,喜欢将其拆分成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实在是对STEM的一种狭隘和极端肤浅的理解。
事实上,“S+T+E+M”仅仅是一种组合,并不意味着一种规范。STEM 课程的培养目标首先凸显出对科学素养(Scientific literacy)、技术素养(Technological literacy)、工程素养(Engineering literacy)和数学素养(Mathematical literacy)等方面的高度契合。
我们注意到,在STEM现世不久,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学者 Yakman就首次提出STEAM(A指艺术。韩国学者金镇洙指出A狭义上是指美术、音乐等学科,广义上包括美术、 音乐、社会、语言等人文语言艺术)。因此,我们现在提出“STEM+”也就顺理成章了。
另外,STEM是一个开源、开放的学习系统。尤其是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可供驾驭和把控的点位,远远超越了课堂、讲台的束缚,教育的形态变异和学习生态改良,为STEM的实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可能。
(3)对STEM理念核心的某种履行。尽管STEM从提出到目前得到世界八十多个国家的响应,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然而,其国家目标的阐释也呈现出多样性的侧重。例如,在澳大利亚,总的目标是应对当前和今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为学生在未来的职业和生活其他方面提供最大灵活性和适应性的技能,包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技能、信息处理和运算(computing)技能对科学和技术在社会中作用的理解,同时发展科学和技术技能,理解和关注全球环境的平衡发展,在道德、伦理和社会公正事务中做出判断的能力。而瑞典的技术教育课程,学生被寄予期望获得基本的有关技术任务的知识、历史视角的知识和反思技术问题解决方案的知识和技术(工艺)能力;还需要发展分析和评价社会、工艺和自然背景下人类团队活动之间关系的能力。
并且,STEM的重点解读也各有不同。由于科学的普及,以及事实上的科学前置模式对今天教育的全面主导,所以,STEM强调的不再是科学本身,而更注重科学的演绎方式和知识的应用范式;用我们熟悉的语境来强调,是一种基于素养的教与学的全面重构。
最后,STEM的课堂需求,为整合相关学科教学,提供了可能、可行的融合契机。这里,还是基于K12的基础教育层面为例,就有了所谓辅助学科、小学科合成为大教研环境的多种选择。T-bear理论,即基于工程、艺术和研究的技术学习理论就是其中重要的改革支撑。它揭示了多种课程设计思路,包括基于艺术的视角、基于工程的视角、基于研究的视角等面向问题性、路径的多重选择性、目标分层性等特点。强调将在技术的通识教育阶段,向学生呈现丰富全面的技术应用环境和解决问题的技术路径帮助;当进入提高教育阶段(类似于现在课程中存在的“选修模块”)时,从学生不同的个性需求出发,透过项目探究(研究)的渠道,达到在一个领域中融会贯通各种技术的水平。
(4)对STEM现行践行的某种纠偏。这包括片面强调现有学科的套用和对接。比如,以信息技术学科、通用技术学科为单一的动员目标。再如,过于倚重所谓的创客模式;创客现象,原本就是一种基于成年人的兴趣聚会,是缘于某种技术创新的同类交流,是一种重在技能达成的作品创造。但这一切,毕竟与教育的界定和外延有着较大的差异性,缺少教育的核心内涵。尤其是对于系统工程思维训练而言,这种创客文化尤其显得单薄和功利。
将STEM与杜威、孟禄、克伯屈、陶行知理论的简单等同,属于典型的“搭车”践行。杜威思想代表了资产阶级初期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和现在的探究式科学教育理念有本质上的不同。而行知先生所强调的“做”,指的是生活社会实践,强调在社会实践中学习,而STEM的“做”,是在动手做的科学探究同时,更强调学习对知识的自我验证、对能力的自我突破和对生存状态的自我创新。
还有一种践行,也存在先天的不足。那就是照搬“做中学”的经验,亦或是跳不出“做中学”的既有模式。“做中学”项目最大的特点是实现了从科普到科教的转型;只不过,这种转型还远没有凸显出把STEM提升到教育战略高度的重大意义。
STS(科学、技术与社会)影响也有待矫正。虽然,STS教育项目,突出了个人发展、社会发展与文化的目标;在内容与实操领域也更兼顾到综合性的特点,然而,其立意还是偏重于“科学素养”,也还是一种基于课程的知识解构。 (未完,待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