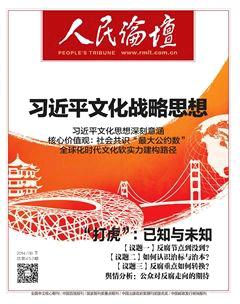迁移(外三首)
我几乎爱上了这个地址,
但我知道,
痛苦如此精确,
裁剪出那么多疲惫的岛屿。
路边的旅馆教会你沉默,
就像一滴落入裂缝的水。
无尽的漂流,
每一个地址都偏移燕子的到访。
那些树,多么奇异,
生长在秋冬的空气里,
在同一个地方领受回去的路。
一个囚禁于生活的人
被遣送到了希望的边缘,
依然试图醒来,
在星期一的下午,
在一条陌生的路上,
受雇于残缺的影子,
看见了另一条街在等待,
“难道你不该在那里?”
炎症
我离开嘈杂的大门,
会遭遇什么?
疾病入侵喉咙,
像闪电撕裂了谎言,
沉默开始了,我听见别人在说话。
其实,看不见什么面容,
人如此盲目,
假如,目光从不凝视缺席的事物。
工人们身穿黄色工作服,
在教堂前,切割着一株冷杉,
用电锯摧毁了一个约定。
只在一夜之间,
无处不在的黑暗,像树干一样被拆开,
错乱地放置在一起。
我的喉咙,在疼痛的时候,
突然走到了人们的背后,
听见均匀的呼吸
在数着阳光。
滞留者素描
飘蓬忽经旬,今此又留滞。
——余怀
一
在雾霾中,他走过一片街区,
国定支路像一个忍受着沉默的岛屿,
菜场的叫卖声加速了他的漂移。
散步犹如一场收集误解的旅行,
他醒来,脚上踢着
疑惑的落叶,在歧义中徘徊。
初冬的树叶已被装载,而骄傲
使垃圾车失去了平衡,
他一边走一边低语:“是我。”
这两个字消失于汽车的鸣声中。
他走入暮霭深处,一阵刺痛
找到了他,寒冷在加重。
二
接受一场失败。窗子关闭着,
提防着浑浊的寒冷,
但是无法抵挡屋内逐渐增加的黑暗。
通过距离,他几乎不能认出自己,
然而在行人的脸上,他看见
无从兑现的乡愁。“这就是我。”
一个偶然的自我,在这条路上
花掉唯一的十分钟,在思考的
片刻,云朵已越过这片街区。
他回到这里,每一次呼吸
与另一些生命分享着同一个节奏,
隔街的遥望减轻了他内心的恐惧。
失踪者素描
一
随着寒冷,他漫游到了这里,
他试图完成生活的训练,每天注视
无叶的树。突然间,他忘记了
来时的路程,与寂静住在一起。
他不知道,是谁把他派遣到了这里,
人们经历着不幸,竟然如此专注。
逃离是不可能的,勇气也还不够,
花了那么多年,他终于爱上生活的丑陋。
房间里的沉默,已无法应付警醒的白昼,
空气中充满力量。地平线在远处守候。
那永远的休憩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
逐渐地,他放松了肌肉,等待命运的注射器。
二
必须醒着走路,必须安全回家,
他通过为自负的人铺设的幽暗之路。
那些正在等待的,是亲人,也是敌人。
房间的门反锁了。人们需要存储秘密。
他的身体中装了那么多痛苦,
但他不能炫耀,他微笑,去郊外散步。
当然,有时怯懦使他无所适从,
在惊恐的片刻,他也曾迷失自己。
那些封闭的人怎能看到他收集裂隙的时刻,
他们拍掉身上的尘土,却拍不掉愚蠢。
每个人的羞耻和嫉妒竟然如此相似,
在人们的眼神中,他看到了脆弱和无知。
三
他呼吸空气,每一天都在接受馈赠。
于是,他看到孩子们在庭院中嬉戏,
没有课程教他们大笑,呼喊,抢夺玩具,
他们却那么快就和欲望结合在了一起。
一出生就被赋予记忆,于是,他越来越
怀疑自我。诽谤者只知道满足。然而,
谦逊并不像开灯那样轻易,开启即关闭,
我们知道,恋爱的人竟无法相互原谅。
他试图进入生活,试图原谅自私的人们,
血液中那恐惧的滤纸不能阻止希望渗入。
再冷漠的目光也要融化在客厅之中,
那里充满了问候,椅子,鲜花和餐具。
他多么渴望相似于每一个被困在世上的人。
胡桑,现居上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