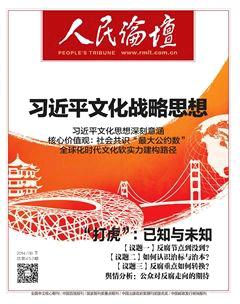有所思(外三首)
雨季过后一周,
太阳才把湿气消化。
一棵大树缠着枯黄的藤蔓
横躺在林中,
连带着两株伴生的小树
拦腰折断,倒入一片狼藉的草丛。
另一边,两棵挺立的松树已死去多年,
眼泪状的糙皮脱落了,
露出石灰白的光面。
抬头能看到围了一圈的橡树
伸出枝干,半掩半露地
把枯死的松树藏在背后。
攀援的藤蔓在那里横向发展,
连接起来,组成一个
神似凯旋门的拱。
除了这几处小小的衰败,
树林里生机勃勃。鸟雀的叫声
此起彼伏,野兔和松鼠也窜动树叶,
加入簌簌的响声。偶尔传来
树枝不堪重负
而折断的劈啪的声音。
一道小溪急流着尚未消化的雨水,
消失在树丛中咫尺外的黑暗,
奔向远处肿胀的河水。
干涸了一个冬季的溪流,
终于等来了耐心的补偿,
它潺潺流露的饥渴,压抑不住地
打湿了我的鞋子。
林间
下午,太阳的热气消退了,
黑油油的池沼,吸收了树林一天的呼吸
把倒影的树木波纹化,模糊化。
一只黄嘴美洲鹃栖息在枝头,打量着什么。
黑白林莺占据一处断木,自顾自地雕琢。
窸窣作响的地方,松鼠拖着尾巴
探头探脑地顿挫着。枯枝烂叶覆盖着的小路,
偶尔几只大蚂蚁无声地爬过去。
一只野鸭子呆站在草地上,湿漉漉的泥水滴下来。
另一只蹲在对面的草丛,把细细的腿拢起。
春天就要过去了,野蜂和蚊虫逐渐觉醒。
葱郁的阴影之外,直升机渐远的嗡鸣在蜿蜒
的深处回荡。
间或一两处树枝断裂,挂了一冬的野果
掉落,夸张了这一片回旋的寂静。
事物各安其位,埋头各自的世界。
我拖着疲惫的脚步走着,感受这些不相干
却又相连的声音,觉得自己也成了一个声音,
和自然
的和声交汇,感到巨大的被辜负的信任。
和一个声音的对话
你是什么?一个声音追着我问。
我困惑地环顾,我是什么?我不知道,
但我肯定不是一只鸟,鸟有翅膀,
令人羡慕,尤其是黑色的,闪着光。
不要回避问题,你今天必须回答我你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我无奈地重复,
也许我是一个人,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的人,
我如果这样答可令你满意,不行?
当然,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怎能不知自己是什么,你当我是傻瓜?
没有啊,不好意思,我没说你傻瓜,
但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我曾经以为自己知道,
尤其是
多年以前。不过我每次发现的我都立刻陌生,
现在?我真的不清楚,我甚至要问你
我是什么,你能回答的话,也许我可以提供一个
令你满意的背景?哈哈,你这个……!
我告诉你,既然你问,我可以肯定
你是一个人,一个有血肉的人,确定无误。
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只有你才能解除我的迷惑。
是吗?我可不敢如此肯定,如果那样,
为什么我如此犹豫?我感到的是血,它在流,
但这说明什么,什么都说明不了,难道你不这样认为?
不,不,我看到你的心浸在血里,难道它是在
水中跳动?
除此之外,你肯定多于我看到的,
你不会对自己的了解比我更少,不,绝不可能,
你又何必回避一个无关痛痒的疑问?
那好,我且不追问你的目的——我若是你,绝对不会
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我是什么,这无关神秘,
我就是一个我,我是你无法概括的我,也是我
自己无法概括的我,
我的存在由我控制,没错,但这又有什么,鹰也可以控制
自己的翅膀。难道鹰更明白自己是什么?
比喻
如果雨点落下来而不汇集,
不凝固,每个雨点都将成为个体,
好像河岸的鹅卵石,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存放的困难。
我们有多少石头来不及利用,
恐怕谈不上善识的眼去鉴别。
假如今年夏天多雨,至少
我们有的是经验对付台风或
洪水,但对于比喻我们还缺乏
必要的训练。如今我们不可能
把雨当作石头,反之亦然。
更有可能的不是比喻,而是幻想,
比如,鹅卵石变成雨点,把存放
的负担交给上天来承担。
比喻只有娱乐的功效,我们
随手都可以将它们低俗化:
任一领域都不再有单纯的沟壑。
而我们感到幸运,因为比喻不再
担负解救我们的任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鹅卵石的替代物,
比雨点更要光滑,轻盈,无害!
杨铁军,现居美国亚特兰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