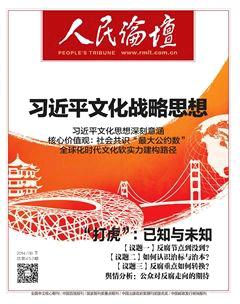我们不读小说了?
先说件事。2013年,潘石屹的妻子张欣,SOHO中国的CEO,在微博上感慨,说现在不读小说只读传记,因为“人到中年已经无法让小说家的花言巧语蒙住眼睛”。当时我还开玩笑跟帖,说这只能证明张老师老了,老得与日常生活一般模样。几天后,我去朋友处串门。他在清理办公室,各种文学期刊堆了半走廊,不乏名刊,多半连信封也没拆开。张欣不读小说我理解,可他是文学期刊的编辑呀,这就有点匪夷所思(期刊来源,一是同行寄赠,另外是单位订阅)。我嘲笑他是不是患了阅读恐惧症。他哂笑,说拿了卖废品的钱,请我喝咖啡。路上,还在邮报亭买了本《财经》。
这是赤裸裸的打脸。我拉长脸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向罗昌平致敬,自己在IPAD里已经订阅《财经》。我想起他前些日子在微博上开列的人文书单,问他现在是不是一个“望尽千帆皆不是”的心态,想跑到外面来看看“小说”。毕竟苏东坡也曾《题西林壁》,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结果他喷了我一脸唾沫。主要观点大致如下:
第一,今日中国是一个极度矛盾的社会,它有五种显而易见的基本冲突:一是知识体系;二是资本与权力;三是国族利益;四是技术与伦理;五是代际。这些文学期刊有哪几本能呈现出这个辽阔的现实?基本上都有一个视野与思想力匮乏的问题。现实每天都在野蛮生长,少有人能找到进入的通道,不是煽情就是矫情,或者说书人的格局,无法对剧变的时代给出一个丰富、深刻的解读。说书人不是不好,还有多少人愿意守候在茶馆里听那声惊堂木响?小说只有摆脱说书人的脸庞,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艺术中的一种,才能向死而生。今天许多小说文本的思想深度甚至落后于普通公众,除了自以为是的道德感,连起码的逻辑与常识都不具备,这怎么可能让读者对他们的大作有兴趣?小说家要在路上,要有对世界广阔性的追求,在这个奇异旅程中,不断地发现自我与另一个维度的事实,这是“广度”;“深度”是小说家终其一生要与之搏斗的事物。因为“我的任何描述总是打开通往更深远之处的门”。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里对“深度”有极精辟的阐释。深度与广度的出发点,都是“我”,不是“我们”,充满不确定性,是自我怀疑的、否定之否定式的。而我们自信的小说家多半热爱上帝的视角,太热衷于扮演道德帝与做价值判断或宏大叙事,通篇陈词滥调,一地鸡毛。时代变了。小说并不比现实拥有更多的特权。小说家也要像诗人那样懂得说,也必须说,“我不知道”。
第二,许多小说家的路径依赖,一望即知,毫无新意。写作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码字,对一个已知命题的加减乘除,以及卖油翁的“手熟耳”。而且越是名家之作,越好推测判断,情节、戏剧性、对细节的呈现方式、语言与结构……这很乏味,作者没有更高的抱负,苛刻一点的读者也难在其中觅得发现的乐趣、思维的乐趣。在这些小说家的潜意识里,他们是为读者生产消费品的,就像宝洁公司提供飘柔、潘婷,讲究的是标准化。这是一个智性与想象力不够的问题。小说是人类的精神产品。对精神产品的消费,与对物质产品的消费,都会遵守经济学的若干基本原则,比如权衡取舍、机会成本、交替关系,以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等,尤其是这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更讨厌的是,一些人非要说他们弄的这个才叫“文学”。我们说“文学就是文学”,不是说文学具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核,只有一小撮人才能心领神会的特别的形式;而是它根源于人类对世界的不断认识,以及基于这个认识基础上的“对激情的赞颂,对美的迷恋,对神秘性的渴望等”。又或者说,它是一个大超市,里面不仅有苹果与梨的不同,还有货架排列组合所形成的迷宫。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史,人类正在进化时,文学亦不例外。
第三,过于追求叙事的魅力,不愿意吸收当下各学科成果的营养,除了情感就是伦理,无法提供更多知识。这是一个信息量与知识力不够的问题。因为工作原因,我与许多小说家有过交谈,他们的思想深度、思维的模式、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占用、对信息社会的理解,确实存在极大的问题。他们少有阅读科学的、政治的、经济的、艺术的。相当一部分小说家,甚至不阅读,并以此为骄傲。某种意义上,小说家需要其他的职业身份,否则他就是个说书人。这个职业身份提供着一群人理解世界的观念、视角与经验(他是对他们的概括),一个可以信赖、值得尊重的知识结构。说书人不是不好,也就只能骗骗小孩开心,他们说的每个故事,与真正的智性与德性毫无关系。
第四,小说文本的主题与结构千篇一律,尤其是语言。随便在这些期刊中抽出几本,遮蔽作者姓名,便不难发现它们惊人的一致性,如同出自于一人之手,还都是“用机器进行的毛衣编织”的那种,阴柔、纠结。我喜欢糖,但若让我一日三餐都吃,吃的还都是大白兔奶糖,我就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语言是一个小说家的上岗证。它是对世界的言说方式,就像白话文运动,所承载的是思想、是情怀、是另一种思维方式。少有小说家能找到一个只属于他的语言系统。这是一个语言匮乏与文体自觉性不够的问题。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背景下,在这个蜂巢结构的信息社会里,文学,不仅是中国的文学,都在迎来一场根本性的革命。仍以语言为例。比如一篇批评新浪微博的文章,里面有一句“我才明白了新浪的‘险恶用心用心良苦”,这个“险恶用心”上有一横,是神来之笔,这是年轻人的写作技巧,我们的文学期刊上能允许这样的“差错”出现么?
第五,你说这是体制的原因,可你们就是体制。时代变了。不管你们是否纠结,整个人类社会的形态都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比如权力的本质已经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法权模式,以及能像商品一样进行交换的“上层建筑”,转为一种分散、不确定、复数的生产要素。官僚精英比你们看得更清楚;也许他们就是只想甩包袱,至少他们已经打算改变在文学这个领域司号发令的方式,更隐蔽,更强调技术手段,而非昔日的长官意志。这是一个文化生产机制的问题。被放逐是你们无法拒绝的宿命。被放逐后,你们的个人利益会受到极大损害,但对文学本身的繁荣来说反而是好事。开放的市场将取代封闭的权力。你们自诩为文学的守夜人,可你们真的能够理解这个“残酷”的现实吗?即现实不再是你们经验里的那个树状的“五子登科”,而是呈块茎结构,在土壤表层匐匍衍生,是图式,而非线性的轨迹,与多种维度相关联,被不断地撕裂、颠倒与修改。而基于二元论所建立起的传统文学原则,善与恶、丑与美、肤浅与深刻、高贵与卑贱、无聊与有趣,这些“非此即彼”的词语能够承载得起这个已经逐渐逸出“传统”的现实么?endprint
第六,不谈体制,也不把“现实”这个词语形而上,说市场,你们真懂吗?郭敬明的《最小说》发行量有几十万册,你们羡慕了,以文学的名义发表他的《临爵》,杂志实销量有改变吗?没有。势利眼容易有,市场很难有,它首先是一个价值观,其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大数据,需要用户体验、消费分析,需要产品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等等——它至少不在象牙塔里。你想告诉我《小说月报》发行量也不错?是不错,但《故事会》更不错。我不是说故事不好,故事是一种魔法,能把人的愿望变成事实;但这种对世界的童稚想象,不能提供更多,比如智识、思维及逻辑框架的建立、类似宗教情感的审美体验。不能因为读者的喜闻乐见就把故事摆上文学殿堂的最高处,日本AV女优还广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呢。市场阐释文学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文学话语权的问题。从技术角度来说,决定一部文学作品最关键的外部要素就是阐释与传播,这是一个极富偶然性的浪漫过程,是“历史的误会、时间的玩笑、社会的意志”等因素的总和,是一个社会现实与个人梦想不断碰撞的奇异过程,刹那,永恒;遗失,消亡。每本被置入文学殿堂的作品都有一个只属于它的奇特命运。过去扮演关键先生的是期刊,以后将是出版机构,尤其是民营书商。比如磨铁公司对“中间代”的操盘,金黎组合与刘震云的合作,乃至于《百年孤独》。据说新经典公司推出的这个取得作者授权的版本在两年时间内,销售已过百万册。多想一想,就能知道读者买的是什么,是“经典”两字,是“版权”本身与“营销”这种技术,而非内容——那些对它文学性感兴趣的人早已领略庐山真面目。这种巨量销售纯粹是一个消费社会里的符号消费。人的思维方式,在被资本意志重塑。市场这只强有力的手,在改变着所有人对文学的认知——不仅仅是“畅销书才是好书”,它在根本上改变着人体内的那个节奏,对美的认知,对什么是诗歌等,都将产生巨大的变化。现在,某些知名小说家还拥有令人咋舌的首印数与版税率,这是出版社集团化浪潮下“政绩工程”的要求。一旦它们彻底成为经济动物,以及数字化时代的全面来临、民企话语权的增加,这些作品的命运可想而知。大部分的文学刊物将沦为自娱自乐的小圈子,且以几位当家大哥的口味为审美标准。所谓小说将成为一种在博物馆展出的传统手艺活儿。
第七,再说得不客气一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杂志的同人性?一个小圈子里的吧。又当规则制定者,又当执法裁判,还往往热爱亲自下场当运动员……曾几何时,一个朋友拿来一本茅盾文学奖获奖者的散文集,说:让我开开眼界。看了几篇。确实,开眼界。这样的水平,也就是高中生的水平。拿纯文学的标签欺诳于世,是为耻辱。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你说我还有必要浪费时间在这些无聊的读物上么?读一本是必要的;读三本以上就是愚蠢的。
我走在回来的路上,怏怏不乐。我不喜欢朋友的这种批评。他的看法,就如刀;他的言说方式,好像世界上的兵器只有刀。他的思维逻辑有点“革命者砍下暴君的头颅,自己再一屁股坐在那把椅子上了”。但或许只有这种粗暴的“革命话语”才能推倒朱墙,使小说摆脱“伦理道德的修辞与实践”、“心灵鸡汤”等固有面貌,进到一个激流汹涌的更高维度。
他批评的是一个封闭结构的耗散与热寂。
传统小说的美学原则再怎么经典高贵,也难以摆脱熵增的宿命。它有过辉煌,当下更臻成熟丰腴。它对唐诗宋词里那个古典中国的传承及叙事,尤其是它在百余年间所贡献的汉字之美,象形、会意,是对人类文明的极大贡献;所承载着的诸子思想,儒释道等,至今也在塑造着一个中国人最根本的性情;它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与发扬,是它的最荣耀处。这是一个持续近百年的过程,是古老中国对世界的吃力打开,其间再三反复,有停滞、断裂,也有狂飙突进。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至今的三十余年间,中国的小说家把西方同行几百年做的事,用汉语及只属于他们的中国经验再做了一遍。一批值得后来者脱帽敬礼的文学经典涌现。用五号宋体书写,填满一张A4纸,没有任何问题。莫言的获奖可视之为这个文学黄金时期所结成的硕果。所以我总是不无偏执地认为,谁说当代中国小说是垃圾,那叫哗众取宠。或者只能说他被那些“集权的婢女”与“市场的妓女”弄花眼了。
但问题是,传统虽好,已然匮乏。
事实上,以虚构与叙事为主要特征的小说,在中国一直不为主流文学所取,直到民初由于梁启超等大力倡导,才被奉为文学之最上乘——其根子是载道言术,要拿小说去改造国民性,要教化与启蒙;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要训诫与规范。康生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其实不是发明。中国的小说一直是作为这个“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的史学传统之皮相存在。
小说是关于人的艺术,是时空观的具现,是对世界尽头的想象,是一个渺小性灵的生物与庞大滞重的现实互相生成。所谓现实,它总是在不断发生变化。又或者说,在观察这个名叫“现实”的人类历史进程时,我觉得首先要把它大致分成“匮乏”与“相对有余”两个时期。人吃饱了与吃不饱时,想的事说的话肯定是两回事。我们在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对“多余品”的追逐将构成人的日常。而以摩尔定律速度涌现的“多余品”将重新开启人的哲学王国与文学王国。
我们在进入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一个开放、多元、充满悖论,极其复杂的,且日趋复杂的社会;一个世俗趣味高涨、工具理性蔓延、拜物教横行的社会;一个不再询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而是询问“国家能为我做什么”的,个人即最高价值的社会。
这是我们今天的现实,但我们的文学实践远远落后于这个现实。以茅盾文学奖历届获奖作品为例,有几部作品能够勾勒出当代中国人的形象与性情?今天的中国人,与三十年前的中国人,以及三百年前的中国人,简直是地球人、火星人与三体人的区别。不客气地说,这些获奖作品中的大多数还是停留在我刚才说的“史学传统”里,所处理的题材基本还是那个已经离我们远去的古典农耕社会的魂魄,对以机械复制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社会少有触及,更毋论当下这个异常复杂的社会结构。他们所津津乐道的美学风貌,无非是“茶杯里的风景”。endprint
在《工作与时日》一书中,赫西俄德用“神的尺子”把人类社会分成:黄金、白银、青铜、英雄、黑铁五个时代。这是诗意的修辞。若换过把尺子,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把如今我们的寄身处,或可称之为“知识社会”。
新知识像炽热岩浆一样喷薄涌出,其增长呈指数形式而非线性,这不仅体现在速度上,亦体现在深度上(学科的分化与精细),还体现于广度上(跨学科的新领域层出不穷)。整个人类社会在这种指数增长的推动下,其结构、整体性产出,以及人际关系的连接方式,理解世界的维度,都在剧烈变化,在事实上被不断重构。这种变化极其复杂。比如,它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即悖论。比如,我们一天之内所能获得的信息量能超过几百年前一个人一生所获总和。一个高中理科生若穿越到牛顿发现苹果的时代,他能做伟人。另一方面,已知的圆圈越大,越清楚圆圈外面广袤的未知,越容易对宇宙与自身的奥秘困惑绝望。而作为个人,几乎都不可避免陷身于各自的知识洞穴。一个学科里的常识对另一学科来说可能是天方夜谭。
知识社会自信息社会中脱胎而出。若说信息社会强调“量的占有”,知识社会更注重对信息的过滤、筛选、加工及再生产的能力,强调人的主体位置,这是关于个人前所未有的事件。举个不恰当的比喻。信息社会是一个图书馆,书是第一位,它起源于技术进步;而知识社会,来图书馆的人是第一位。这是根本性的转变,人重新获得他的尊严与价值。信息社会主要由技术精英主导,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传播,具有很强烈的工具特征。知识社会乃是众生的觉醒,扁平、开放,对政治经济体制有着不言而喻的要求。
再通俗点说,我们在拿着手机用微信泡妞时,应该意识到:若没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没有那只薛定谔的猫,手机、电脑等这些90后觉得天经地义的东西,根本不会出现在人类社会中,成为民众须臾不能离开的现实。还有什么比这个被人类稀里糊涂地使用的量子力学更神秘魔幻的?马尔克斯获得世界性声誉后,大家说他魔幻。马尔克斯大声分辩:“我就是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家。”现实早不再只是牛顿力学支配的那个宏观世界里的日常经验;也不仅仅是伍尔芙看见的斑点,普鲁斯特想起的小茶饼,卡夫卡在洞穴里的梦呓与孤独……它是更多匪夷所思的建筑结构、吴莫愁古怪的音乐、凤姐与干露露的出位、中美就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博弈、黑天鹅事件、占领华尔街运动、种族冲突、科技增长、微博微信,以及越来越复杂的情感、人际关系等。
知识体系是子宫、矩阵。我想这也是朋友把知识体系的冲突列为今日中国五种基本冲突首位的原因所在。今天我们讲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一个西方化,是用西方几千年积淀下来的那套知识体系来改造全人类,所谓“世界改变中国”。这里也还存在一个“中国改变世界”的反馈机制。但前者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不同的知识体系之间甚至会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只能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用亨廷顿的话来说,这叫“文明的冲突”。亨廷顿把儒家文明列为几大基本文明之一,但经过1949年后的意识形态改造与1978年改革开放后消费主义兴起的双重风暴,今天的中国是没有儒的,再哗众取宠一点,那个“古老中国”在文化上已经濒临灭绝。被征服的,一定是落后的吗?又或者说,狐狸之所以吃兔子,吃得理直气壮、理所当然,是因为兔子是“落后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吗?这又是另外的话题,打住。
在这块“现实”土壤里,小说如何发现这个时代独一无二的特点与形式,获得它作为一门艺术“理应得到迄今为止仅仅为音乐、绘画、建筑方面的成功行业所保留着的一切荣誉和报酬”?
如果让我用两个词语来描述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时代,我会选择“Facebook”与“谷歌”。后者基于数学和逻辑学的理念,通过冰冷、严谨的技术建立;前者基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理念,联接人与人之间的“瞬间、暗示、碎片、神秘的微光,以及执子之手将子拖走”。
这是诸多文学大师所未能体验与无法想象的。
这也就是小说不死,仍将薪火相传的根源,是我们这些后来者继续书写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要有自身作为“人”的光芒。
极端地说,若文学只是对传统的继承,写作者就要有勇气做所谓文学的敌人,乃至于与自己为敌。要想拥有世界文学的高度,就得彻底摆脱乡土中国的经验——从故事模式到叙事技巧。今天的读者已被陷入匮乏的传统美学(小说)败坏了胃口。小说家要有能力区分小说与当代小说,像区分亡灵与生者的容貌,要有这种愿望去不断探索,充分借鉴电影、摄像、雕塑、音乐、绘画等其他艺术门类的理念与形式,以及科技进步带来的众多启迪,用一个《千年文学备忘录》的视野,写出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学,写出IBM电视广告里那个“智慧的地球”。
作为小说家,也得学会对读者提出要求,不再满足于分享经验、情感,在道德上做出判断与叙事。要有对难度及复杂性的呈现,这才是对读者真正的尊重。今天的读者已摆脱被动阅读的命运。他们不再是砖、螺丝钉,不愿意被规训、被洗脑。启蒙早不再是某种价值观的输出与接受,而是一个自我觉醒的动人旅程。在喜怒哀乐之外,读者渴望更多的智性含量。作为小说家,要有焦虑、愤怒,对现实的批判能力,对人的悲悯,对国族的爱;更要有能力与精神高度,去看见那些肉眼看不见的。在文体上,还要有这个能力去设计迷宫,提供梦境,为他们打开另一个不属于日常经验里的复杂空间。
真实世界永远比人最夸张的想象还要复杂亿万倍。小说要有这种对复杂性的追求。在我看来,这种愿望即是人最后的自由,是人存在于地球却能以浩瀚星辰为舞台背景的根本理由,是小说及人所创造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至高的美学原则——而不是温暖、悲悯等道德修辞,以及对人性有多少悱恻动人、深刻而又痛苦的描写。
那些目前被视作简洁且美的,不过是这只庞然大物表面的一块斑点,并且随着它的飞速膨胀,极可能丧失原本的形状与内涵,譬如曾经塑造过中国人性情的唐诗与宋词。它们的大多数是会形成标本,被保存,提醒着后来人:他们的来龙去脉。
博尔赫斯说“沙之书”。人类文明史上出现的每一本书都是其中一页,犹如蝶之翅翼,值得珍藏与赞叹,但不必五体投地。欣赏完后,年轻人要有这个冲动去翻开新的篇章,要有这个勇气去站在秩序与混沌的边缘,把自己视为“一个最微小的初始条件”,输入这个系统里。世界属于众生,但归根结底是被你注视的。你的目光让它获得了组织结构、声色光影,以及未来。要理解“蝴蝶效应”的真正涵义。endprint
换句话说,小说有一望而知的好,是好事,但不够,它在公众的经验范畴中,赞美是脱口而出。当代小说要有勇气来审视这些经验范畴,它给人最直观的第一印象,可能是“震惊”,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提到的那个词。这里要指出的是:当代小说并不意味着对读者的抛弃,它帮助读者发现那些前所未有的体验与思考,发现一个作为二十一世纪人类之子存在的“自我”,也像发现IPAD一样。
阅读可以分为三种,或者说三重境界。第一是倾听别人说话;第二是与自己对话;第三是见万物众生。第一种好理解。在倾听的过程中,读者逐渐地发现“我”与他者的关系,自我意识渐渐萌芽。第二种指六经注“我”,万物皆备于我。随着“我”的茁壮成长,世界因此五彩斑斓,有荒谬虚无爱恨愁苦。但这还不够,阅读还有更深的指向。第三种其实就是孔夫子讲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读者能从他/她/它的角度出发,像男人一样思考,像女人一样思考,像一个自由主义者一样思考,像一个国家主义者一样思考,像情人一样思考,像仇人一样思考,甚至是像动植物/无机物一样思考。一句话,一条公理,一篇文章,一个模型,能同时在你心里激起N种不同的,甚至是截然抵触彼此矛盾的声响。“自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内心宇宙,而不是傲慢与偏见的代名词。
后两重境界,是当代小说家所要引领读者的所去之处。是阅读在未来的大势所趋。
而从现实层面来说,当代小说家也完全没必要有被读者抛弃的顾虑。读者抽象且具体。一方面它犹如星辰,映耀着一间间书写者的陋室与那条隐秘的人类精神河流;另一方面,它本身亦在不断变化。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接近百分之九十;现在,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发布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是百分之四点零八。公众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必然会对小说提出新的要求。当代小说家要有一种在阳春白雪的高度去书写的愿望。登上层楼,再上层楼,只有小说家先“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了,读者才可能跟着攀援而上,欣赏到《望岳》这样绝美壮丽的诗句。
许多人说文学在式微。这话对,也不对。式微的,其实是几种文学媒介与形式,以及社会对文学的关注度。文学本身并不式微,反而随着知识生产的倍增,呈现出一个极开阔、极复杂的图景,且与教育水平得到普遍提高的公众关系更为密切,呈现出一种从公共空间走向私域的倾向。文学在成为母体,犹如水滋养各种艺术形式。
一个人内心的宽度,只能靠他读过来的文字几毫米毫米地码出来。人们不是不阅读了,只是阅读的介质、模式、主要群体,以及阅读的技术、方法等发生了变化;小说不是没有人读,而是传统语境里的那个“小说”少有人读了。
我们吃饭,每天都吃,但不能说活着就是为了吃饭,而是另有追求。对于当代小说而言,传统小说的叙事美学不再是核心。叙事是完成语言与结构,完成一个人自我认知、自我进化、自我溢出的过程。
当代小说的命运将不可避免地转向诗、哲学、人物的脸庞,以及虚构之力。当代小说最重要的职责将是:启人深思,帮助人们在喧嚣中发现孤独,发现生命的百感交集,在众多一闪即逝的脸庞上瞥见天堂。
一个当代小说文本,是人在键盘上敲下的,“他所想、他所能”敲下的亿万之一,是概率的产物,骰子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停止转动,词语与句子得以显现。在这个“自我闪耀”的奇异旅程,读者与作者成为人的左右脑。或者说,作者与读者这两个词语,还是启蒙语境里的分离,分别扮演传道授业的老师与“程门立雪”的学生形象;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它们构成一个完整的“人”。对于这个“人”来说,阅读与写作是他了解宇宙与自身奥秘的两种手段,是他生命中的学与思,是第一位的;而来自他人的认同感(发表与稿费)退居其次。
李敬泽先生出版了一本《致理想读者》。在我看来,这个“理想读者”其实就是致一个理想的自己,是对“自我”的镜中凝眸。另外,在这个每天都在被“全球化、消费社会、技术进步、互联网思维、知识革命”等深刻改变着的社会里,理想读者也不会只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形象,映雪囊萤,悬梁锥股……一个刚运动完的少年,坐下休憩,顺手拿出手机开始阅读,指尖划过屏幕,突然有那么几句文字犹如闪电一样,照亮了他的心灵世界。那时的他,就是理想读者。
当代小说并不等于小说的当代性。当代小说是在“大海停止处,望见另一个自己在眺望大海”,它强调:深度、广度、维度、高度。深度是说“我的每一次触及都在打开更深远之门”。广度是说“我的履痕及对世界广阔性的赞叹”。维度是说“我看见了银幕这面,也看见了银幕的后面”。高度是说“我在月球上望见地球是圆的这个事实”。
当代小说是有关于“我”的一切,是从“我”出发所看见的一切,世界因为“我”的行动呈现出种种可能性,它是狐疑的,充满不确定性与否定之否定。而当代性是一个正在鼻子底下发生的现实,是对处理这个“正在进行时”经验的概括与分享。比如过去的女人碰到男人劈腿,找妇联哭诉;现在的女人碰到男人劈腿,通过微博微信声讨。传统小说同样可以具有很好的当代性,比如写拆迁。写爷爷穿上寿衣,扛着钢瓶上了屋顶。当代小说来处理同样一个题材,就不会仅局限于道德控诉与戏剧性冲突。也许是邻居的猫,举着一根被顽童浇油点燃的尾巴,窜到屋顶被拧开阀门的钢瓶前……换句话说,相对于传统小说的一条或几条路径,当代小说是一座小径分岔的花园。
世界是复杂的,且日趋复杂。当代小说将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事实。
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徐冰先生说过一句话:“素描训练不是让你学会画像一个东西,而是通过这种训练,让你从一个粗糙的人变为一个精致的人,一个训练有素、懂得工作方法的人,懂得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明察秋毫的人。”
我在这里改写一下:“对文学的热爱不会让你当官发财,而是通过这种热爱,让你从一个贫乏的人变为一个丰饶的人,一个自我觉醒、懂得爱恨的人,懂得在这个科学建构的世界里发现美与激情的人。”
黄孝阳,作家,现居南京。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人间世》、《旅人书》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