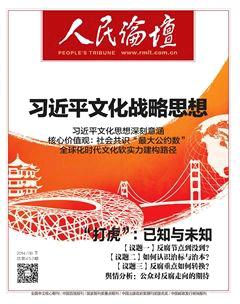鸽事短章
严敬
鸽事短章
严敬
鸽事
以前,细哥养鸽的时候,有很多鸽子选择我家作为它们的新居所。鸽子是非常恋巢的鸟,绝不会轻易离家出逃,即使把它们捉到很远的地方去,它们也会回到旧主人的家。它们如果离开旧主人,那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多半是因为旧主人的鸽窝太拥挤了,没有它们的立足之地。它们要生儿育女,所以要寻找新的家。
细哥总是在屋檐下不断地挂上新鸽窝(一个农药箱子,或者一个竹篮子),使每对鸽子夫妻都有固定舒适的窠,有的鸽子甚至有两个窠,满足了鸽子生存的需要。鸽子喜欢住在一起,一块儿觅食,一块儿翱翔蓝天。鸽子还喜欢走亲访友,同村的、抑或不同村的,都要来来往往,互相走动,保持联系。在相互拜访中,欣赏着彼此的居所。经常有别人家的鸽子飞到我家,在我家的鸽子窠上歇一会儿,探究一番,常常舍不得离去。
那时养鸽很简单,不搭鸽棚,往屋檐下挂一个木箱子,当作鸽子窠,招来鸽子,让它留下。鸽子很愿意和人亲近,只要有一个形似窠的东西,它就会把它看成家。鸽子根本不喂,到田野里打野食。也不用控制它们,飞进飞出,完全自由。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对雨点鸽,而且是当时少见的大鼻子鸽子,它们飞进我家,住下来,繁衍起它们的后代。这应该是1972年前后的事情。一年后我家搬了,在新屋里,由于开家的失败,老鸽子死的死、逃的逃,但细哥成功地留下了大鼻子雨点鸽的后代,并依靠雨点鸽的一对儿女重新养起鸽子来。不久,我家的鸽群又在天上盘旋,还吸引来了别人家的鸽子。
逃跑的鸽子
458是一只深雨点雌鸽,左右翅膀各有一根白色羽条,很是漂亮。有案可查的是,它出生于2008年7月9日,2010年11月6日莫名其妙地飞失。我在家等着它归巢,谁知,它连影儿也不见。它参加的这次训放并不困难,仅仅是两百多公里的阳江站训放。
在此之前,它参加了几次五百公里的比赛,虽没有值得骄傲的成绩,但均顺利归巢。使我看重它的是,2009年12月19日,458参加了厦门比赛,空距一千公里,它次日中午归巢,获二十八名。它是我的第一只千公里归巢鸽,我心里盘算着如何给它挑选几只雄鸽,让我的鸽棚里充满千公里鸽子的子孙。但事与愿违,458这只漂亮的雌鸽配过两只雄鸽,产下的都是畸形蛋,最后干脆不见动静。无论我怎样盼望它受孕生卵,结果,它一直没有做过母亲。
次年秋赛,我再次让它参加比赛,按部就班由近而远地训放,心想让它再飞一次千公里。但是,训到阳江时,它没有回来。
我非常失望,一只参加过千公里比赛并获奖的鸽子,居然在两百公里的训放中飞失了。什么原因?这不合情理,如同挑过千斤重担的肩膀,最后叫一根稻草压垮了。
我想,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它不能归巢,它出了意外,受伤了?当然,这有可能,但是,以往它经历了许多次这样的训放都安全回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过去那么幸运?
除了难以预料的客观原因外,是否存在着主观原因,458既没有受伤,也没有迷路,而是它干脆不想回来了。接连不断的训赛使它产生了厌倦情绪,它讨厌没完没了的比赛,它心中闪过一个念头,拒绝再过过去那样的生活,而且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所以,它没有继续往前飞翔,而是停在中途的某一个地方。或者,它飞到了家,但是,它从鸽棚的上空一飞而过,告别了家,另觅新家去了。
会是这样吗?真的不得而知。
女孩
鸽子一般长到六七个月的时候,即可发育成熟,这时,它们开始配对、交尾、产仔、繁衍后代。
蛋产出来,光滑,浑圆,如珠似玉。一枚漂亮的蛋变成一只鸽子,要等上漫长的十八天。
我见过很多鸽蛋,然后,看见一枚枚蛋蜕变成鸽子。蛋怎样变成鸽子呢?这简单之至,只须时日,只消白天和白天的叠加,只消一些昼夜的更替。蛋变鸽,只是时间的堆积。
我总是焦急地等待蛋变鸽,很多时候,结局是美妙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孵化,薄薄的蛋壳里形成了乾坤,一个娇嫩的小生命破壳而出。刚刚出生的雏鸽,很难说它是什么,与其说是鸟,不如说更像人的胚胎。但它是生命,这个比拇指还小的肉团,身上布满了细细的血管,一线稀薄的血正在周身缓缓流淌。而这血线由十八个昼夜连结而成。
这个结局是美妙的。
但是,有一回,我失去了耐心,按我的计算,该是雏鸽出壳的日子,但蛋毫无动静。蛋里面可能发生了情况,雏鸽遇到了麻烦,它既咬不破蛋膜,更无力挣脱蛋壳。我很可怜这个雏鸽,心里十分着急。这一急不要紧,我干脆动起手来,用手慢慢为雏鸽剥去身上的铠甲。在我帮助下,雏鸽出世了,它的头颈发育良好,已经有模有样,但它的肚子却是一泡血水,看不出是什么东西。雏鸽的眼睛紧闭,但小嘴微微张合,仿佛无声地责备我,为什么要这么造次。
我很难过,如果再等一两天,它就是一只鸽子,但现在,它什么也不是。我阻碍了时间的脚步,使它来不及让一枚蛋形成完美的结局。
许多时候,我把目光从鸽子身上移开,投到我身边的事物上。
有一个女孩,她说谎,早恋,贪吃,搬弄是非,甚或爱慕虚荣,贪图享受。她唯一的长处就是,她年幼,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少女,时间在她身体逐日堆积,使她的身体正迅速走向成熟,如同一株搭乘夏天这列火车的植物,轰隆隆地驶向秋天,不久,将结出一身香甜的果实。一个极容易被诱惑的女孩,同时,世界也被她轻易地诱惑。
我目睹时间像水一样流去,也目睹她一天天变得有模有样。
时间正往她身上堆积宝藏,而经过我时,却大把地捎去它以前馈赠给我的礼物。
斑鸠
斑鸠是信鸽的表亲,若干年前,信鸽从旷野移居到人类的屋檐下,而斑鸠仍留在森林里,它保留的是自由和野性。它的嘴又尖又长,小脑袋瓜细削得有点滑稽,胸脯也不丰满,而且所有的斑鸠都穿着相同的赤褐色的衣衫,这些似乎都说明,旷野的食物越来越少了,它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尽管它的表亲们都过上了富裕的日子,但它依然死脑筋,拒绝和它们来往。我从来没有见过斑鸠跑到鸽群中来,哪怕前来张望一下。对于信鸽的丰衣足食,它好像从来就不羡慕。
阴雨天持续了有一些日子,今天,天终于晴了,天空辽阔,空气新鲜。
趁着好光景,斑鸠急忙谈起了恋爱。早晨和中午它都在长鸣,极其执著,它的身影掩隐在浓密的树丛里,嘹亮的歌声到处飘扬。
只是我不知道,两段时间里的斑鸠是不是同一只斑鸠,如果是的话,它所从事的工作是不是已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
这种鸟很腼腆,怕见人,生活在密林里,高兴的时候也跑到楼房旁的树上唱个不停。被它的歌声吸引,我轻轻地靠近它,谁知弄巧成拙,斑鸠察觉了树下的异常,突然关闭了歌喉,“啪、啪”,大怒而去。
三十多年前,为了把这种鸟看得仔细一些,夏天的正午,我匍匐在它经常觅食处的草丛里,守候它的到来。草丛不透风,热得像蒸笼,呆一会儿就浑身湿透。我的愿望总是落空,守候了许多个正午,不是没有鸟来,就是那精明的鸟儿倏地一声从头顶上飞过。
有一回,肯定是对我的奖赏,一只赤褐色的斑鸠落到我的眼前,它像一团炭火,十分耀眼,它的眼眉仿佛刚刚描画过,漂亮极了。它一心觅食,正午的炎热,烫脚的尘土,草丛里张大的眼睛,似乎都不在它的心上。
鹰
天空,是祖辈留给它的巨大的遗产,尖嘴、利爪也是的。从天空深处,俯冲而下,这种雄姿,也是它持有的遗产之一。它还是鸽子的天敌,那种睥睨一切的优越感(已经融入了它的血液),照样是它领受的遗产。诸多遗产,组成了鹰的取之不尽的财富。
一天早晨,楼顶上空来了三只鹰。鹰的位置很高,像指甲般贴住苍穹。它们既悠闲又傲慢,圈也不转,极其缓慢地朝南移去。
风似乎从它们翅膀底下流过,但它们不认为是风驮着它们,相反,是它们翅膀扇出了风。风生云,云生雨,雨孕万物。没有它们的翅膀,便没有风。
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冲着我的鸽子来的,但是,如果此时鸽子出现,说不定会有惊险的一幕上演。幸好,三只鹰心不在焉,一点点移动,仿佛已经入睡,正躺在空气的怀抱。也许它们只是路过,它们惦记着别的更重要的事情。也许,今天,它们什么事情也没有,只是休闲,散散心,做做游戏。
这不打紧,阳光把它们的身影投射下来,我的鸽子,早就发现了鹰影,互相警告着,躲在棚里,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等了很久,可能就是一个上午的光景,流云和各种影子一一消失,我的鸽子,打头的是608,才心有余悸地飞出鸽棚。
离去的鸽子
自2007年再次建棚养鸽以来,棚中每只鸽子都有记录,无论是健在的,还是放飞丢失的和赠送给人的,我都有关于它们的详细档案。哪怕一只天落抑或过路的鸽子,我都记下它们的环号、羽色、眼砂。只要打开电脑,这些鸽子又会翩然来到眼前。
记忆是深刻的,有时安静下来,就会想起这些年离我而去的鸽子们。它们是我的朋友,在不同时候,陪伴我度过了许多时光。
别说是这几年离去的鸽子,就是二十年前、四十年前的许多鸽子我都清楚记得它们的样子,如果能穿越时空,有缘再和它们见面,我能一一认出它们,一一记起当时的天气,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人事和鸽事。
好多事情就是这样奇怪,比如记忆,现在,往往一分钟之前做下的事,眨眼就忘个精光,而几十年前的旧事却如同刀刻一般留在心里。
我的许多离去的鸽子就是这样活在我的心里。
1996年,整个夏天我都住在医院里,祁伟——这个比我年少的朋友,常常跑到病房里和我聊鸽子,住院之前,我的鸽子008刚刚从淮北归巢,它是我的第一羽放飞500公里归巢鸽子,它自然成了我们经常的话题。鸽子使我忘记了病痛。
记住一只鸽子比记住一个人容易,也幸福得多。如果一只鸽子同一个善良的人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更完美的事情。
鸽子不用去记,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脑海里,它来来去去,我的不太好使的脑瓜就是它的栖架。
严敬,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小说集《五月初夏的晚风》。
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