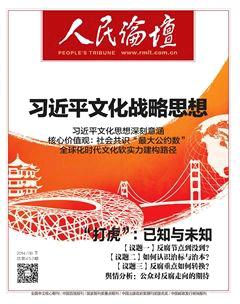渔人笔记
刘春龙
渔人笔记
刘春龙
扳罾
罾是一种古老的渔具了,《楚辞·九歌》中就有“罾何为兮木上”一句。罾的种类也多,像吊罾、提罾,还有蟹罾、虾罾……这里说的,是那种横跨整个河面的大罾。里下河水乡,有河就一定有大罾。至于罾的大小,则完全取决于河面的宽度。这样的大罾离村庄并不远,谁家来了亲戚,拎只篮子,跑到罾棚前就能买到鱼。
扳大罾的设施包括罾网、罾架、绞车、罾棚等。过去的罾网都是人工编织,可以一人也可多人合作,现在已改成机械制作了。不管是人工的还是机制的,这样的网片总不能直接作为罾网,还需依据河的宽度和深度再次加工才行。罾架用以支撑硕大的罾网,几根粗壮颀长的竹篙,连在罾网的四角,固定在岸边,随绞车的牵引而直立,松放而平躺。绞车其实就是辘轳,收放罾网用的。罾棚呢,自然就是扳罾人歇脚的地方了。
扳大罾是个力气活,你要把那么大的一个罾网扳起来,没有一把力气是不行的,尤其是那种支放在宽阔河面上的大罾。光凭力气也不行,还得讲究点技巧。高中毕业那年,我和同学跟着表哥去扳罾,同学就吃了不懂技巧的亏。看着表哥扳罾挺熟练,以为自己有的是力气,软磨硬泡,缠着表哥也让我们试一试。表哥开始不答应,说我们个子小,没啥力气,指不定会“甩田鸡”的。我以为不会踏水车的会“吊田鸡”,哪有扳大罾“甩田鸡”的说法?不肯归不肯,编瞎话哄人干什么。表哥见我生气,很不情愿地让步了。我高兴极了,摆开架势,扳起罾来。还好,尽管稍稍吃力,但还能把罾扳起来。当然了,那罾很小,架在一条新开挖的河道上。我清楚地记得,那一罾扳了一条鲌鱼两条鲢鱼,还有十多条餐鲦。同学把那长长的捞海伸到罾网里,可怎么也捞不着鱼。表哥笑着抢过来,只在罾网里拍打了几下,那鱼就“跳”进捞海里了。放罾的时候,我学着表哥的样子,先把扳架从绳套里松开,然后双手搁在两个扳架中间,随着罾网急速下沉,只听得耳边呼呼的风响,感觉好极了。同学见状,嚷嚷着也要扳罾。他个子比我还小,似乎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要不是表哥“借”了把力,凭他的本事是没法将罾网出水的。不过,那一罾的收获比我扳的要多,我都有点嫉妒了。也许是表哥只顾着捞鱼,疏忽了对他的保护,也许是同学高兴过头,放罾时,那罾网的拽力太大了,一不留神,同学的衣服竟被绞车的扳手缠着,随着惯性,猛地被撂到罾网里,真的“甩田鸡”了。好在同学只是撕破了衣服受了点轻伤,我们都吓坏了,谁也不敢跟家里人说。
扳大罾更重要的是经验,老道的扳罾人自然知道哪个季节鱼多,哪个时辰有鱼。梅雨季节是扳大罾的旺季,扳罾人白天黑夜连轴转,因为收获的鱼多,并不感到疲劳。大多数时候,白天是不怎么扳罾的,所以行人看到的大罾常常是吊着的。我见过的最大的一个大罾是架设在车路河上的,怕有几十米宽吧。扳罾的辘轳是竖着的,要三四个人齐力推着才行。收获的时候,罾网里要停只小船,专门用来捞鱼。一罾扳上一船鱼,那是常有的事。有一年发大水,我曾亲眼看见过,光毛(鳗)鱼就扳了大半船。不过,这样的大罾也有麻烦,车路河是省级航道,来往船只太多,忽然来了一条拖队,是让它从罾上走,还是从罾下过,那可是要计算好的。也有说扳罾人奸诈的,有机动船从罾下经过,不小心碰着罾网了,撕开很大一个口子,船主不知就里,好说歹说,赔了好多钱。扳罾的窃笑,其实只要一根线就可以补好了。后来据说有人专门干此营生,不扳鱼只扳船,这就不对了。
小时候,我常到罾棚里玩,看扳罾,听扳罾的讲故事。那时听得最多的就是“鱼阵”的故事。发水季节,鱼儿常常成群结队溯水而行,碰上这种情况,有心计的会让“阵头”过去,只扳“阵尾”。说有一个人心路太大,看到鱼阵,想“一锅端”,结果鱼群把罾网冲破了。“有时人真的不能太贪,太贪了往往会失去得更多。”扳罾的讲完故事,常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打簖
渔家有句俗语,叫“勤扳罾,懒打簖”。这话的意思是说,扳罾一定要勤快,而打簖是可以偷懒的。如此说来,打簖似乎是一劳永逸的了。春头上把簖打好了,只等着每天收获就是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簖也的确是一年到头固定在那儿的,除了簖旁停只渔船或是搭个渔棚,并不见渔人忙着什么。果真如此吗?未必。只是打簖人的艰辛,我们不常看到罢了。
起初的簖是芦苇编织的,只能打在小河小沟里,虽少来往船只,但也容易受损。后来渔人改用竹箔,把劈开的竹条编成箔子,安插在河道上,再用粗壮的竹篙稳固。现在的簖又变样了,材料大都是塑料网片,虽比过去省事,又常跟缳袋连在一起,但这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簖了。这固然是社会的进步,可我依旧怀念竹簖时代。不管它是哪种材料哪种形式,簖的最大功能就是设置机关,又称鱼道,以阻挡鱼蟹的前行,诱使其进入“陷阱”。所以,人们又形象地把簖称之为“八卦阵”或“迷魂阵”。
你要问里下河的簖有多宽,渔人只告诉你,河有多宽簖有多宽。那簖要把整个河面拦截起来,中间留有一定距离的口门,口门的竹箔与水面大致相平,以方便船只通行;左右则是对称的鱼道,鱼道的竹箔要高出水面很多。鱼在游动或蟹在爬行时,碰到竹箔挡了去路,自会顺着竹箔寻找出口,不经意间就会进入渔人设置的机关,也就是鱼道了。渔人又把这叫作“篓儿”。游进的鱼也好,爬进的蟹也罢,几乎不可能再逃出来,渔人只需在清晨用捞海朝“篓儿”里捞鱼就是了。我讲的当然是竹簖了,网簖就简单许多,只需拎起缳袋倒鱼就行了。有时,渔人还会在簖的两边配上“跳箔”,挂起一张网,斜斜地插上几根涂白了的篾片。鱼儿游近“跳箔”附近时,感觉到晃晃的白光,以为是湍急的流水,本能地跳跃起来,一跳也就跳进了网里。
打簖也有忙的时候,那是黄梅或重阳时节。黄梅时节,正是里下河的汛期,连绵不断的雨扩充了水体,也刺激着鱼儿。鱼儿骚动起来,是那种少有的亢奋,常会成群结队,溯水而行。这正是渔人所希望的,他们会加固簖箔,理好鱼道,慷慨地接受老天的馈赠。
另一个时节则是重阳前后了,那倒不是捕鱼,而是捕蟹。成熟了的螃蟹不会在内河水体里自然繁殖,它们要洄游到海水淡水交汇处的长江口去。这时的螃蟹仿佛被施了某种魔法,只顾埋头向前,遇坎爬坎,遇簖翻簖。渔人就要在“篓儿”上加上一层盖网,但就这样也保不准有螃蟹翻过簖箔的,鱼儿也一样,跃过簖口是常有的事。因此,渔家又有“千罾万簖,捕不到一半”之说。
阿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残阳映鱼簖,尤其具有画图风味。”关于簖的记忆,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却是在一个朗朗的月夜,驾船过簖,见簖口挂着两盏马灯,隐隐约约,听竹箔滑过船底的声响,嘎嚓嚓嚓——疑似梦境,恍若隔世。不管是残阳下的还是月夜里的,簖确乎已成为水乡的一种意象了。
这段时间重读唐陆龟蒙的《渔具诗》,见有“沪,吴人今谓之簖”一句,我总觉得这种说法不太严谨。沪虽说也是一种捕鱼的竹栅,但与簖还是有区别的。沪设在江边或海边,长短不限,依赖涨潮落潮而收获,簖则打在内河里,拦截整个河道,基本不受水情影响。从这件事情说开去,有时古人的话也不一定全对。
围箔
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真正意义上的湖荡吗?想想儿时的湖荡,自然生长着芦苇,自由飞翔着野禽,自在游弋着鱼虾……不知何时,鲜活的湖荡已是容颜不再,魂灵远逝,只剩下故事和日渐陌生的名字,偶尔让你想起一个曾经叫过湖荡的地方。
某一日,我漫步在得胜湖边的圩堤上,透过一方方整齐的鱼池,一条条笔直的田埂,试图找寻久远的往事,捡拾记忆的碎片,拼凑出一个真实的湖荡来。
谁家清塘了,池底露出来,有几处水洼,游着最后的鱼儿。岸边早聚集一帮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等着打扫战场呢。这是一种近乎原始的叫作伴工(也叫换工)的劳作方式,今天我家帮你家,明儿你家帮我家。当然不计报酬了,无非款待一下,也不讲究,烧条鱼就行。不知是谁领了头,大家操起了捞海、趟网,鱼池里一片忙碌,一片欢笑。
说不清什么诱因,是浓浓的捉鱼氛围,是渔姑的悄然一瞥,是鱼舍前的几张鱼罩,还是谁的一声惊呼?蓦地,我的眼前顿时出现一幅久违的打箔围渔图。
画面的背景应该是油菜花吧,还有青青的芦芽,清清的湖水。几条渔船从花丛苇丛中驶出,蜿蜒前行,在一处浅滩边依次停下。船头有几张鱼罩,几捆竹箔。渔人将竹篙插入湖中,系上船绳,随即纷纷跳到湖里,有的扛着竹箔,有的端着鱼罩。这支队伍是个大家庭了,怕有二十个人吧,也许更多?
扛竹箔的大都是男人,每人两条竹箔,一条大约五米长。他们排成一列,像接力赛,第一人把竹箔插入湖底,第二人接着再插,一个跟着一个,竹箔也就不断向前延伸,呈一个接近半圆的弧形,宛若水上长城。这个过程就是打箔了,也叫围箔。
当最后一个人把最后一条竹箔打下时,另一路人马出发了。这是罩鱼的,常常是女人。她们紧挨着一字排开,沿着竹箔的路线向前,边走边按下鱼罩。罩着鱼了,就用双脚夹起,鱼也不大,像鲫鱼、黑鱼什么的。没罩着也无所谓,此时罩鱼更多是为了驱鱼,把鱼往“陷阱”里赶。
在罩鱼的队伍缓缓前行的同时,打箔的会将罩鱼人身后的竹箔收起来,快速跑到尽头,再接着往前插。这样的线路是渐渐内缩的螺旋状,围着的水面也就越来越小。看看差不多了,打箔的来个急转弯,用收起的竹箔将包围圈收口了。这下好了,鱼儿再无逃路,渔人尽可以从容地用鱼罩捕捉了。越到最后,鱼的品种越多,个头也越大。
围渔的队伍是该有个头儿的,可你看不出,谁都像,谁都不是,多年来的默契,约定俗成了。围渔的过程也该紧张的,可又不觉得慌乱,是那种井然有序,从容不迫。偶有一声惊呼,也是因为碰着一条值得惊呼的鱼了。什么鱼值得如此这般惊呼呢,得胜湖里可是什么鱼都有的,见怪不怪了,难道还有不曾见过的鱼?等捉上来才知道,嗨,不就是甲鱼、黄箭(鳡鱼)嘛。可那是锅盖大的甲鱼,头二十斤的黄箭啊,能不惊呼吗?
这样一个捕鱼的大场景,或许会让你想起村姑采菱的嬉闹,想起皇家围猎的豪放,只是时间空间不同罢了。而昨日的打箔与眼下的清塘,时间虽不同,空间却一样,也已“物似人非”了。恍惚中,我竟成了打箔中的一员,至于什么角色,倒有点模糊了……模糊的,还有这渔事背后的那个湖荡。
罱鱼
虽说人类文明的进程是先渔猎后农耕,但我仍然认为罱鱼是从罱泥演变而来的。起初,农人罱泥时常会罱到小鱼小虾,像罗汉鱼、鳑鲏儿什么的,有时也能碰上稍大点的黑鱼、鲫鱼。这样的次数多了,有人干脆就制作了专门的罱子,趁着农闲罱鱼去。
小时候,我喜欢跟在大人后面去看罱泥。按理说,罱泥单调乏味,有什么看头呢。我之所以爱去,说出来不怕您笑话,就为了看一罱子泥提放到舱里后,那随泥而下的鱼虾活蹦乱跳的有趣样子。这刻儿,我会抄起自带的捞海,把鱼虾捞上来……后来上初中放忙假时,我又学着“拿”泥船;也曾人小鬼大地要学罱泥,可两只手连罱篙都抓不牢,只得求其次了。“拿”泥船也不是件轻巧活,你不仅要会撑船,还得与罱泥人的动作保持协调,俗话叫“敌”得住船。就连这,我也是手忙脚乱。有时,罱泥的叔叔宽厚地笑笑,要我把船撑到垛田的沟汊里,由着他一个人罱。那就不是弓着身子向前罱了,而是直直地把罱子按到河底去“夹”。倒是不用“拿”泥船了,乐得我只顾去捞舱里的鱼虾。有时一罱子泥放到舱里,会突然窜出一条大黑鱼,吓你一跳,溅得一脸泥水……
农人把满舱的泥攉到泥坞塘里,沤草窖,作肥料。第二天起早再来看看,常有意外收获。经过一夜的沉淀,塘面上竟是密密一层螺蛳和鱼虾,那是昨天的漏网者。你就抓紧捡拾、捞取吧,下一个泥坞塘还等着你哩。
现在罱泥已渐渐离我们远去,残留的记忆常常是春耕季节大河湖荡里罱篙如林的场面,还有粗犷的罱泥汉和勤快的“拿”船女。不过,怀旧归怀旧,到了冬闲时候,里下河水乡还会看到另外一道风景,叫人依稀联想起罱泥的事情来,这就是罱鱼,农人戏称为“夹大罱子”。
罱鱼之罱与罱泥之罱是不一样的,前者取鱼,后者取泥嘛。罱鱼的罱口大,网眼稀;罱泥的罱口小,网眼密。罱鱼的罱篙是笔直的,不像罱泥的罱篙要把根部“熨”成弯形。最大的不同是罱的方式,罱鱼是把罱口张到极致,猛地直按到河底,随即快速并拢提起;罱泥呢,则是把罱子搁到河里,着底后再张开罱口向前推进,等罱子里的泥满了,这才慢慢并拢提起。
只有在冬季才会见到有人专门罱鱼,这是由农情和渔情决定的。罱鱼时,通常是一人撑船,一人夹罱子。选择水底平坦的岸沟、菱塘、湖荡、荒滩,一路罱下去。撑船人和着罱鱼人的节奏“拿”着船,罱鱼人一罱子下去,挨着船帮提起来,张开罱口,将罱中所获倒到舱里。罱鱼所得,大都是底层鱼,鲫鱼、黑鱼、虎头鲨,还有一些小杂鱼。原先庄稼人罱鱼只是图个热闹、找个乐子,顺便弄点下酒菜,并不以此谋生的。现在一些大水面的罧塘捕捞时,倒是经常可以看到专业的罱鱼队了。
这样一说,最热闹的罱鱼场景肯定就是出罧的时候了。十多条乃至几十条罱鱼船活跃在罧塘里外,气势恢弘,蔚为壮观。在罧塘里罱鱼的是自家人,请来帮忙的;罧塘外的则是捡漏的,所谓“鱼生四两各有主”嘛。不管是谁,大家都比试着罱鱼的技艺。这就有点卖弄的意味了,因为岸上正聚集着看新奇的人群,黑压压一片。于是罧塘沸腾了,欢笑声、惊呼声、吆喝声闹成一片。这是一个豪放的季节,也是一个喜庆的季节。
刘春龙,作家,现居江苏兴化。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深爱至痛》、散文集《乡村捕钓散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