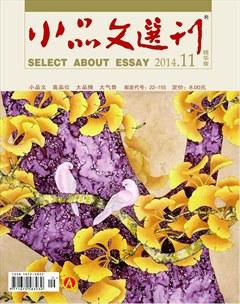声响
周伟
我一回去,母亲就跟我说,你奶奶不知怎么的了?一到夜里,总要生出好多好多无由无端的声响来,一整夜一整夜地不歇。
那一晚,我就睡在奶奶卧房的隔壁。房子中间只隔一扇木板墙,木板也许是年代久远了,单薄陈旧,木板之间的缝隙都大开着。奶奶不吃夜饭,早早地就上床睡了,灯也不开。我也熄了灯,躺在床上,我能感觉到奶奶的鼻息和呵气,还有夜空中弥漫着米汤、南瓜粥和烤红薯的气息。我想,今夜,我会拥有难得的温馨与酣睡了。
不一会,窸窸窣窣,窸窸窣窣。是不是我睡的房子里有老鼠?我一向怕老鼠,我一下坐了起来,忙扯亮了灯,什么都没有。我下意识地感觉到是奶奶那边弄出的声响。我侧耳细听,猜测奶奶是在整理爺爷早年留给她的信件。为了不让奶奶察觉,我熄了灯,借着手机的微光从墙缝看过去,果然不错。
今夜,无灯寂静的深夜,无声漂浮的夜色之海上,奶奶看得见那些信吗?看得见过去那些莺飞草长的日子吗?看得见那字里行间涌动的情感波涛吗?窸窸窣窣,窸窸窣窣的响声,在黑沉沉的漫漫长夜里,是那样的近,又是那样的远……
小时候,奶奶说我胆子像老鼠,要历练!不历练怎么行?你一生要走的路长得很,还要走山路和夜路呢?
我第一次一个人走夜路,是在上初中那一年。中学离家很远,6里路有4里山路,山路的一边是岩坎,几丈多深,看一眼,令人不寒而栗。每天5点起床,天刚蒙蒙亮就出发了。我们村子里3个人结伴,大人们把我们送到山那边。乡里的中学放学早,下午3点,我们3个人蹦蹦跳跳走在回家的路上了。
可是有一天我参加学校的地区数学选拔赛,村子里另外两个人没有资格参加,他们那天不用上学。那天早晨,奶奶特意为我打了两个荷包蛋,还有一个肥肥的大鸡腿。我吃了饭早早出发,奶奶一直把我送到了山那边。下午正式考试,题目很多,考试时间3个小时。但看看其他同学一个个咬着笔头,我还是觉得胜券在握。我以往总是早早交卷,落下一些遗憾。这回我吸取了教训,一直检查到交卷钟响,才满意地踏出教室。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很是得意。满山的野杜鹃竞相盛开着,远远看去如花的海洋。我奔走在花丛中,想象自己也成了万千蝴蝶中的一只,从一朵花到一朵花,追逐着醉人芳香。
天渐渐暗下来了,我丝毫没有留意。一直暗到头顶时,我才清醒过来。脑袋里嗡的一声:天黑了,我还要回家!我几乎哭出声来:天黑了,我怎么回家?我不知是在问自己,还是在问我的奶奶。但奶奶没有来,我只能一个人回家了……一路上,我几乎边跑边哭,大束大束鲜艳的杜鹃花,被我丢在了地上。
走着走着,走进了山路的深处,夜的黑幕里,我一个人,整个山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满山的鸟雀走兽没有弄出丝毫的声响,只有我的哭音、我轻轻的脚步声,还有我心跳的咚咚声。
我不时地回过头去,怕有人追上我,猛兽、强盗、怪物、厉鬼……反正,此时所有怕人的东西我都想到了。但也就在此刻,我想到了奶奶说过的话。我一遍遍对自己说:生出声响来……我要生出声响来!我开始大声地说话,跟奶奶说、跟妈妈说、跟老师说、跟同学说、自个儿跟自个儿说。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我晓得自己的嘴巴一直在不停地说着;我大声地唱着歌,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唱《丢手绢》,唱《我在马路上捡到一分钱》……我拍胸脯拍得嘭嘭响,浑身长了胆似的;我又把手甩得哗啦啦响,一路狂跑,我的脚拍打着每一寸山路,两脚用力地跺地,啪啪响个不停;我还把手紧紧地握成拳头,握得手心流汗,捏得指骨头一节一节响,我知道我的力量还在……
一路走着,我始终有一个信念:走、走、走,走过去就是家了!家里有奶奶,家里有红彤彤的煤油灯,家里有烤得喷香的红薯。间或还有两个荷包蛋,浮在油汪汪热腾腾的汤碗里。
我走到山那边的大路上,奶奶提着一盏马灯屹立在路口,笑吟吟地看着我。我本该一路狂奔扑向奶奶,却和奶奶距一丈远,远远地站住了,如船桅立在夜色之海上。奶奶打量着我,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东西。
以后,这样的夜路,我走过了很多次。
路走得多了,对于声响,我有了更多的认识和思考。
放眼看看,看看我们的乡村,看看我们的乡民吧。那大碗喝酒的场面,最让人激动的是几只大瓷碗响亮地碰在一起,碰出亲情友爱的火花。就是那爱情胜火的农家小两口,还要时不时摔个锅碗瓢盆响,来为生活添味。一塘死水里,哪个小孩子丢下一颗小石子的声响,立即荡开一片童趣。那春气弥漫时谷种发芽拱出一两片新绿时的声音,还有那斥牛的长鞭在空中噼啪爆响,那都是生命的声音和力量……
你只要见过这样的场面,听过这样的声响,就一定会感到:声响是最动人的旋律,是最令人振奋的力量。是我们的乡村和乡民,是我们的童年,给了我们这样最朴素最本真的哲理。
如果有一天我们听不到令人心动的声响,或者我们已懒得生出一丝声响的时候,无疑,那时我们的乡村正在消逝,消逝的还有给我们温暖让我们怀念的东西。但那些消逝的宝贵的东西只要还留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世界里就不怕有黑夜。
声响,声响。
声响是不败的花朵,绽放在每个人的生命深处,有声有色,多彩多姿。
(《青年文摘》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