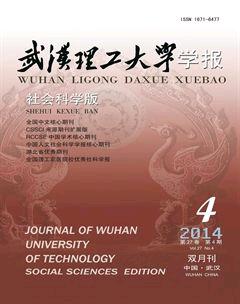阶层分化背景下的农民利益表达
收稿日期:20130701
作者简介:王春娟(1978-),女,河南省洛阳市人,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和中国农村问题研究。
*基金项目: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项目(11YJC810033);2014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20141b016)摘要:农民利益表达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也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热点问题。根据农民与农村、农业生活、生产关系的疏密程度可将其划分为三个大的阶层,即依赖农村型阶层、城乡游离型阶层和“新市民”阶层。由于他们社会关系、社会资源和政治社会态度的分化,引起了利益的分化,从而出现农民利益表达的复杂性。可从以下三方面分析:利益表达意识的摇摆化,农民利益表达主体意识的苏醒和“臣民意识”的纠结;利益表达内容的复杂化,政治性权利的非均衡化与资源性权益的多元化;利益表达方式的不确定化,理性化与非理性化间的徘徊。由此可得出结论:根据农民利益表达的复杂性构建基层民主是新农村建设顺利实施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阶层分化;利益分化;利益表达
中图分类号:D621.5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4.04.016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7卷第4期王春娟:阶层分化背景下的农民利益表达
自古以来我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农民一直是作为一个单一的身份而存在的,农民的“农”性是他们最根本的身份属性,他们与农业、土地的依附关系非常紧密,农业、土地是他们生活的最基本保障,因此他们的利益也随之比较一致,农民一直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中国的20世纪70年代末。
自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发生越来越明显的变动,虽然他们的户籍仍是“农民”,部分农民依然与土地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部分农民的天然“农”性越来越淡薄,部分农民半“农”半“工”,部分农民半“农”半“商”,一些农民甚至与农业、土地完全脱离了关系,因此农民从单一的身份分化为多个不同的阶层,他们的利益也随之发生了分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陆学艺首次提出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标准以后,农民阶层分化的研究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大部分学者研究的重点在于如何划分分化后的农民阶层,对划分的标准进行了诸多探讨,但极少有学者侧重研究农民阶层分化后伴随的利益分化及利益表达,而这个视角的探讨对在当前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如何更有效地深化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改革有不一样的解读和意义。
一、当前农民阶层分化的内容和特征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是社会分层研究的两大视角。马克思认为社会结构因素是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而被西方学界所广泛接受的是韦伯的观点,他认为个人特征禀赋的差异导致资源配置上“量的差别”,因此对于社会不平等,他认为不仅是经济因素,政治和社会因素都是社会不平等的源泉,因此个人的财富、声望、权力是考察社会分层的三个维度\[1\]。韦伯的观点对中国学者的影响也很大,目前关于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标准主要是农民的职业、身份、收入、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
目前在中国学界最有影响的当属陆学艺的分层标准,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按照职业不同,把中国农民划分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农村管理者阶层八个阶层\[2\]。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村和农民进一步发生了变化,他的分层标准已不太适合农村当前的社会现实,比如雇工阶层不再有实质意义,但就以后大部分学者的分类研究来看,基本上都是大体沿袭他的思路框架。其他比如按照收入、消费、社会资源等标准研究也有不少,但整体来看,以职业为分层基础的研究得到最大多数人的认同。
本文所采用的标准也主要是职业、身份等,但对此前分类标准进行简化和重组。因为农民分化具有不完全性,边界也不易确定,并且会出现“阶层回流”的现象,一部分群体会经常变动职业,身份频繁转化或兼任几种身份,因此纯粹依靠职业来划分不易于厘清本文要阐述的问题,因此本文根据农民是否长期居住农村,与农业、土地的关系、利益的密疏程度来划分不同的阶层和他们的特征,藉此分析阶层分化背景下的农民利益分化和不同的利益表达。
(一)依赖农村型阶层
这部分群体长期居住农村,生产和生活依赖农村,大多数属于农业劳动者的阶层(在以职业为分层标准的研究中),这部分群体主要居住在农村,从事农林牧渔等生产和经营活动。农业、土地等传统的农业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源对他们关系甚密,这个群体是农民其他阶层的母体。在目前社会情况下,这部分群体的特征大多是:文化程度较低;除农业外欠缺一技之长;年龄偏大;家庭妇女;老弱病残等。当然,也有少数文化水平较高、头脑灵活的养殖种植大户。除此群体之外,还有文化水平较高、素质较高的乡村知识分子阶层和村务管理者阶层以及极少量的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比如居住在农村的民办教师、乡村医生、村干部、乡镇企业经营者(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普遍萎缩,这个阶层数量越来越少)等。由于这部分群体的生产、生活主要依赖于农业、土地,因此他们对农村的基础生产设施、农村公共物品、农村的村风村貌等农村发展问题较为关心。
(二)城乡游离型阶层
这部分群体是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穿梭的夹心层。在当前农村中最为常见,主要是农民工阶层、半农半商的农村小商人阶层。这部分群体主要指既没安心在农村务农、生活,又没有在城市中寻找到归宿的农民,他们农忙时务农,农闲时打工或做小生意,或家庭成员进行劳动分工,部分务农部分打工或做小生意。在市场化的今天,这部分群体成员甚多,他们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对城市和农村都有依赖,但又都不能完全视其为自己唯一的生活和心理保障,成为介于农村和城市的“两栖人”,这也是“农民工”群体中的一部分。这个群体的特征是对农村有一定的依赖,由于对城市生活缺乏安全感,因此对农村心理上的依赖更大于其物质上的依赖,把农村作为其可退可进的最后一道屏障。这部分人的生活、心理状态决定了他们对农村仍有一定的感情,对农村的发展尽管仍有一定的关心,但由于打工或经商在外,很多时候表现不明显。
(三)“新市民”型阶层
这个群体是脱离农村生活的“新市民”阶层。主要指举家迁往城市进行生活的阶层,他们或者常年打工,或者长期在外经商,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城市立足,几乎完全脱离了农村生活,正处于“市民化”的状态,这个群体在大部分学者和媒体的视野中被称为“农民工”,近年更是成为热门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的难点。这部分群体近几年呈扩大之势,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南方农村,这个群体更为庞大。这部分群体大部分在城市买房或租房长期定居,他们的生活已完全被城市所支配,他们都已完全不从事农业生产,把自己的田地非常廉价甚至无偿转让给其他村民,或者抛荒。他们的后代甚至不认为自己是农民,因为他们出生和成长在城市,他们与农村渐行渐远,除了户籍仍是“农民”外,他们的经济依赖、生活方式、政治社会心理等都已几乎完全脱离农村,是一个新兴的“市民”阶层。
二、阶层分化背景下的农民利益分化
分化后的农民因为具有“农”的身份,一些共同的价值观、政治意识和心理、生活方式等,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属于“农民”这个大群体,但农民的阶层分化导致农民社会关系、社会资源、政治态度的不同,引起农村利益主体和利益来源多元化\[3\],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农民阶层分化就是农民利益的分化。
(一)社会关系的分化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主要指血源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等社会关系系统。血源关系指以血亲或生理联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种族、氏族、宗族、家族、家庭等都是以其为结点形成的群体;地缘关系是指直接建立在人们空间与地理位置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关系;业缘关系指以社会分工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它是在血缘与地缘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当前农民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农民的社会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分化。以前农民由于户籍制度和就业生存条件等因素都居住在农村,有共同的活动空间,家族、亲戚等分布在周围错综复杂,又均靠农村等农业生产维持生活,因此他们有盘根错接的血源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但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这种多年以来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对于依然长期居住在农村,主要依赖农业、土地的农民群体,他们的社会关系主要依然在农村,社交网络有限。而其中的纯农业劳动者更是社交面狭窄,少数的种植大户、养殖大户群体以及乡镇企业管理者,由于其依赖一些现代的经营销售方式,因此尽管血源关系和地缘关系与个体分散的纯农业劳动者相同,但业缘关系更为广泛。对于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穿梭的“夹心层”,因为其居住场所的定期或不定期迁徙、职业身份的频繁变更,因此他们尽管血缘关系主要在农村,但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发生了很大变更,社交网络大且复杂。而对于脱离农村生活的“新市民”阶层,部分血缘关系仍在农村,但已在城市开始新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则已完全在城市。
(二)社会资源的分化
毛丹从社会资源的角度研究农民的阶层分化,他认为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和象征性资源。根据他的分析,经济资源指获得经济报酬的能力,象征性资源指如身份地位、社会关系、知识、权力等所有潜在和现有的能够对自己或别人的生存、发展机会产生影响的资源\[4\]。在借鉴毛丹等人研究基础上,本文把土地、林业、水产等农业生产要素也纳入经济资源的范畴(毛丹等人忽视了土地等传统农业资源),因为本文主要从农民与土地等农业生产的关系为划分标准来分析,何况土地本身也是农业阶层一个最根本的资源。
对于长期居住在农村的农民阶层来说,他们的经济资源普遍不强,比如农业劳动者阶层,由于农业小规模经营的效益有限,土地的产出不能支撑他们变得更为富裕,而对规模经营的种植大户和养殖大户及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产出较高,经济资源较强,但随时面临着未知的市场风险,乡村医生、教师等阶层收入较为稳定,但收入有限。尽管他们知识稍高,但其在农村的身份地位、权力、对农村公共事务的影响等方面与普通农民并无太大差别,因此象征性资源也有限。而对完全从事农业劳动的乡村管理者来说,他们的经济资源并无优势,但在身份地位和政治权力等象征性资源方面拥有传统的优势。对于“夹心层”,因为他们的半工半农或半工半商,因此他们的经济资源与纯粹依赖农业的农村劳动者阶层相比,更具有优势,另外打工或经商的生活会大大开阔他们的知识面和视野,社交网络也更为超社区性,因此具备比纯农业劳动者群体更多的象征性资源。而对完全居住在城市的“新市民”阶层,他们的经济资源参差不齐,但大部分经济能力尚可才在城市定居,由于长期居住和生活在城市,知识面较广,但又限制于他们的“农民”户籍,因此他们身份地位处于尴尬的、不明朗的状态。
(三)政治社会态度的分化
由于农民各阶层对农村依赖程度的不同,社会关系、社会资源的不同,因此影响到他们对政治社会态度的不同。根据杨华的分析,具体表现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农村公共事务、农村政策和制度安排等方面不同的倾向、主张和诉求\[3\]。贺雪峰经过调查发现,因为阶层的分化导致农民利益的分化,因此他们对土地的态度、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需求的热情程度有很大不同,政治社会参与程度也随之相异\[5\]。
对于依然长期居住在农村社区,依赖农业、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源的阶层来说,他们通常比较关心农村社区的基层民主制度,而农村的公共事务、农村政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更是与他们的生活、生产紧密相关,涉及到切身利益,他们比其他阶层更为关心,更愿意去投入时间、精力和财力去做这些方面的事情。对生活和生产奔波于农村和城市中间的“夹心层”来说,他们依然关心农村社区的民主政治和农村的公共事务、公共政策等,比如少数经济能力强的“能人”对村干部的选举和担任非常热情并积极参与,农业种植补贴对大部分人仍具备相当的吸引力,但由于他们的经济、生活重心并不全在农村,因此对他们而言,农村只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于是否参与公共事务等,要看是否能给自己带来直接的实惠或者是否有时间参与。而对脱离农村生活的“新市民”阶层而言,他们由于经济和生活重心完全转移到城市,因此只有极少数“经济精英”会出于“光宗耀祖”等各种心理会关心老家农村社区的基层干部选举,对农村公共产品给予一定的经济资助,但绝大部分人对农村的政治社会态度冷漠,他们的关注焦点是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城市,关注自己的就业机会和后代的上学教育等问题。
三、利益分化下的农民利益表达
农民分层不仅仅只是职业的分化,而是更深刻的引起利益的分化,农村原有的资源占有格局占有模式和利益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6\]。相同的群体会形成相似的价值观和利益需求,并且会通过一定的方式表达出来,利益表达是积极的公民权,是公民参与的一种形式,但也是最浅层次的一种。不同的阶层则会有不同的利益需求、表达能力,因此会有不同的利益表达内容和表达方式,但在当前农民阶层分化不完全,各阶层往往会相互转换的情况下,农民的利益表达意识和表达方式会出现不确定化,表达内容和特征也随之表现出复杂化。
(一)利益表达意识的摇摆化:农民利益表达主体意识的苏醒和“臣民意识”的纠结
改革开放后,由于农民社会分层引起的利益分化,农民的“个体”利益意识逐渐增强,对自己的权利有了一定的认识,而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的普遍确立,既是农民利益表达主体意识一定程度上苏醒的标志,同时也为农民民主意识的萌发提供了制度性平台。随着农民整体文化素质水平的提高,外出务工经商人群的扩大,电视、电脑等媒介深入生活,农民接触到的维权案例和路径越来越多,因此改革开放后农民的利益表达意识被逐渐唤醒,对自己的利益尤其是直接的经济利益愈来愈有明确的表达意识。
但农民利益表达意识的苏醒并未完全取代农民心底的“臣民意识”。孟德拉斯说过:“农民在内心深处坚信, 他的土地是独特的……即使在农业劳动者以理性的和经济的方式对待土地资本的时候,他依然对土地保持着深厚的情感,在内心把土地和他的家庭以及职业视为一体,也就是把土地和他自己视为一体。”\[7\]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农民长期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基于这种生存理性,因此对权威的依附心理严重。“皇权意识”几乎一直弥漫在乡村,他们习惯了被游离于政治之外,政治态度冷漠,而对于维护自己的利益,“清官”和“明君”是农民心头萦绕不去的情结,他们仍习惯把维护自己利益的希望寄托于“清官”和“明君”,而不是把自己与官员置于同等的地位——即作为公民去主动诉求自己的利益,现代“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对现在大部分农民而言仍有一定的距离。公民社会是现代公民意识生长和存在的前提,而在当前的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仍处于萌芽之中,大部分人心底仍存在着传统的隶属心理和政治依附心理。
在农民诸阶层中,留守乡村的乡村企业管理者阶层因为其自身经济能力、社会关系、社会资本资源等方面有一定的能力和优势,利益诉求能力和诉求技巧较强,诉求效果较好,因此他们的利益表达意识相对而言较为清晰,但对于农业劳动者阶层而言,由于知识水平普遍较低,社会资源较弱,并且自己的利益范围主要在农村社区,因此传统的政治心理对其影响更大,他们大部分更依赖于传统的方式——即权威型的方式来处理自己在生产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尽管有村民自治制度,但他们仍大多依赖村干部,因此利益表达主体意识较弱。对于经常出去打工或经商的“夹心层”而言,他们中的大多数由于经常外出,见识增长很多,并且社交范围和资源扩大,商品意识和权利意识增强,因此对自己的利益主体地位有一定的认识,但由于其对农村生活或生产依赖有限,因此他们对不是关系自己直接利益的事情大多缺乏热情,再加上居住地点和工作生活变更较为频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他们利益表达的热情。而对脱离农村生活长期生活在城市的“新市民”,在长期的城市生活中,见识和能力大为增加,但因为城乡二元分化的户籍制度,他们的农民身份使他们与城市社区的政治生活人为隔离,话语权处于弱势地位。权利意识的加强和话语权弱势的纠结,使他们的利益表达意识处于摇摆不定之中。
(二)利益表达内容的复杂化:政治性权利的非均衡化与资源性权益的多元化
资源性权益和政治性权利一般是利益表达的主要内容。资源性权益主要是具体的经济资源,政治性权利比较抽象,一般为政治性资格。资源性权益往往是政治过程链条的末端,起点往往是政治权力,由政治权力带来政治权利,最后才影响到直接的利益分配。因此由于利益表达能力和政治社会心理的不同,农民这个大群体里面极少有人去关注位于政治过程顶端的政治权力(这个群体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少数群体关注政治性权利,大部分群体注重的是资源性权益。
1. 政治性权利的非均衡化。在我国,农民比较忽视政治性权利的表达,尽管有学者认为农民的利益表达正从资源性向政治性转化,但笔者并不认同,笔者认为目前农村仍是资源性权益表达为重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是农村最常见的一种政治性权益的利益诉求,但这种表达带有强烈的自上而下的痕迹。有这种权益需求的阶层主要是上文所划阶层的前两个中的部分群体:即长期居住在农村、生活生产依赖农村的农民阶层和部分“夹心层”。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主要包括:建立健全以村党支部、村委会、村民代表会为主体的村级组织体系;建立健全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配套齐全的村级民主管理制度体系;以村级工作运行、干部群众行为和各项制度运作规范为基本内容,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村务运作体系。简单讲,就是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而实际情况并未达到制度设计者初始的预期效果,原因当然很复杂,但相当一部分原因可归咎于政治性权益表达主体——农民的表达意识不强和表达能力有限。持有这部分需求的农民大致为以下几种类型:农村传统权威、农村能人。传统权威主要为农村本社区以前担任过村组干部的农民,农村能人主要为经济能人。大部分劳动者阶层因为文化水平较低、经济水平较低等原因成为农村基层政治的“边缘人”,尽管部分也会参与投票,但往往成为农村能人的配角,乡村教师和乡村医生尽管知识文化水平较高,但一般也被排除在外,“能人治村”尤其是“富人治村”成为当前农村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对于长期在城市生活的农民阶层而言,他们的政治诉求往往难以表达,因此农民的政治性权利呈现非均衡化。
2. 资源性权益的多元化。由于小农意识和长期身份地位的局限性,农民相对忽视政治性权利,更为追求资源性权益,尤其是直接的经济利益。在我国,目前从整体看,资源性权益是广大农民最常见、最关注的利益诉求\[8\]。在农民利益分化的前提下,资源性权益的内容愈来愈多元化,普遍关注的是国家的农村政策、农村公共事务和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等。由于农民阶层的分化,这种资源性权益对于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意义,因此他们有不同的态度。对长期居住在农村的阶层而言,农村公共事务和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有着直接的利益需求,因此对于农村公共事务和农村公共品比如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很大的需求热情,愿意通过实践来参与,并且处理这类事情的结果往往能为积极有效参与者在农村树立一定的声望;对于当前国家对农村的补贴政策,中低收入者更为重视,而对收入较高的乡镇企业管理者尽管仍居住在农村,但对其没有热情。对于“夹心层”而言,因为部分时间不在农村,因此对农村政策、公共品的供给等关心程度一般,而对于脱离农村生活的农民阶层,他们的资源性权益主要侧重在城市,侧重在就业方面的问题,比如工资待遇、医疗教育等。
(三)利益表达方式的不确定化:理性化与非理性化间的徘徊
目前农民利益表达的制度内渠道有:乡镇人大代表制度、村民自治组织、信访制度等。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很多既有的利益表达渠道“有名无实”,比如乡镇人大代表基本上是由乡镇基层干部和经济能力强的乡村精英组成,由于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自利的经济人,政府官员亦不例外,因此这些代表很难真正代表最普通劳动阶层的利益。而一度被学者和媒体炒得很热的村民自治制度这几年似乎也进入了尴尬境地,在目前“乡政村治”的模式下,自治效果有限,似乎难以达到制度设计者的预期目的。而信访制度由于信访部门不被重视,权力有限,办公人员缺少等因素更是失去了制度设计之初的预期效果,信访往往演变成“上访”和“闹事”。随着农民阶层分化的加剧,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和缺失越来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仅仅依赖制度内的理性化的利益表达方式似乎难以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阿尔蒙德认为:“坚持持续不断的利益表达,其耗费量是很大的,勉强能维持生计的集团和个人可能无力承担……在贫富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的社会里,正规的利益表达渠道很可能是由富人掌握的,而穷人要么是保持沉默,要么是时而采取暴力的或激进的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9\]229230由于制度内的利益表达渠道有限,农民在诉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会采取他们自认为最直接有效的利益表达方式。利益表达的关键是有关行动者能够获得进行表达的渠道或途径 \[10\]。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弱势农民通常采取非理性的表达方式,比如大规模静坐、抗议等,以此集体形式公开表达利益诉求,不仅是一种权利救济形式,而且已经成为公民集体特别是弱势人群的一种生存手段,更是社会多元博弈和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 \[11\]。
在“富人治村”几乎成为当前农村普遍趋势的情况下,在留守农村的阶层中,乡镇企业管理者等农村精英尤其是经济精英往往取得了农村话语权和表达权,因此他们的利益表达方式往往倾向于理性化的表达,比如通过乡镇人大代表、村民自治委员会等途径和渠道。而对于农村劳动者阶层而言,自己的利益范围主要在农村,乡镇人大代表的选举和村干部的选举对于自己有一定的意义,但多数情况下处于旁观者的角色。在农业税时期,尤其是90年代,由于农业税费负担的沉重,农村基层干部和村民之间矛盾严重,因此农民非理性的表达较多,比如农村大量土地抛荒、上访、甚至围攻基层政府。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又实行了种粮补贴等惠农措施,对长期依赖农业生产或农村的农业劳动者阶层来说,国家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信心和希望,因此尽管这部分农民并未充分分享到村民自治的成果,但能给他们带来相对平静安稳的日常生活,因此除个别极端案例以外,他们也倾向于温和、理性的利益表达方式。而对于“夹心层”和“新市民”阶层而言,他们由于在城市打工或经商,他们的利益范围早已超越了相对封闭的农村社区,在城市身份地位的尴尬和从事工作岗位的底层,使他们在政治上处于草根的地位,而农民分散性的传统,形成农民个体化、原子化的特征,缺乏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组织,而个体的利益表达和政治效能显然非常有限,因此一些农民工经常因为讨薪而采取极端的非理性化的表达方式,美国学者阿尔蒙德曾指出:“那些本身不具有影响决策者的途径和资源的集团,只能使用争取同情和支持的非常规手段。”\[12\]216因此越级“上访”,抗议、自杀等方式成为他们主要的非理性化表达方式,“上访”其实就是农民长期以来寄希望于“清官”的政治依附心理的反映。而有些农民在城市目睹一些维权事件后,发现了媒体在利益表达中的独特作用,因此一些农民通过“自杀”等极端非理性化方式,通过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来达到自己的利益诉求。
总之,随着农村社会的分化,旧有的资源分配体制、组织体制等发生了消解,而新的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缺乏与当前社会现实相匹配的利益表达方式,因此农民在利益表达时没有确定的有效方式,不得不根据实际需要在理性和非理化之中徘徊抉择。
四、结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的人口流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将继续蔓延,中国农民这个以前传统社会中单一的身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两千多年以来他们与农村、土地的依赖的关系也随之发生质的改变,职业的分化将更加频繁和多维度化,利益的分化是他们阶层分化最核心的体现,利益表达内容和方式呈现复杂性的趋势。
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农村社区建设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但农村社区建设不仅仅是简单的把城市社区管理的一套规则直接套用在新农村建设中,而是要结合当前农村出现的变化即农民的阶层分化来研究,要符合当前农民利益分化和社会需求的变化,需要新的社会管理机制来协调。因此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强化农民的公民责任,激发农民的利益表达意识,摆脱心底的“臣民”意识是构建农村公民社会的基础;资源性权益和政治性权力相平衡是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的目标所在;而制度内的理性化的利益表达方式是保障这种自治目标顺利实现的必要手段。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龙婧,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2\]陆学艺,张厚义.农民的分化、问题及其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1990(1):1621.
\[3\]杨华.农民阶层分化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新挑战\[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1(6):4045.
\[4\]毛丹,任强.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几个问题\[J\].浙江社会科学,2003(3):9098.
\[5\]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6\]孔繁金.农村阶层分化后农民诉求表达的新变化及对策分析\[J\].理论探讨,2009(1)912.
\[7\]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 \].李培林,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541.
\[8\]杨友国.现阶段我国农民利益表达的特征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2432.
\[9\]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0\]胡伟.政府过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193.
\[11\]许章润.多元社会利益的正当性与表达的合法化:关于“群体性事件”的一种宪政主义的法权解决思路\[J\].清华大学学报,2008(4):113119.
(责任编辑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