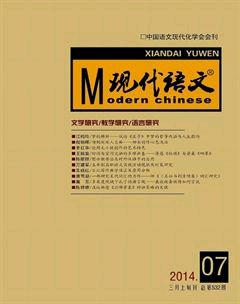梦的解析
摘 要:《庄子》一书中的“梦”有着丰富的内涵,揭示出庄子的人生哲学。庄子擅长于虚构梦境,借助托梦者的神秘与权威说理。庄子在作品中的梦觉观表现出了其对人生的迷惘及对“人生如梦”的悲哀,而齐物精神的阐发对处理物我关系意义非凡。庄子通过对“其梦不寝”的真人塑造,折射出在物欲横流之社会保持理智清醒眼光的必要。
关键词:梦的虚构性 悲剧内蕴 齐物 情意妄想
《庄子》一书中的“梦”一直备受关注,庄子被认为是“梦象艺术”的开创者,是“以梦为文”[1]的大师。尤其是“庄周梦蝶”这一哲学问题,蕴含了庄子诗化哲学的精髓。从美学及文学艺术的角度去理解庄子是十分必要的,但尤不可忘的是庄子与其他诸子一样,其哲学亦用来观照人生。《庄子》三十三篇中,有九篇十一处提到了梦,笔者认为,庄子笔下“梦”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它虽没有完全摆脱上古巫觋文化的影响,但已经被庄子改造成了其哲学体系中的一个层面,包含着复杂的哲理和庄子对人生的思考及感慨。
一、梦的呈现:梦的虚构性与揭示性
庄子之梦承袭并突破了前人描摹梦时的梦魂宗教崇拜之神学性思维模式,将虚构的梦纳入作品,借梦象释理抒情,跨越了哲学常规的逻辑说理方式。[2]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在一些作品中看到梦魂宗教崇拜的印记。如:
于是旦而属之大夫曰:“昔者寡人梦见良人,黑色而髯,乘驳马而偏朱蹄,号曰:‘寓而政于臧丈人,庶几乎民有瘳乎!”(《田子方》)[3]
其父梦之曰:“使而子为墨者,予也,阖胡尝视其良,既为秋柏之实矣?”(《列御寇》)[4]
第一则是写文王虚构梦境假借先君之意启用臧地老者,是利用梦的神圣以服众。与《人间世》里栎社托梦于匠人道出处世之哲学一样,梦中栎社的娓娓道来依旧透着神秘与权威,客观上增强了说理,而梦的崇拜被利用本身就是对其神圣性的消解。第二则是庄子虚构梦境以阐述顺应自然本性之道理。缓身为儒者,恨其父站在墨家一方,竟然愤恨自杀。缓的行为不但得不到父亲的理解和愧疚,反而遭到了父亲在梦中的反驳,这样既消解了其抗争的意义,也加剧了其生命的悲剧性。缓的行为是固执己见的极端,庄子在这里也作出了讽刺,认为即便是成为“秋柏之实”,也是个体自由的选择。笔者认为,个人为所执而献身本无可厚非,而这种带着极端狭隘思想并严重干扰他人的所谓的“为道而死”,为庄子所反感。庄子在积极追求自由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对他人权利的理解和尊重,对思想“强权”的抨击和反抗,体现出其思想的包容和独立,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却是一种超越。
上述可知,庄子用构梦手段进行说理,借助了托梦者之神秘与权威,而托梦者之权威在客观被消解的同时,也为庄子主观所质疑,如下:
宋元君夜半而梦人被发窥阿门,曰:“予自宰路之渊,予为清江使河伯之所,渔者余且得予。”元君觉,使人占之,曰:“此神龟也。”君曰:“渔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会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渔何得?”对曰:“且之网得白龟焉,其圆五尺。”君曰:“献若之龟。”龟至,君再欲杀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杀龟以卜吉。”乃刳龟,七十二钻而无遗。仲尼曰:“神龟能见梦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网;知能七十二钻而无遗?不能避刳肠之患。”(《外物》)[5]
在这里,庄子用神龟的故事完成了一次精彩的“小大之辩”。以神龟能托梦、能知人所不知的神力,依旧无法逃脱被网而被杀的命运,揭示即便是知者也可能在残酷的现实中被杀害。网住神龟的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渔者”,他甚至没有掌握自己所捕之物的权力,只得听命上交。神龟的实际命运还是掌握在宋元君的手中,君“再欲杀之,再欲活之”,死生只在君王一念之间,何其悲哀!可是最终使得君王痛下杀手的,竟然是因为占卜得到杀之而吉的结果。而神龟死后,再被用来占卜,结果居然分毫不差。这样“以卜杀卜”,相残相杀,最终不禁让人陷入了迷惘:造成神龟之死的究竟是谁?
依照后文所叙“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6],神龟似乎是死于它的“有用”,它的神力无法预见自己被捕的命运,无法预见被人决定死生的场景,更无法预见最终死于预见的结局。庄子告诉我们,神龟死于无法预见自己死于预见!是它自己杀死了自己。这似乎有陷入诡辩的嫌疑,但逻辑上却又合理。笔者认为,依庄子看来,神龟“有用”上的疏漏或不及造成它的死亡,完全就是“无用”的,明白了这些以后,才可以讨论真正的“有用”。如何防患于未然,如何明哲保身,如何处理“小大关系”,这些人生哲学才是庄子要告诉我们的,无论智慧到达多么高的境界,都要始终铭记,个体所掌握的技能和本领,事实上是最有可能给个体本身带来麻烦的。不为自身所累,不求名居名,跳脱出来审视人生,这才是更加高明的境界。
二、人生如梦:梦的悲剧内蕴和齐物精神
前文“缓之自杀”与“神龟之死”,都是悲剧性的故事。当庄子将梦幻与现实连通,以“梦”与“觉”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就陷入了人生的迷惘之中。“庄周梦蝶”也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
“梦”与“现实”究竟如何区分,是一个高深的哲学问题。弗洛伊德用科学的方法解释梦境,认为梦里所出现的现象都来源于过往的经验。弗氏在揭开人类心理隐私的同时,证明梦境并非荒诞不经,而是有迹可循的。梦可以是非常真实的,它是人意识的另一个侧面。庄子也认为梦是魂交的现象,是个体意识的活动。当人处梦中时,觉得一切都明白如真,而梦醒之后却又是另一番境地,这其中的差距不禁令人对所处环境产生怀疑,究竟眼前所看到的是“真实”,还是另一场梦境?这种对真实的怀疑必然招致对“不觉”的悲哀,对个体无法掌控自身命运感到无奈和迷惘。郭公民先生指出:“庄子对存在的逼问,目的就在于确立一种合乎自然的健全人格,而现实中却是人的天性为‘异化社会的臧贼……‘异化现象中体现出的历史必然与庄周要求重建合乎自然的伦理和发展健全人格都有其合理性,但二者却产生黑格尔所说的悲剧冲突,而且庄子的‘绝圣弃智‘返本归真,在历史进程中明显是不合时宜的,注定要为历史洪流所吞没。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社会中,面对强大的历史必然,庄子就意识到了自己对于‘天命的无力和无奈,这种醒意识也成为其悲剧的根源。”[7]郭先生认为庄子悲剧的根源在于庄子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合时宜”终将被历史的洪流所吞没,这种认识是非常具有史家眼光的。
但是笔者认为,这并非是庄子悲剧的根源。庄子固然有不合时宜的一面,有对自己人生的感慨和悲悯,但更多的是对处于“大梦”中的整个人类的悲悯。
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齐物论》)[8]
“梦之中又占其梦焉”,庄子陷入了梦与觉无限循环的苦恼之中。对现实判断的无力感让人觉得,倘若这是梦,那么梦中的哭与笑岂不是没有任何意义?这是何其悲哀!“不觉者”还被梦里的一切所左右,“觉者”本身又在一个梦里,是以没有永远的“觉者”,只有相对的“觉者”。放到无限的空间与时间里,短暂的人生充满了欢喜忧愁,在后人看来,岂不就是一场梦?而后人自觉清醒,不过也被后人之后人看做是一场梦罢了。庄子知道自己并非“独醒者”,“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他自知自己也与众人一样,处在一梦之中。人类的苦难和欢乐,不过就是一场梦啊,如何才能大觉?这样的终极问题,庄子认为“万世之后而遇大圣知其解者”,而这种大圣,只能“旦暮遇之”。庄子在对“梦”与“觉”这个问题的思考过程中,充满了“人生如梦”的悲哀及对“梦中人”的叹息与悲悯。我们再来看“庄周梦蝶”: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齐物论》)[9]
当庄周为蝶时,全身心为蝶,不知有周,但当庄周醒来时,他是庄周。则同理可得,蝴蝶梦为庄周,则蘧蘧然周也,不知蝶也。俄而觉,则栩栩然蝴蝶也。到底是庄周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庄周?现在蘧蘧然的庄周,会不会是栩栩然蝴蝶的梦呢?庄子自己也分不清何为周,何为蝶!但是庄子又很坚定地认为,周与蝴蝶绝对有明确的界限,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正如陈鼓应先生所言:“在庄子看来,宇宙间一切物象,生意盎然,各呈其能。然而个体存在显现出无比的差异性、对立性,又如何相互汇通融合呢?因而阐扬个体生命价值的同时,个体间的相互交会互为主体,是庄子进一步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他提出古典哲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道通为一。”[10]齐物是齐不齐之物,世间之物尽管千差万别,但在本质上是相融相通的。蝴蝶与庄周隐含着蝴蝶可能是庄周、庄周也可能就是蝴蝶之意味,亦透露出看待自我生命、看待外物的倾向,那就是“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11],当你梦为鸟,你就自然在天上飞,你梦为鱼就自然在水中游,完全投入做好现在,“自喻适志”,就能体会到自在之快乐。而对于非我之存在,依庄子之意,“非我”之存在完全可能是“我”之存在的另一种方式,和“本我”可能有千丝万缕之关系。道本相通,物本相连,对待外物应该是理解、尊重、宽容、同情。
三、其寝不梦——摆脱情意妄想的理想生存方式
无论是构梦以阐发哲理,还是用“梦”与“觉”表现出人生之悲哀及迷惘,都体现出了庄子对梦的认识和看法。但庄子并未就此止步,梦若是人生一场幻象,要遇万世之后一大圣方能解之,那么,怎样的“大圣”才能摆脱梦的困扰?这又与庄子笔下的“真人”“神人”联系起来了。如下:
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大宗师》)[12]
庄子在此描绘的“真人”,是睡觉不会做梦,醒来也没有忧虑的。成玄英对此的解释是:“梦者,情意妄想也。而真人无情虑,绝思想,故虽寝寐,寂泊而不梦,以至觉悟,常适而无忧。”[13]庄子认为人生如梦,人处在其中而不自觉,梦与各种人类情感及欲望相连,给人带来了无尽的忧愁烦恼。成玄英把梦解释成情意妄想,认为真人不被任何幻象所迷惑,也没有任何欲望,故而能够超脱于世。真人与庄子笔下“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14]的神人一样,已经进入“无待”的逍遥境界了。不管是“真人”“神人”,他们已完全摆脱了人世的困扰,生存方式已经与众人完全不一样了。只有通过“心斋”“坐忘”等方式,让心灵虚静澄净,沟通天人,随物宛转,方能达到无可无不可的境地。
由此可见,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环境中,庄子的心胸是十分豁达的,他对精神世界的看重和追求,是带着彻底摒弃欲望与物质的极端决心的。这在现实故难以实现,但其人生指向却是非常清晰的。庄子认为“耆欲深者,其天机浅”,越是纵容自己的欲望,越是智慧浅薄,越是执迷,越无法看清外界,才会被种种的情绪所牵制,这即是向外界传达克制“深欲”的生存方式。众人虽难以达到“其寝不梦”的高深境界,但在生活中,保持理智,坚持适度原则,亦能不被欲望迷失双眼。
注释:
[1]张兰花,白本松:《庄子是中国“梦想艺术”的创始人》,中州学刊,2005年,第4期。
[2]陆建华:《庄子梦之解析》,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3][战国]庄子撰,[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南华真经注疏》下册卷七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12—413页。
[4][战国]庄子撰,[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南华真经注疏》下册卷十杂篇《列御寇第三十二》,第592页。
[5][6][战国]庄子撰,[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南华真经注疏》上册卷九杂篇《外物第二十六》,第529页,第530页。
[7]郭公民:《庄周梦蝶的悲剧内涵与哲学指归》,《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8][9][战国]庄子撰,[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战国]庄子撰,[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南华真经注疏》上册卷一内篇《齐物论第二》,第52—53页,第58页。
[10]陈鼓应:《中国哲学中的道家精神》,第16界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主题演讲稿,2009年。
[11][12][13][战国]庄子撰,[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南华真经注疏》上册卷三内篇《大宗师第六》,第160页,第137页。
[14][战国]庄子撰,[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南华真经注疏》上册卷一《逍遥游第一》,第13页。
参考文献:
[1][战国]庄子,[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南华真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弗洛伊德著,罗生译.梦的解析[M].上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
[3]张兰花,白本松.庄子是“梦象艺术”的创始人[J].中州学刊,2005,(2).
[4]郭公民.庄周梦蝶的悲剧内涵与哲学指归[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1).
[5]陆建华.庄子梦之解析[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2,(2).
(江梅玲 北京语言大学 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