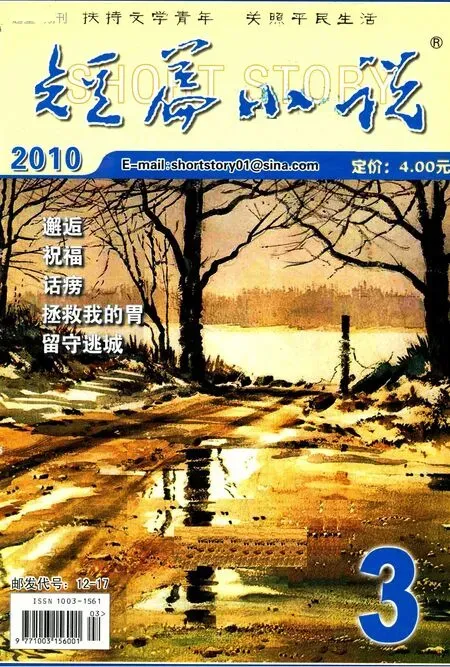怀念一个逃亡的凶手
◎尔 碧
怀念一个逃亡的凶手
◎尔 碧

那时候我们也就十来岁吧。
廷瑞的脑袋里似乎装着怎么也用不完的点子。通常是在我们腻烦了一种活动,坐在略微发烫的铁轨上,一手毫无目的地扔着石子,看着湖面上挖泥船拖着的长长的蛇阵,或者仰头望着山脊上的某个褶皱里腾起的道道烟柱——向往而又沮丧的时候,廷瑞黑葡萄似的眼珠子骨碌一转,我们很快又陶醉在另一种乐趣之中。
廷瑞生得黑,个头没我高,身体却特结实,咋摔都摔不坏。脑袋圆溜溜的,眼神又狠又亮,大人都叫他猫头鹰。不像我,细胳膊细腿子,麻竿似的。他家住在生产队牛圈的隔壁,是一间又黑又窄的石头屋。门前一棵石榴树,长得和我一样瘦弱。吃过晚饭,我们一般大的孩子都会准时到他家会合。廷瑞的妈也黑,脾气却不坏,嗓门大,通常都是乐呵呵的,那么多孩子老往家里塞,她也不恼,时不时还给我们哼一段花灯戏。不像我父母,成天愁眉苦脸精疲力尽的样子。偶尔,廷瑞妈会悄悄地塞给我一把煮熟的饲料,悄声嘱咐我千万别跟人说。她热乎乎的口气拂过我的耳畔,那种温暖的感觉连同饲料的喷香,愈发增添了我对廷瑞的依赖。
可惜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似乎是一夜之间,村里大人小孩一下子就忙碌起来。大人们几乎都是天不亮就下地,月亮出来才回家。原来散落在田间地头、坡顶沟壑的苞谷秸,现在一放学就有孩子们争着拾捡。有人从山上背柴,起初是些荆棘、树枝,后来就见白花花的被解剖成段的树身。很多人家门前的柴堆码得高高的。家家都养了猪。廷瑞也带着他弟弟廷航,拖着耙子,脱光了衣服到湖里捞水刺,湿漉漉的一大篮一大篮地往家里背,获得大人们啧啧的赞叹。
我父亲终于忍不住了。他把一个和我差不多高的背篓扔在我面前,一边吸着水烟筒,一边板着面孔说,你看人家猫头鹰,和你一样年纪,都能顶一个大人了,就你只晓得吃闲饭。从今天起,每天不给老子背点东西回来,你就到猪圈里跟猪一起嗷嗷叫!
我就去找廷瑞。廷瑞和廷航正围着炉子烤洋芋,昏暗的石屋里弥漫着洋芋半熟的浓香。廷瑞妈正坐在一个草墩子上剁水刺,嘴里咿咿呀呀地哼着不知什么调子,粗壮的手臂挥舞着一把宽厚的菜刀,发出咚咚的很有节奏的声响。她身后灶台上的那口大黑锅堆得满满的。廷瑞爹撅着屁股,伏在磨石上,霍霍地磨着镰刀。猪慵懒的哼哼声从裸露的石头墙缝里断断续续地传过来。
再瞎哼哼老娘就宰了你!廷瑞妈咳嗽一声,朝墙缝里骂了一句,那些猪果然就安静下来。
小三子,你家养了几头啊?廷瑞妈的笑容叠在又黑又胖的脸颊上,手中的菜刀又舞了起来。
我接过廷瑞递过来的洋芋,刚咬了一口,牙龈被烫得生疼。我低下头说,两头小的。
我的声音还没完全落地,廷航就响亮地接上了:我家养了五头!过年杀一头,卖一头!
廷瑞妈又唱了起来。这回我听明白了,她唱的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廷瑞扯开嗓门喊,爹,顺便把砍刀也给我磨快了!我们就在廷瑞妈像水波一样涌动的歌唱声中决定了去砍柴的事。
第二天,我们每人往背篓里塞了十个洋芋,天蒙蒙亮就出发了。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山脚,山地荆丛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矮小的松树。沿着灌木丛中的一条崎岖小路高一脚低一脚地往上攀爬。抬起头,已经看不到山顶了。离我们头上不远的地方,山的肚子已经被人们炸开了,露出大片大片突兀的新鲜的岩石。有马车和蹦蹦车顺着山脚新开辟的大路搬运石料。
你说红军真的爬过这座山吗?
廷瑞似乎没有听见我的话,却一本正经地问了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你说山上有没有宝藏?
傅屯村正后方的山体,石头多,灌木多;往南几里,也就是我们要去的小白崖,树木多,杂草多。此外,顶多也就有野兔、松鼠、穿山甲之类的小动物罢了。难道真有什么神秘的山洞,藏着古代留下来的金银财宝?看他那副完全不像开玩笑的神情,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这样的人也会异想天开啊。
一个钟头后到达小白崖。虽然村庄、大地、湖、烟囱以及城市密集的楼房,都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然而我们其实还在山脚。我们只不过是上了一个又一个的坡面,真正触摸到了山的脚背而已,但这足以让我敞开襟怀情意飞扬了。金色的阳光透过云层洒下一道道光束,鸟儿在树梢上在荆丛里啁啾跳跃。偶然间,灰白的野兔拖着尾巴一闪,隐到丛林中不见了。仰头望过去,满目青翠,飞瀑流泉。从白云深处的人家,到我们身边的缓坡,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全是挺拔、奇秀的松树,夹杂着葱翠葳蕤的灌木。山风吹过,涛声阵阵,空气中流淌着松脂和草木混合着的清香。
我和廷瑞扔下背篓,立刻变成了南天门的马儿,变成了水帘洞的猴子。廷瑞爬上一棵松松,欢叫着劈下几根肥硕的树枝,那枝条上缀着一个个饱满油亮的松包,像黑色的菠萝。廷瑞说,等我们把柴砍够了,找一堆干柴,把这些松包和洋芋一起架在柴火上烧,烧得皮开肉绽,白胖胖的松子就露出来了。我的舌头禁不住咂了几下,舌底像泉眼似的洇出一汪一汪的口水来。
廷瑞说磨刀不误砍柴工。他提着亮闪闪的砍刀,专砍松树上壮实的枝丫,然后再修掉那些细枝末节。没用多久,他的背篓就像塞满了一枚枚火箭炮。我只带了把镰刀,又不敢爬树,只能站在地上——用廷瑞的话说,给松树理发。尽管如此,我的脸还是多次被细细的枝条弹得火辣辣地疼。廷瑞说,你干脆吃剩饭吧。茂密的树林里,像廷瑞那样修剪下来扔掉不要的枝条这儿一簇,那儿一堆,有的还晒干了,比我的胳膊粗。剩饭就剩饭。我没费什么力气,也把背篓装得鼓鼓的。
我们架起柴火烧洋芋、松包。熊熊的火焰,越烧越高,夹着劈啪炸裂的声响。又黑又浓的烟柱,让我想起了烽火台上的狼烟。我们的心也燃烧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很多年以后,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这个时刻的情形——廷瑞年少而雄勃的心,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点燃,然后渐渐以无法控制的速度燃烧起来的——那声音分明来自小白崖附近的深沟密林之处。咚,咚,空谷回音,沉闷而浑厚,像疲惫的军士在敲击战鼓。
有人砍树!廷瑞拨弄着柴火的手停了下来,鹰眼骨碌转了一下。
有人偷树!我也警觉起来。
廷瑞站到一块青灰色的板岩上,搭眼仰望。
回到火堆旁,他用柴棍拨出一个烧得乌漆麻黑的洋芋,在绵软的草地上搓了几下,洋芋变得黄灿灿的,袅袅地冒着热气。我也学着他的样子搓了一个,那味道委实比家里的炉子烤出来的要美。
廷瑞不紧不慢地蠕动着腮帮,吃了几口,眯着眼,望着我,那神情颇有些悠闲,又有些蔑视:你刚才说啥子,偷树?
嗯!我有些不解地望着他。
你这是哪来的道理?这山上的树,又不是哪家的,咋个能算偷?
我一时想不出话来驳斥他,但又不愿服输,情急之下,我嗫嚅着说就算不是偷,那也不能瞎砍。我的思维还算不慢,一闪念我想起了我们的钱老师。我理直气壮地把钱老师的理论搬了出来。谁知廷瑞却听出一脸黑色的鄙夷,他说我告诉你啊小三子,钱背锅的话要是能信,屎都可以吃!他教我们啥子颗粒归公啊,可去年我亲眼看到他偷队里的苞谷……还有,红军是爬过乌蒙山,但根本就不是我们村子后这一段。钱背锅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钱老师的背有点驼。廷瑞说的未必就真,我也无意去维护钱老师的形象,但有一点我深信不疑——我继续跟廷瑞理论:课本上就是那么写的啊,这总归假不了吧?
烧得焦黑的松包张着嘴巴望着我们。廷瑞很不高兴,黧黑的脸颊透出隐隐的红。这是我第一次和廷瑞唱反调。我有点后悔。廷瑞向来对我都很好的。我刚想缓和一下气氛,嘎吱嘎吱,远处的林子里爆出几声脆响,骨骼断裂似的,接着是扑哧,哗啦,灌木被骤然扑倒、压折的颤音,伴着鸟雀奋翅惊飞。
倒了。廷瑞冷笑一声说,谁也拦不住。
我感觉到心中的某种东西也倒了下来。我看了看周围的树林。它们那么小,最大的也就碗口粗。它们应该和我们一样,正是少年时代。我不敢想象,人们锋利的砍刀、斧头——迟早一天,这些可爱的小树也在劫难逃——那是怎样的疼痛啊!
廷瑞站起身来,甩动手臂。接着他骨碌碌的鹰眼,朝四周巡视。我疑心他在寻找下手的对象,心不仅怦怦跳了起来。幸好,他向我使劲地招手:快来看,快来看!神情诡异,身子猫在一丛榛莽后面。我也猫了过去。
钱背锅穿着铠甲褂,肩膀上扛着一棵笔直的黑黝黝的松树,沿着一条隐秘的小路,凸着背吃力地穿行……
那天晚上,天完全黑下来我们才到家。父亲头一次朝我碗里夹菜,头一次夸我有能耐。确实,廷瑞扔给我的那一背篓像火箭炮一样粗壮、结实的柴禾,把我的两个肩膀都磨破了,我是一路咬着牙忍着火辣辣的剧痛捱到家里的,背篓一落地,好半天都站不起来。可是第二天,得知廷瑞扛回来的是一棵标致的松树,是搭猪圈的上好的料子,父亲连续骂了我十几声“猪头”。我担心他阴骘的眼睛里会钻出一只白骨爪,从我喉咙里伸进去,把头天晚上夹给我的菜掏出来。末了,他叹息一声:养儿如羊,不如养儿如狼。
后来的情形正如廷瑞所言,谁也拦不住。全村男女老少,甚至是邻村的,都疯了似的朝小白崖进发。我想恐怕是因为没人愿意做“猪头”的缘故吧。我也放下一切顾虑,和廷瑞一起加入背篓、麻绳和牛车的行列。只是斧头吃进小树的肉身,肉屑飞溅,我的心还是会疼一下,渐渐也就习以为常了。人们起初还有些偷偷摸摸的意思,后来就光明正大起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山就秃了,全秃了,连那些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树也一棵不剩。再后来,那些长势不错的灌木丛也未能幸免。只剩那白云深处有人家的地方,仍旧林木蓊郁蔚然深秀。据说,彝人手里有火药枪。
廷瑞小学毕业就辍学了,而我遂了母亲的意愿,考进了城里的中学,从此在很大程度上逃离了繁重的没完没了的农活,这使我非常开心。只是和廷瑞的联系少了,心中多少有些怅然。星期天回家来,我总要跑到廷瑞家的小黑屋,却很少看见他。他和他爹在山上开了一个石场。偶尔遇到,比以前更亲热。廷瑞兴致勃勃地给我描绘山上的种种见闻,如何打炮眼,如何装雷管,点燃引线时的刺激与惊险……我原以为廷瑞没能继续上学,会失落、难过的,谁知恰恰相反,廷瑞相当快乐。廷瑞似乎天生就属于土地,属于山川。用他妈的话说,山中也有黄金屋,山中也有颜如玉。
我上初二的那年,十六岁的廷瑞做出了一件震惊傅屯的大事,这件事让傅屯村彻底燃烧起来,并且持续燃烧了很多年。傅屯村自此名声大振,傅屯人自此趾高气扬。我想起了第一次和廷瑞上山砍柴的途中廷瑞问我的那个奇怪的问题。原来山中真是有宝的,真是有黄金屋的。小白崖以北的火塘峰一带,海拔相当于大山的乳房部位,是两座山的交界之处,是放牛的好地方。廷瑞也曾带我爬过,除了泉水较多之外,没什么特别。然而廷瑞却在这里点沙成金。他开建了傅屯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沙场。他的火眼和慧眼,他的胆识和远见,让我们村那些活了几十年的男人们嫉妒、羡慕、羞愧而又蠢蠢欲动。当然也包括我父亲在内。只不过,他不承认自己无能,而是骂我无用,只配给廷瑞去提尿罐。
也就一两年的时间,乌蒙山上出现了七八家沙场。都是学着廷瑞的办法,山上挖一个蓄水池,再倚着山势,凿一道渠,直抵山脚,山脚下挖一个蓄沙池。用炸药轰开山体,将那些夹杂着泥巴的细沙,通过激流冲洗,运送到山脚。泥巴顺流而下,最终注入水库。沙子沉淀于池。这种沙子称为水沙,建筑市场非常抢手。
廷瑞家很快就盖了新房,是那种两层的水泥房子,墙上打了马赛克,地板磨出光亮的好看的图案。据说,他家房子的图纸也是他自己绘制的。所有的这些本事,别说小学,我读到初三,也没学过。廷瑞却能无师自通,真是奇怪。他家这种造型的房子,在我们傅屯村是第一家。暑假里,作业和农活之余,我就到他家玩。真皮沙发摆满了一屋,还请了保姆。廷瑞妈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头发用筷子烫得卷卷的,还抹了发油,时常把身子陷在沙发里,捧着个算盘,噼噼啪啪地拨着珠子,两片嘴唇上下翻飞,一边利索地吐着瓜子壳儿,一边悠闲自得地哼着《渴望》的主题曲。
我家虽然没有沙场,也没有鱼塘,但是日子和父亲的脸色还是好看了许多。有感于家乡的巨大变化,我在学习了通讯这种文体之后,老师让我们写一篇习作。我就写了一篇,谁想被推荐到市报上发表了。这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它的轰动效应不亚于廷瑞发现第一个沙场。村长为此奖励了我五张大团结。至今我还记得那篇通讯的题目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傅屯村勤劳致富奔小康》。
我最终还是跳出了农门,在远离故乡几千里之外的地方谋到了一份教员的工作,成家立业,一样地为生计操劳奔波。最近几年,春节或者暑假,我都尽力回乡省亲。在分享了窖藏的亲情之后,我会不由自主地爬上铁路,试图触摸或者寻找儿时的记忆。然而,目之所及,不禁黯然。
我看到的是故乡的骸骨。
山依旧保持着亘古以来的沉默与凝重,不同的是,它的身体,自乳房以下,是一刀一刀深深浅浅纵横交错的疤痕,沿着山脚几公里的肌肉都被挖空了,形成了痛苦的冤屈的嘴。更远处是一家停产的水泥厂,灰扑扑如楼兰古国的遗址。水库萎缩了,露出大片大片的滩涂。河道被填平,长满荒芜。鱼塘虽然被填回了土,却再也变不成稻田。那些看护鱼塘的破败的小房子,星罗棋布,是故乡的癌。
村庄也寂静了。过去的土房和石头房基本都换成了砖房,挨挨挤挤,参差不齐。村中道路虽然已是水泥浇筑,然而到处流淌着污水。虽然也袅袅着炊烟,但是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在茅厕的矮墙上,我偶然还看到了“专治性病”的“牛皮癣”。
一不小心,遇到了廷瑞妈。
只能是遇到。我不能像小时候那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去她家玩。其实我很想去的。但我真的不能去。我要是去了,对廷瑞妈是否过于残忍?
是在当年生产队的牛圈门口遇到的。这一排红土夯筑而成的房子,土地下放之后卖给了私人。风雨剥蚀,年久失修,如今已破败得不成样子了,椽子、瓦砾早已埋进粪草泥土之中,只剩几堵断壁残垣,随时释放着危险的信号。廷瑞妈就从一间明显修整过的牛圈里摇了出来。她双手端着一口烧得黑乎乎的大锅,锅里冒着热气,因为沉重,腰佝得很低,牙齿紧紧咬合,露出森然的白,腮帮鼓凸,步履蹒跚。我担心那锅会捧不稳忽然掉下来。她艰难地把锅墩在门前的石榴树下,一间低矮的断砖、土基垒成的猪圈门口。直起身,喘气,看见了我。
大婶!我有些不自在地喊了她一声。我不知道自己为啥会不自在。仿佛自己不该见到她,但回避已经来不及了。
廷瑞妈怔了一下,浮肿的眼泡里,两点浑浊的白,缓缓移动。她仍旧留着齐耳短发,却已花白、稀疏,头皮清晰可见。沉睡在味觉深处的某一种气息,忽然被唤醒,我想起来了,是生产队的饲料,干瘪的苞米和发霉的金豆混合烹煮的喷香。
小三子,你回来了!廷瑞妈终于认出了我,笑了一下,声音里仿佛有朽木、尘埃滑落。
当年那个爱说爱唱的廷瑞妈和我们的童年一起消逝了。我们简单地寒暄了几句,纯粹是应付客套。都显得小心翼翼,不愿去触碰一些像玻璃一样扎人却又脆弱不堪的东西。找个借口,惶惶地走开了。转身之时,我才发现了廷瑞的爹,他枯坐在土墙下的一根断木上,衣衫土灰,神情呆滞,仿佛刚从某个人类遗址里钻出来。
廷瑞家的房子,当年他亲自设计、建造的新房,以及那间昏暗狭窄夹杂着牲口哼叫的石头房,很多年前就已变卖了。一屁股两肋巴的债务据说已还得差不多了。如今他的父母得以容身的牛圈,也是邻居无偿提供的。人生无常,世事无常啊。置身傅屯,我心里堵得慌。
我爬上铁路,一列客车刚刚远去。车轮与钢轨的铿锵节奏刹那间回旋起我们的童年。我的目光越过村庄,沿着大山肚子上的某一道灰色的刀疤,缓缓而上,在火塘峰的某个凹口落下来,落在1992年暑假那个奇特、诡异的傍晚。
那一天天上仿佛有十个太阳,到处下着火。那火的身影细如轻烟,在大山的草木荆莽、荒坡乱石间,在密密麻麻的苞谷林里,蒸腾、跳动。站在坡顶上,天地之间如同一个巨大的蒸笼。廷瑞家的工人都撂下铁铲,走出蓄沙池,歪歪扭扭地躲到背阴处不敢出来。山脚下,十几堆沙丘被阳光烤得滋滋作响,水分蒸发,间或发出几声坍塌、陷落的响声。这种酷热,在傅屯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人们都说,老天要收人了。
其时我已上了师范学校。漫长的暑假,我不愿意待在家里看父亲的脸色,也不愿意干繁重的农活,就去找廷瑞,希望能谋个差事,挣几文零花钱。廷瑞叼着一支香烟,瞅了瞅我电线杆似的身子说,我可不敢得罪文曲星啊!
文曲星也要吃饭啊。我说,我要真是文曲星,那你就是财神爷了。财神爷,求你了!我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
廷瑞一副很受用的样子,轻轻吐着烟圈说,我跟我妈商量一下。
商量的结果让我格外开心。挖沙、铲沙、放炮这些工作我无疑是做不了的。廷瑞就安排我做传令兵,执一面小黄旗,衔一枚口哨,往返于山脚、山顶之间,传递开闸、放沙的信息。这个差事完全不必专人负责,任何一个工人都可以兼任。廷瑞无疑是在养闲人。这使我格外感动,便尽心尽力地把事情做好。好在廷瑞虽然当了老板,对我却没有什么架子,虽然不再有小时候那样的亲密无间,却也相当够朋友了。
酷热难当。我和山顶上的工人便遵从了廷瑞妈的旨意,躲在火塘峰口的一处悬崖下纳凉。廷瑞妈说,小三子,到崖底下给我接一壶泉水来。廷瑞妈说,小三子,到工棚里把大婶的针线拿过来。我很乐意地跑上跑下,并隐隐地以此为荣。我们就谈起了廷瑞。廷瑞到城里买炸药去了。想起炸药,我不免胆寒。廷瑞和我同样的年纪,就能办这样的大事,崇拜之余,我也感到羞愧。用我父亲的话说,我就是一个读死书的人。如果不走读书这条道,注定讨不到媳妇,注定要饿死。
突然,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传来轰隆一声巨响,石块飞溅。我感到纳闷,谁家也太缺德了,如此酷热的天也不让工人喘口气,真是钻到钱眼儿里去了。廷瑞妈骂了一声狗日的,摆动着粗壮的胳膊、大腿,朝放炮的地方闯过去。廷瑞爹也寡着黑瘦的脸,一路小跑着跟在廷瑞妈的后面。很快,那边就传来激烈的争吵咒骂。我和工人们也跑了过去。原来是绰号叫梁光头家的沙场强行改渠。这梁光头三十来岁,他爹和叔叔都是搞建筑的老板,在村中颇有些名气。他家的沙场紧挨着廷瑞家,原来的排沙渠因为线路勘得不理想,流速太慢,严重影响了水沙的产量。几次和廷瑞妈商量,想从廷瑞家的渠道上面立交过去,廷瑞妈认为这样做不吉利,还有被人欺压的意思,很果断地拒绝了。梁光头便强行改道。他们吵得很厉害,双方的祖宗八代都被翻来覆去地操。廷瑞爹气愤不过,和梁光头扭打起来,却被梁光头三拳两脚打翻在地。梁光头喘着粗气,赭黄的脸涨得紫红,像一只战胜的公鸡。梁光头看着趴在斜坡上的廷瑞爹,悻悻地说,你个老东西,敬酒不吃吃罚酒,竟然跟老子斗……
我忘记了酷热,站在箐丛边不敢吭声,也不知道该怎么劝阻。廷瑞家的几个工人刚开了几句口就被恶狠狠的梁光头唬住了。廷瑞妈哭得鼻涕眼泪乱抹,扶起廷瑞爹,一路诅咒着下山去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廷瑞妈哭,我也很难过,这实在是欺人太甚啊,梁光头做得太过分了。
事情发生在傍晚。热气渐渐消退,微微的有了凉爽的风。太阳挂在西天,又红又大又圆,安详而又宁静。我像往常一样走到半山腰的一个峰口,吹起口哨,挥动旗帜。几分钟后,从山顶上发出轰隆隆的声响,身边的渠道就醒了,洪水裹着泥沙,咆哮着,左冲右突,奔涌而下。我正饶有兴味地欣赏着着洪水奔泻的气势,看见了廷瑞和他的弟弟廷航,一前一后,逆着洪水,一步一步地摇上来。大约半个小时后,廷瑞兄弟俩出现在工棚门口。
我连忙迎了上去,正想开口安慰他几句,却见他的脸像刚淬火的生铁,冰冷却又似乎在滋滋地冒烟。也不和我说话,径直进了低矮的工棚。他的目光在存放工具、杂物的角落里扫了一眼,又踅了出来,望着他家的沙场。一条被手推车碾压出来的流淌着泉水的沙石路,弯弯曲曲,拐进山的肚子。几个工人戴着草帽,正撅着屁股,挥舞着洋镐。然后,他圆溜溜的铁头转动了一下,目光朝不远处的一个工棚望过去。他终于说话了:走吧。
我就跟了过去。他猛地回头,眼里仿佛要喷出火来:没叫你,该干啥干啥!
我愣了一下,机械地停住脚步,才见廷航咬牙切齿,手里握着两根粗壮的钢筋。
我看着廷瑞兄弟俩一步一步朝梁光头的工棚逼近。我知道梁光头正在睡觉。他竟然睡得着觉。
我的心剧烈地跳动。我手足无措,四处张望,满山都是红霞。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我想喊又想叫。,我不敢喊也不敢叫。
几声惨烈的嚎叫。我痛苦地闭上眼睛,我的心纠结起来。
几分钟后,廷瑞兄弟俩一身一脸的血迹,小跑着回到了工棚。我浑身颤抖,看着他在工棚里不知翻弄着什么。很快他就出来了,递给我一张沾着血迹的纸条。他脸上的汗水和血水糊在一起。他的声音也有些颤抖。他说,不要打开,亲手交给我妈。
兄弟俩折身往山上跑去。我拿着纸条,手不停地颤抖。我呆呆地望着他俩跌跌撞撞的身影,还没完全回过神来,却见廷瑞又折了回来。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望着我,竟然笑了,他说,小三子,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吗?
我的眼泪掉下来,嘴唇像打摆子似的难以吻合,抖颤着说记得。
廷瑞又拍拍我的肩膀说,不要怕,这件事和你没有关系。说着,从夹克衫里掏出一沓钱来,捻出几张,塞到我僵硬的手里,并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将来你当了老师,对我小妹好一点,教她好好读书。拜托了好兄弟……
生活似乎就是一个无法控制的旋涡。从故乡回来,我很快被卷进日常生活的旋流里,上班下班,接送孩子,想方设法多挣几个钱以便早日还清房贷。至于轿车,暂时还不敢想。这没什么不好,我自得而又自足。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夜里,廷瑞兄弟俩提着钢筋,恶狠狠地闯进我家里。
我记得当时我正伏在电脑旁边,赶写一篇报社副刊主编约定的关于“慢生活”的文章,要求有真切的鲜活的体验。我们这个城市即将举办首届水城水乡国际旅游节,媒体便要围绕着这个主题为节日宣传、造势。这使我感到头疼。老实说,我对米兰·昆德拉的这个理念是赞同并且向往的,然而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我委实缺乏这方面的体验。就在我绞尽脑汁公鸡下蛋似的纠结难耐时,廷瑞兄弟俩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二十年没见,廷瑞还是当年的样子,黑脸、铁头、鹰眼、唇上一层绒毛,不同的是,眼珠是蓝色的,放出一道道卡通人物似的光芒。我正想起身招待他们,廷瑞把那根森然的钢筋压在我的头上,冷冷地说,别动!
当初我委托你的事,你是怎么做的?廷瑞的声音仿佛是从肚子里发出来的,瓮声瓮气,没有温度。
我忙不迭地跟他表白、强调。我说那张纸条,我亲自交给你妈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纸条上写的什么内容。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那么,我妹妹呢?廷瑞的脸比刚才更黑了。
我支支吾吾。我不知道该如何向他解释他才肯原谅我。廷瑞出事的那年,她妹妹才四岁。我师范毕业以后,就一直辗转他乡,最终落脚在遥远的江苏。我是有心有力可是没有机缘啊。听家人说,后来廷瑞的妹妹初中尚未毕业就去了广东,做着人们都心照不宣的那种营生。
打!廷瑞兄弟俩挥动钢筋,朝我头上猛砸下来。我感觉到自己的脑浆和鲜血四处迸溅。我啊地尖叫出来,猛地直起了身子……
责任编辑/董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