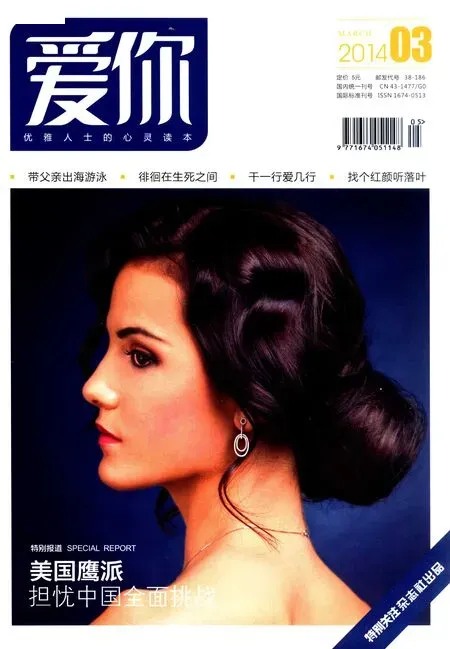姥姥走了
◎ 宋 维
姥姥走了
◎ 宋 维

姥姥走了,79岁,生活的艰辛和挣扎可以一一放下了。那座小山坳里寄托了我所有童年欢欣和苦涩的姥姥的家,已失去所有意义,我再也不会回去。
姥姥在去世前最后的日子里,依然弓着身子,跌跌撞撞给牲畜添喂草料。全然不同于有退休金颐养天年的老人,姥姥晚年的遭遇是中国农村老人的生活缩影。
姥姥缠过小脚,虽中途松绑,依旧落得终身步履蹒跚。30年前我出生的那个大雪天,姥姥一个人背着干粮,翻山过河,步行整整一天赶来照顾我。对一个小脚又不识字的农村妇女,这样一次远行有太多不可言说的冒险。在很多时刻,我都禁不住回想那个被风雪笼罩的傍晚,姥姥俯身抱起襁褓中的我,唤我的乳名。
去世前,姥姥已多日未进食,疼痛和饥饿让她的筋骨迅速松垮,血气散尽。我把她抱在怀里,她瘦弱得像个婴孩。我背她去屋外,姥姥生怕累着我,没几分钟就催着回去,一遍遍唤我的乳名。生命两端的相遇和告慰,何其相似。
姥姥的炕靠墙那一侧摆放着三个混杂着各种陈旧味道的箱柜,里面的物件是她这一生的全部,无外乎一些舍不得穿的新衣服、纳好了准备送人的鞋垫、布鞋、糖果之类。下葬时间已确定,我只希望这一切静静地过去就好。
我童年的每个暑假都在姥姥家度过。为我的去留,强势的母亲、怕老婆的舅舅、势利的舅妈和隐忍、慈爱的姥姥之间没少博弈。我欢欣于小孩子的各种游戏和恶作剧之中,虽寄人篱下,但有姥姥的庇护,童年的时光漫长却快乐。瘦小的姥姥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耕种甘肃农村的山地是对人力极限的巨大挑战。从犁地、播种到打晒、磨面,姥姥汗涔涔戴着草帽的样子、混着汗水和草渍的味道是我存留在心里的永恒印象。
姥姥经常穿老式大襟盘扣衣服,我每次离开时,她总会从衣服襟子里掏出一个已看不出颜色的手绢,塞给我一些钱。姥姥家在深山,十几户人家住得分散,姥姥捡拾野李子和杏子,再砸李子核和杏核,等货郎串村串户时换些钱。这些钱她小心翼翼地攒起来,连同子女和亲戚偶尔给的钱都仔细包在那块手绢里。甚至在我有了妻女后,每次离别,姥姥还是会颤抖着掏出那块手绢,执意塞些盘缠给我。
姥姥总是念念不忘两件事,说我怎么疼她、对她好,其实这和她对我的疼爱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我上小学时,姥姥有段时间来照顾我。碰巧那时有社教队在母亲单位驻点,时常会从兰州带来些农村孩子没见过的零食。我第一次吃奶油蛋糕、卤鸡爪以及一些当时不认识的水果,都是因此得来的。人家一旦给我吃的,我便拿回家给姥姥。这些举手之间一次次小小的给予,在我和姥姥之间留下一段段美好的回忆。
另一件是十年前,我刚参加工作,带姥姥到兰州逛了逛。返程时买了火车票,让姥姥坐了火车。这些后来在姥姥的叙述中都带着明显夸耀的口吻,称见了“大世面”。
姥姥走了,这世间的牵扯,终究成空。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38期 图/陈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