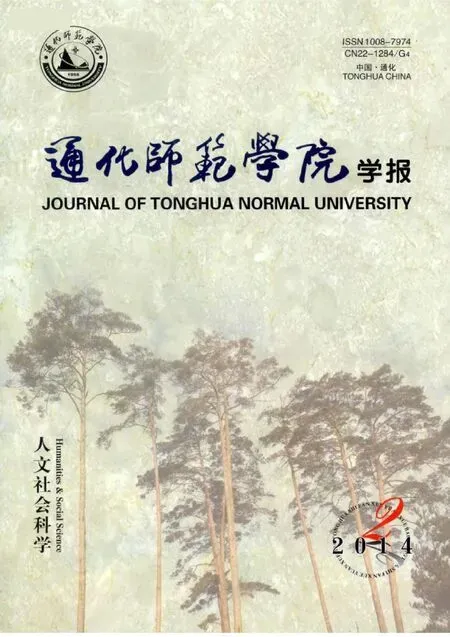1911-1932年中国内地与外蒙古贸易述略
赵金辉
(呼伦贝尔学院 政治与历史学院,内蒙古 海拉尔 021008)
历史学研究
1911-1932年中国内地与外蒙古贸易述略
赵金辉
(呼伦贝尔学院 政治与历史学院,内蒙古 海拉尔 021008)
中国商人至外蒙进行旅蒙贸易始于清康熙年间,并取得巨大发展。但是,民国时期,随着外蒙古独立等政治事件影响以及外蒙在政治上采取亲俄(苏)政策,对中国内地与外蒙贸易带来较大冲击,并逐渐走向衰败,至1932年后几乎完全断绝,这也标志着中国内地与外蒙的旅蒙贸易的终结。
中国内地;外蒙古;贸易
清代,旅蒙贸易取得巨大发展,但近代以来,中国商人垄断外蒙古①市场的地位被打破,沙皇俄国②势力侵入外蒙,外蒙市场开始呈现出中俄竞争的局面。随后,英、美、德、日等国的洋行亦开始涉足于外蒙贸易,贸易格局呈现多元化。至民国时期,受到外蒙独立等政治和军事因素的影响,中国内地与外蒙贸易开始走向衰落,最终完全断绝。而外蒙在政治上接近俄国(苏联),大力发展与俄(苏)之间的贸易,贸易额大幅度增加,至30年代,外蒙贸易几乎被苏联所垄断。
一、与外蒙贸易走向衰落(1911-1914)
清代旅蒙贸易兴起后,外蒙市场完全被以晋商为代表的中国商人所控制。清咸丰十年(1860),俄国商人取得在外蒙古库伦的贸易权,光绪七年(1881)清政府“又许彼于蒙古各处,均得贸易,皆不纳税”。[1]31俄国在外蒙地区的贸易扩大,但贸易的主导权仍掌握在中国内地商人之手。据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实地考察外蒙的李廷玉在《游蒙日记》中记载:“随谒廷大臣探询商情。知库伦商户百余家,晋人十之六,顺直十之一,俄人十之三。”[2]644另据1908年统计数据,“俄蒙贸易的进出口总值是八百万卢布,而同期中蒙贸易的进出口总值则达到五千万卢布。”[3]106
民国时期,由于受到国际和国内一些政治、军事因素影响,中国内地与外蒙贸易波动较为频繁。清宣统三年十月十九日(1911),外蒙喀尔喀四部在沙俄的策动下宣布独立,建立蒙古帝国[4]107。外蒙独立使贸易往来受到较大冲击。外蒙宣布独立之时,“在留华商,尚有一万六千余人”,外蒙政府虽也下令保商,让商民“正常贸易,安心居住”,[5]21但“华官去后,保护无人,来货绝迹,抢劫时闻,各旗所欠华商款项,不下四五百万,一时无法筹还,遂思一网打尽,以图抵赖。”并对华商做出种种限制和暴行,包括:禁止华商出入喇嘛圈内;禁止华商集会;禁止华商与蒙人杂居;禁止华商与内地交通;勒令华商承办差徭供应夫马;勒令华商改易蒙古装束(未实行);勒令华商纳进出口税,值百抽五;蒙官时以小故控诉华民,一言不合,力毙杖下,或以冷水灌顶,立时毙命;蒙兵强买货物,稍不有遂,肆行打毁;明火劫夺,月三四起,官不过问。 [5]34-35
上述各项限制华商的措施,对华商在外蒙的经营产生负面影响。如对华商及贩运货物征收重税,“自外蒙官府独立以后,岁入之款,除森林、畜牧、矿产外,咸取资我国商民,穷搜悉索,税及人头。”[6]86“东西库伦税局,征收毫无纪律,日渐加增……商人切齿,怨声载道。”[7]43华商的安全也不能得到保证,在民国元年八月十三(1912),在库伦的大汇兑庄锦泉涌被抢夺,四名铺伙被杀,抢去现银六千余元。[6]86上述原因致使“商旅裹足,然犹于取缔监视之下,免取微利。”[8]35对外蒙贸易举步维艰。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外蒙与俄国的贸易,由于采取亲俄政策,在1912年与沙俄秘密订立《俄蒙协约》及其附件《商务专条》,俄国取得在外蒙的政治经济特权。包括:在蒙自由居住;免纳出入口各税;开设银行、邮政;租买土地,建造工厂货栈;开垦耕种,享用矿产、森林、渔猎;添增领事馆,划定贸易圈;航行外蒙河流,使用外蒙台站,修筑桥梁渡口。此后又有电线、铁路等合同。[9]39俄国在外蒙的商业势力得到迅速扩张,“俄蒙贸易关系,日趋于密切,蒙古复成俄国之市场矣”,[10]2719“1914年俄国对蒙输出货值计一百三十万卢布。”[11]而且,俄蒙之间由于边境警备不全,向有秘密输出的惯例,见诸于统计者仅为其中一部分。另外,这一时期俄国对于发展蒙古贸易,“举国上下,靡不竭力经营”,不仅大力整顿俄蒙之间交通,设立“对蒙贸易输出协会”,筹设俄蒙银行等,促进了对外蒙贸易的发展。[10]2719-2731
虽然这一时期中国内地与外蒙贸易遭遇诸多障碍,但就贸易主导权而论,仍控制在中国内地商人之手,因为以晋商为代表的中国内地商人在外蒙贸易已有两百多年历史,“商人间之信用,由来已渐,”俄国虽企图控制对外蒙贸易,但也“难顿遂其野心”。[10]2719-2731
二、与外蒙贸易的复兴(1915-1920)
一战爆发后,俄国在外蒙市场上迅速退却,“俄蒙贸易关系,几乎完全断绝”。[11]华商利用有利时机,重新夺回市场,中国内地与外蒙贸易迎来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对贸易发展有利的条件包括:在政治上,1915年《中俄蒙协定》签署,中国商人在外蒙商业活动有条约来保障,此后,北洋政府利用一战和俄国革命的有利时机,由徐树铮率军进入外蒙,并最终促成“外蒙撤治”。在徐树铮和陈毅等治外蒙期间,取消了人头税和房屋税;设立商务总会;在库伦筹设中国银行等举措,[6]86-108有利于中国内地与外蒙贸易的发展。在交通运输上,张家口和库伦之间汽车货运的开通,先后设立的包括大成公司、西北汽车公司和美商元和洋行等,[6]111-112现代化运输方式的使用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
据库伦商会统计,民国四年十二月(1915),仅库伦有“大小商铺,共五百七十七家,人数计六千一百十五名。此外有土木工匠一千五百余人。”“全蒙华商之进口,以牲畜、皮毛、蘑菇为大宗,出口以砖茶、生烟、绸缎、布匹为大宗,其余日用饮食必备之品,无一不备,甚至如舶来品之纸烟、牙粉、胰皂、毛巾等,亦为出口货之附属品。”[6]981915年至1916年中国内地与外蒙的贸易额在4500万到5000万卢布,远远超过俄蒙之间的贸易额。[12]150而对外蒙贸易的中心城市张家口“自边防军筹建汽车路以还,输运愈便,商务尤盛。西沟‘外馆’增至一千六百家,贸易额达一万五千万两,计进口八千万两,出口七千万两,是为张库交易‘鼎盛时期’。”[13]786
三、与外蒙贸易再次衰落并走向断绝(1921-1932)
1921年,白俄恩琴匪兵侵入外蒙,使外蒙出现“二次独立”事件,这一系列的政治波动对华商贸易造成沉重打击。在白俄恩琴匪兵攻占库伦时,“一遇中国官商兵民即行开枪”。[14]180另外,“传闻外蒙各旗,凡我国商民,不但货物抢空,生命损失尤众。……统计此次官商损失,生命有数万之巨,财产约万万之巨。”[14]182大量中国本部商民逃离外蒙,其中数万华商和难民被迫经由苏俄远东共和国上乌丁斯克、赤塔等地,被北京政府和东北当局接运回国。[15]
政治变动使华商损失惨重,贸易也一时中断,但很快得到恢复。因为外蒙经济较为落后,“向以其皮毛牲畜,来内地交换物品,举凡粮食、衣服、器皿,即一缕一粟之微,莫不养给予汉人。”[14]215“自中蒙纠纷,货物往来断绝,库伦外来货物异常昂贵,土产物品无人收买。”[14]182因此,新成立的外蒙“革命政府”,对恢复与中国内地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持欢迎态度。[14]177“八月一日出示商民,……所有俄人、汉人、内蒙人、藏人,均以外国人待遇,月收人税银二钱五分,半年一收,一年一收,予以工商护照,自由在蒙疆以内贸易。”[14]181另一方面,在外蒙政治局面稳定后,经美国领事至外蒙协商,美国在张家口的洋行率先恢复了与外蒙之间的贸易,而华商担心外蒙商业权益的丧失,华商的库伦商务总会积极促成与外蒙贸易的恢复。
1921年9月察哈尔与外蒙边境戒严的解除,与外蒙贸易得到恢复,甚至一度仍占据外蒙贸易优势,如据1923年统计,外蒙共登记商行2323家,其中中国商行1440家,占66%,英美商行62家,占3%,俄国私营商行166家,占7%,蒙古私营商行655家,占24%。其中中国商行的贸易额占总数的60%。[3]194但在外蒙政府的限制和苏俄的竞争下,呈逐渐下降趋势,特别是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中国内地商人采取限制措施,不仅债务被取消,大量货物亦被没收。据1926年到访外蒙的毛以亨在《满蒙回忆录》中记载,原本中国大商人居住的东库伦,因“无人居住而成为废墟,大商人的财产在革命时已被没收”,当时在库伦的华商皆为小商人,作“小本经营,杂货店、理发馆、澡堂、妓馆都应有尽有,但没有一家能像样的”。[16]29另外,大量中国本部商人回国或转行从事手工行业,包括木匠、瓦匠、银匠、糊裱匠、成衣匠等聊以糊口。[13]805
外蒙政府在政治上接近苏俄,贸易亦逐渐被苏俄所操纵。在1922年,苏俄对外蒙输出73.6万卢布商品,从外蒙输入了8.1万卢布的商品,贸易额仅为81.7万卢布。但随着1923年苏联与外蒙秘密签订《俄蒙贸易协定》,外蒙古“必须在国家中促进形成联合会的合作社组织的发展,组织蒙古原料走向外部市场,为蒙古直接获得商品,尽可能避免在蒙古从事贸易业务的外国商人作中介”。[17]外蒙与苏联贸易关系日益紧密,并采取多种歧视性政策将中国内地及英、美、日等国逐渐驱逐出外蒙市场。可以说,“自苏俄之兵力达外蒙古以后,其地实际上已等于丧失。至少在经济上之情形如此。惟名义上主权仍属中国耳。蒙古与苏俄贸间之贸易蒸蒸日上,而与中国本部之贸易则逐年减少。以1929年为尤甚。但次年之情形更劣。蒙古除向我购小部分茶叶外,其它竟无所有。 是年蒙古对我国输出商品更等于零。”[18]418-419外蒙与苏俄之间贸易增长从表一中可以概见。[19]17

表一 外蒙与苏联贸易额统计
从上表中可见,苏联与外蒙贸易从1923-1924年度的3474000金卢布,至1931年增至66176000金卢布,增长了19倍。而中国内地与外蒙贸易则呈下降趋势。至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苏断交,中国内地对外蒙贸易再次遭受沉重打击,重要的对外蒙贸易城市张家口“中俄绝交后,市面商务,遂一落千丈,三沟商号,收歇殆尽。 ”[20]110在归绥,中国最大的旅蒙商号大盛魁也于1929年歇业。多伦诺尔亦是“外蒙古全然封锁,华商贸易之路,完全杜绝,财产没收于外,事业衰歇于内,多伦商务一蹶不振。[8]35至民国二十一年下半年(1932),张家口与外蒙贸易进口仅165711.82元,出口772246.40元,且多为德华洋行经办。中国本部华商与外蒙之间的贸易基本断绝。[13]801
四、中国内地与外蒙古贸易衰落的原因
这一时期中国与外蒙古地区的贸易呈现出阶段性波动的特点,最终走向了完全的断绝,其主要原因为:
(一)随着俄国对外蒙古地区的侵略,中国的政治势力逐渐被逐出外蒙,此对中国内地与外蒙贸易产生重大影响。外蒙古喀尔喀四部早在清初即臣服于清朝,康熙年间多伦会盟之后,清朝完全确立了在外蒙古的统治地位,先后设置了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和科布多参赞大臣进行管理。近代以来,沙俄利用不平等条约将侵略势力侵入外蒙地区,1911年外蒙在沙皇俄国的策动下出现了第一次独立,虽然其后北洋政府利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时机,实现了外蒙的短暂撤治,但旋即外蒙又出现 “二次独立”,中国仅保留所谓的宗主国的头衔,在外蒙的政治、军事影响力几乎完全丧失,而外蒙最终被苏联所控制。这种局面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的贸易关系。在俄国(苏联)控制外蒙期间,利用《俄蒙协约》以及《俄蒙贸易协定》,取得很多贸易特权,不断侵夺中国内地商人的市场。[4]102而中国内地商人失去政府保护,“有事只由中国商会处理,每受压迫,无法申诉”[4]103
(二)商业环境恶化,外蒙对中国内地商人采取多种歧视性政策加以排挤。民国时期由于外蒙政治变动频繁,商业环境极具恶化。另外,外蒙极力排挤中国内地商人,对商人和货物采取严格的管理和登记制度,稍有不符则处以十倍重罚;在金融方面,惟一金融机构蒙古银行在华商汇兑方面多种限制;在税收方面,以征税明目层层盘剥,各种货物税率达6%,另外尚有落地税、检验税等明目。[21]81在《蒙藏新志》中记载:如资本一万元,即派出流水捐五六千元,红利捐三四千元,华商必须照交,稍有迟缓,立代拍卖完税,这种掠夺式的税收政策致使华商完全收歇,而当时所传的中国商业完全被外蒙政府没收这一说法即源于此。[13]788-793在债务方面,宣布旅蒙商与外蒙债务全部失效,商人损失惨重。仅大盛魁在外蒙古被没收的货物,就约值二、三百万两银子。[22]另外,还有严格的盘查制度,甚至对商人与内地往来书信都要查验。在此种情形之下,中国本部的商人“金钱既耗,禁锢旋加,危且及于生命,所以纷纷返回,又须受种种留难,至两手空空而始放行,汉商将有全灭之势。 ”[4]103
(三)“二次独立”后的外蒙古效仿苏联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逐渐掌握贸易主动权。1921年外蒙古“二次独立”后成立革命政府,1924年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所谓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完全被苏联所控制。同时,开始效仿苏联,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以国家为主导实施 “一五计划”,发展畜牧业、农业、工业和商业,并积极推进国营化,建立国营农场和牧场,至1931年已有国营农场和牧场740余个。在商业和对外贸易上,将中国内地商人的贸易视为剥削,极力排挤,并逐渐由政府掌控贸易的主动权。如成立中央人民消费合作社,与苏联密切合作,在1928至1929年只占外蒙贸易额的25%,至1931年已占71%。而在1930年,外蒙将对外贸易机关收归国有。[23]31-32外蒙古的这一政策使中国内地商人逐渐丧失外蒙古的贸易基础和市场,渐次被逐出外蒙。
(四)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内地商人在商品、市场和信用方面的优势逐渐丧失。中国内地商人在外蒙古的贸易历史悠久,而由于外蒙古单一的畜牧经济结构,中国内地商人贩卖的粮食、茶叶、器皿等商品具有很大的优势,旅蒙商也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商业运营方式,使中国内地商人长期掌控对外蒙贸易的主动权。但是,民国时期这种优势逐渐丧失。在商品方面,随着俄国(苏联)的工业发展,中国商品的优势逐渐被取代。在交通运输方面,中国内地商人对外蒙古的贸易长期依靠骆驼、牛车等方式,虽然民国时期开始出现汽车这一运输方式,也极大的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但在20年代中期大部分汽车被冯玉祥的西北军廉价收买,用于军事运输,一度不允许张库路上商人的汽车运输。[16]33而俄国(苏联)却可以通过西伯利亚铁路等现代化的交通运输方式,甚至出现了将中国的砖茶等运至海参崴,再经西伯利亚铁路对外蒙再出口。特别是在苏联时代,随着苏联“一五计划”的完成,“苏联的工业规模和在远东的运输能力已大大超越旧俄时代,最终确立了对蒙古贸易的优势地位。 ”[24]
总之,民国时期的中国内地与外蒙贸易波动较为频繁,且主要表现为中国和俄(苏)在外蒙贸易主导权上的博弈,影响博弈结果的主要因素为政治因素。中国内地商人凭借两百多年积淀下来的商业信用和商品上的优势,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下,仍将对外蒙贸易主导权保持到20年代中期,随着苏联在政治上完全控制外蒙,对华商采取诸多歧视性政策加以打击和排挤,最终致使中国内地与外蒙贸易走向彻底断绝,也标志着从清代持续到民国时期的旅外蒙贸易的彻底终结。
注释:
①本文中涉及外蒙古问题,这一时期外蒙古出现两次政治独立事件,时间分别为1911年和1921年,特别是在第二次独立后成立革命政府,1924年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但中国政府并未承认外蒙古独立,1924年中苏协定仍认定外蒙古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中国拥有主权。至1945年8月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举行公民投票来确定外蒙古的独立,1945年10月外蒙古进行了公投,国民政府于1946年1月5日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
②本文所论涉及俄国,在本文时段内由于俄国出现政治变革,分别是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沙皇俄国,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以及1922年12月后的苏联。因此文中在相应时段写为相应名称,在涉及几个时段政权时则写为俄国(苏联),或简写为俄(苏),引用文献的原文不在此例。
[1]姚明辉.蒙古志:卷三[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2]李廷玉.游蒙日记[G]//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中心出版,1990.
[3](苏)伊·亚·兹拉特金.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M].陈大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4]马鹤天.内外蒙古考察日记[M].南京:新亚西亚学会,1932.
[5]唐在礼,唐在章,撰.黄藻音,点校.蒙古风云录[G]//吕一燃.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
[6]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第二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7]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第一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8]杨溥.察哈尔口北六县调查记[M].北京:京城印书局,1937.
[9]郭廷以.俄帝侵略中国简史[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10]佚名.俄蒙贸易最近之情况[G]//经世文社.民国经世文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11]沈光沛.中俄贸易之检讨[J].东方杂志,1933(2).
[12]彭传勇.1911-1945年俄(苏)与外蒙古的政治、经济关系[D].长春:吉林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未刊.
[13]黄奋生.蒙藏新志[M].上海:中华书局,1938.
[1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15]樊明方.1921年接运库、恰难民述略[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3).
[16]毛以亨.俄蒙回忆录[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17]彭传勇.20世纪20年代苏联在外蒙古的贸易活动及影响——以苏联国家进出口贸易管理局西伯利亚部的活动为中心[J].西伯利亚研究,2008(6).
[18]孟宪章.中苏贸易史资料[M].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
[19]独立出版社.我们的外蒙古[M].汉口:独立出版社,1938. [20]李延墀,杨实.察哈尔经济调查录[M].新中国建设学会出版科,1933.
[21]刘虎如.外蒙古一瞥[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22]宁有常.近代最大的旅蒙商号大盛魁[J].文史精华,1996(3). [23]民羅多.外蒙古[M].出版者不详,1928.
[24]渠占辉.20世纪前期俄(苏)蒙贸易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历史教学,2001(11).
(责任编辑:徐星华)
Discussion on Trade Between Chinese Mainland and Outer Mongolia in 1911-1932 ZHAO Jin-hu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Hulunbuir College,Hailar,Inner Mongolia 021008,China)
During the Kangxi period,Chinese businessmen began to Outer Mongolia for trade,and has achieved great development.However,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Outer Mongolia's independent and taking Pro-Russian (Soviet)policy has a bad effect on the trade between China mainland and Outer Mongolia,and the effect on trade was devastating,after 1932 was almost completely cut off,this also the symbol on trade between China mainland and Outer Mongolia ended.
Chinese mainland;Outer Mongolia;trade
K258.9;K26
A
1008—7974(2014)02—0037—05
2013-10-11
赵金辉(1979-)内蒙古通辽市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城市史、北方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