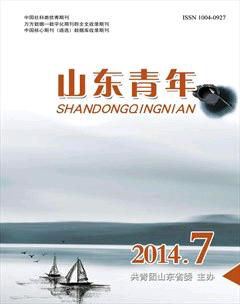建国初期农民党员入党动机分析
吴修申
摘 要:建国初期,为巩固新生政权,中共积极地在农村发展党员,以便使新党员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进而提高党的形象和威望。不过建国初期一部分农民新党员入党动机并不十分纯正,这与农民注重实际利益的获得及其文化水平低有密切关系。中共通过整党和党员自我思想改造等途径,使农民党员的入党动机逐渐纯正,为党的农村政策的推行和巩固执政党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农民党员;入党动机;阜阳县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为巩固新政权和政党建设的需要,中共必须进行工作重心的转移,即从以农村为中心到以城市为中心的转变。不过在把工作重心向城市转移的同时,中共仍然离不开四万千农民的支持与拥护。中共在农村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能不能很好的实施,一方面要有正确的政策,另一方面还需要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这样党的政策才能落到实处,才能得到广大农民的真诚拥护。因此新政权成立初期农村党员能不能担负起改造农村和农民的担任,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对于党在农村的形象塑造和长期执政都有极大的意义。
提升党在农民中的形象和维护党的声誉的关键之一在于农民新党员的素质。基于学界对建国初期农民党员的入党动机研究比较薄弱的状况,本文借助入党志愿书和党员登记表等一手材料,以皖西北阜阳县农民新党员为例,就建国初期农村党员的入党动机等问题作一分析。
一
新中国初期,如何巩固新生政权,赢得广大民众的拥护,是中共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模式,主要依靠农民的支持,最终赢得革命胜利。新政权建立后,要巩固政权,还是离不开农民的鼎力支持。新中国成立之初,大部分地区是新解放区,要让当地民众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新政权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特别是过去一直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一些农村,当地民众长期受国民党的宣传,将中共妖魔化,要清除这些妖魔化宣传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例如,距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比较近的安徽省阜阳县,从1927年到1948年始终处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当地民众主要受国民党舆论控制,虽然当地也有中共的组织,由于绝大部分时间处在秘密状态,影响不大;因此,民众对中共的性质和宗旨不太了解,对中共及其新生政权心存疑虑,甚至害怕。安徽阜阳县农民陈永林说:“在家乡未解(放)前,听到反动派的反宣传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斗争等,内心是有点恐惧的”。[1]
1949年3月,阜阳全境解放,属新的解放区。在阜阳新解放区,中共及其各级地方组织首先向广大民众宣传革命的正义性和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以打消新解放区人民的疑虑和担心,塑造自身的合法性和赢得支持。1948年8月阜阳县城解放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严明的纪律,坚决不扰民等行为,很快打消了民众的疑虑,赢得了民众的信任。阜阳县农民陈永林说:“解放军的纪律很严明,借人家的东西不但很客气,而且损坏还赔偿”。另一方面中共和解放军还大力向贫苦农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对农民说:“你们穷人翻身了,我们打倒大资本家、大地主,在国民党时期他们是统治你们穷人的,今天我们就要革掉这些人的命”[1]。通过自身的行为表率和宣传,中共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军努力启发和唤醒农民的阶级意识,使贫苦农民逐渐觉悟。
在取得农民信任的基础上,中共阜阳地方党组织通过剿匪反霸、生产救灾、治理淮河等中心工作,建立了基层党支部,发展了一批新党员。1949年底,阜阳地区有党员3310人,到1950年4月,有党员10676人。在不到半年时间内,阜阳地区发展新党员7366人。[2](p.60)建国初期阜阳地区的党员绝大多数是新党员。我们以陈永林为例,对部分农民新党员的入党经过和入党动机加以分析。
陈永林,阜阳县程集区时庄村农民,家庭出身贫农,上过二年私塾,后来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在家生产。1949年他25岁时,阜阳县工作队到程集区开展反匪反霸运动,在时庄开展工作时,认为陈永林念过二年私塾,又是贫农出身,便动员他竞选村长。陈永林一开始还不愿干,经过乡长和工作队的动员,才担任村长。在村里工作半年多,由于协助政府征收公粮等工作表现出色。在1950年1月被乡政府推荐到阜阳地委团校学习并在学习期间入党,成为中共候补党员。当时陈永林的入党动机为“经过反匪反霸的斗争急切入党,认识到中共替人民伸冤报仇”。[1]
陈永林的入党经过在建国初期中共接收农民新党员的事例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体现了中共接收发展农村党员的一般途径。中共在改造农村的运动中发现和培养一批积极分子,先让其进入乡、村政权内担任一定的职务,进而考察他们在工作岗位上的表现,最后选择其中最优秀分子吸收入党,为党在农村政策的贯彻实施进一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正如陈永林在陈述自己入党手续时说,“工作队见我工作积极,于时(是)就动援(员)我参加中共”。[1]早在1948年底,中共中央中原局就提出在农村选拔积极分子,经过训练,使之成为乡、村一级干部,“并有组织地较大部的从中吸收入党。”[3](p.76)这一发展农村党员的方式既可以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又能够增加党组织的新鲜血液,巩固党的领导地位,更有利于贯彻执行党对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
其实这些农民新党员入党之前正是由于得到党组织的信任,获得了一定的实际利益后,才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比陈永林稍微早一点入党的钱文言,1949年11月入党。他的入党动机非常实际,就是为了提高自己在村里的政治地位,“当了村干部,认为过去没有政治地位,只因是义子大家都看不起。现在参加了党,是很高兴的,只因也有了政治地位”。[4]比陈永林晚1个月,1950年2月入党的刘金生,是村农会组长,谈到自己的思想转变和入党动机说,“自任自然村农会组长,工作积极,情绪高”。[5]
从上述3人的入党情况分析,他们都是在党领导的改造农村的活动中,工作出色,表现积极,因而担任了一定的职务。这些人在参加革命后,自身受益,对中共的性质和宗旨有了直观的认识,他们的政治地位是党给予的,因此他们的政治命运与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进一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追求进步,积极要求入党。他们的入党动机比较实际和质朴,与自身的实际利益获得紧密相关。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米格代尔所言:“像农民加入的其他类型政治组织一样,革命运动必须向农民个人提供物质利益,以换取农民对革命的支持和参与。”[6](pp.8-9)endprint
从上述农民党员的入党动机和思想转变过程的自述中,我们没有发现他们填写诸如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之类的字眼。究其原因,大概与农民对这些比较专业和带有理论性的术语不太理解有一定关系。再结合他们的入党动机分析,建国初期农民党员对中共和革命理论的理解比较粗浅,有实用主义因素在内。他们更注重自己实际利益的获得。1927年中共湖南省委谈到了农民对于革命理论和革命宣传的一些反应:“开口共产主义,闭口阶级斗争,一句反对资本主义,二句主张马克思主义——实在说宣传这些,完全是笑话,他们一天忙衣食,哪里管你这些不相干的事情,而且未读过书根本不懂。”[7]p.41这段话虽然谈及的是1927年时农民对于中共和革命理论的态度,但是也符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党员对党的认识和态度。3位新党员除陈永林读过两年私塾外,其他二人都没有读过书。因而就文化程度而言,他们对党章中的一些名词术语,诸如阶级斗争、共产主义之类等就很难理解其含义。大概基于建国之初农民新党员入党动机比较质朴,对党的基本知识了解无多的现实,中央组织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入党志愿书上印制了统一的入党誓词,具体内容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议,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积极工作,精通业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4]。这一入党誓词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党的纲领、纪律、宗旨和奋斗目标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民新党员对党的知识了解无多,对党的认识不到位的遗憾。
二
一般而言,入党动机是申请入党者的内在的精神动力。从中共革命话语而言,农民起来革命,支持和拥护中共的主张和政策,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天然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与地主的矛盾尖锐,不可调和。因此,从逻辑上分析,农民申请加入作为农民利益代表的共产党,其动机应该涉及到受地主剥削,与地主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有志于推翻地主的统治等因素。
不过就一些农民党员的入党动机而言,则与这一逻辑差别较大。陈永林、钱文言、刘金生等新党员虽然都是佃农,靠种地主的地维持生计,受到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但在填写入党动机时,他们并没有把受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作为自己的入党动机之一。这就说明农民从理性上清楚地认识到受地主剥削和压迫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经过启蒙教育才能逐渐清楚这一道理,从而唤醒自己的阶级意识。例如,陈永林就是在中共的启发教育下,才认识到自己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的根本原因,在于受地主剥削和压迫。他说:“通过了反霸,群众斗争会,使我认识了地主为何残酷的剥削农民,压迫农民,使农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激起了我的阶级仇恨。”[1]
有的新党员在入党志愿书中没有谈到地主与农民的矛盾问题,但是在经过土地改革和整党之后,就认识到了自己入党动机有受地主压迫剥削的因素,这说明党员的入党动机有一个不断纯正的过程。刘金生在其1950年的入党志愿书中,没有谈到受地主的压迫和剥削问题,但到1954年填写党员登记表时,他的入党动机变成了“为了人民翻身,因原受地主压迫,为了不受压迫剥削,求得解放,坚决干到
底。[8]将地主剥削作为入党动机的原因之一在于刘金生通过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对地主剥削农民有了清楚的认识。1951年10月到1952年8月,阜阳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土地改革中,中共通过动员贫苦农民诉苦,开斗争地主的群众大会等方式,将贫农深受地主压迫和剥削的话语烙入农民心底,变成了革命流行话语之一,因此经过土改之后的党员,懂得了更多革命道理,更加热爱中共,因而这时再来梳理自己的入党动机时,思想认识就有了很大的提高,顺理成章地将受地主剥削这一事实内化为自己的入党动机。
195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党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整顿党的作风,改善党的组织状况”,决定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全面的整顿,在全体党员中进行一次中共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的学习教育,并对每一个党员进行认真的审查和登记。这次整党运动到1954年基本结束。中共阜阳地委从1950年10月开始整党,到1954年3月,整党工作基本结束。经过学习和整顿,广大党员,尤其是新党员深受了一次党的教育,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如,陈永林在1954年9月所填的党员登记表的“入党动机”一栏中写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行共产主义。”可见经过几年来组织上的教育和学习,陈永林的入党动机已经比较纯正,知晓了党的宗旨和最终奋斗目标。他对党的认识也有所提高,认为中共能够“正确领导农民”,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技术,改善农民生活”。[9]
还有一个入党动机也是入党志愿书中没有涉及,而是在党员登记表中谈到的,就是不被拉壮丁也成为当时一部分阜阳农民党员入党动机之一。例如,邹洪才谈到其入党动机,是“因为拉壮丁,受地主压迫”。[10]刘金生在党员登记表中(转正时登记表)的入党动机之一是“为了不当壮丁”。[8]这一动机虽然不是完全纯正的,但却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强拉壮丁给当地民众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和痛苦,以致成为部分党员参加中共的动机之一。南京国民党政权在抗战时期就开始强拉壮丁当兵,老百姓不愿去的就用绳子捆上,被押着送到兵营。为了逃避当兵,有的人被迫自残。据郑永彦回忆,其妻兄为避免被抓壮丁,被迫忍痛用石灰将自己的双眼刺瞎,落得终身残疾。[11](p.8)因此国民党政府的抓壮丁行为是阜阳当地老百姓最痛恨国民党统治的原因之一。
1949年阜阳解放后,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农民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匪反霸运动。1949年10月,在反对地主恶霸运动中,阜阳县不少农民提及了抓壮丁这一国民党政府的恶政。例如,1949年,在开斗争阜阳县大地主倪步蟾的大会上,贫苦农民控诉倪步蟾的一大罪行,就是他任国民政府保长时,强迫人去当兵,甚至将家中是独子,应该不去的,也强迫去,致使有的被迫自残、有的家破人亡。[12]endprint
按照正常逻辑而言,阜阳县农民长期处于国民党统治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深受国民党政府强拉壮丁之苦,这些党员在填写入党志愿书时没有谈到这一点,而到了1954年才将其作为入党动机之一。这恰好说明了农民新党员经过整党整风的教育,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入党动机进一步纯正的结果,充分证明了建国初期中央进行整党的必要性、紧迫性和正确性。
结语
从阜阳县部分农民党员的入党动机的变化可以得出,建国初期农民党员的入党动机有一个从纯朴到逐渐端正的过程。部分农民党员入党动机的不纯,并不能说明他们是不合格的党员,而恰好说明了他们用质朴的语言表达了对中共和新政权的由衷热爱。因此,中共对于这些党员,并不是将他们清除出队伍,而是通过党内支部教育、党员自我学习、整党等方式,不断教育,使他们思想认识上不断提高,入党动机逐渐端正。
党员入党动机日渐纯正,一方面表明中共通过党支部教育和党员自我学习等方式端正新党员入党动机的做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是新党员努力追求进步,自觉学习党的规章制度,不断进行自我改造,勇于与不正确的思想作斗争,不断提高自己的结果,反映了新党员思想改造的心路历程。
[参考文献]
[1] 陈永林:《鉴定书》,1951年.个人收藏.
[2]《征途—阜阳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汇编》(一),内部资料,无出版项,2006.
[3]钱文言:《入党志愿书》,1949年.个人收藏.
[4]刘金生:《入党志愿书》,1950年.个人收藏.
[5]《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第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6][美]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7]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中共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8]刘金生:《党员登记表》,1954.个人收藏.
[9]陈永林:《党员登记表》,1954.个人收藏.
[10]邹洪才:《党员登记表》,1954.个人收藏.
[11]郑永彦:《往事漫忆》,内部资料,无出版项,2009.
[12]《阜阳县有关恶霸倪步蟾的罪行材料》,阜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1-107-6.
(作者单位:阜阳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