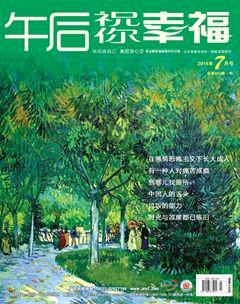韭菜馅饺子
荆方
弟弟在俄罗斯常驻,感触最深的就是对味蕾的歉疚。俄罗斯地处寒带,食物大多重荤重油,这对于吃惯荤素搭配菜肴的中国人来说未免太油腻,而且花椒大料葱姜蒜这些去腥、解腻的调料一概不用,烹调简单粗暴,无论猪牛羊肉都是一个炖,顶多煎一下,还放大量黄油,做出来的菜还没吃就能闻到浓郁的腥膻味,难以入口。那些年在俄罗斯淘金的中国人,对家乡的各种思念里最直接、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对食物的刻骨思念。弟弟说,每次回国时,国际列车一进满洲里,车上的中国人蜂拥而下,将满洲里小站商店的食物抢购一空,大到午餐肉罐头、方便面,小到榨菜、黄豆酱,什么都不会留下,列车过后的商店就像蝗虫过后的田野。实在连豆酱都抢不到的人,就抢一包五香瓜子,因为那里面有中国独有的五香味儿。
俄罗斯有中餐馆吗?有,但贵得离谱。
俄罗斯还叫苏联的时候,两美元换一卢布,物价极其稳定,一些吃饭用的瓷盘子底部有“2卢布”的字样,像盘子本身的图案一样是烧制上去的,当地人解释说这盘子当年就卖两卢布,物价几十年不变,所以可以直接烧在盘子上,免得进入市场后弄错。而到边贸开放的时候,物价飞涨,一美元能换几百卢布,民不聊生。当时莫斯科最贵的餐馆基本都是中餐馆,一盘鱼香肉丝十五美金,合当时的人民币一百多块,够在北京买几十盘的。但中国餐馆就餐的人并不少,都是发了横财的中国倒爷,他们一掷千金,一桌子菜花上百美金眼睛都不眨一下。
弟弟他们去不起中餐馆,实在馋得不行了就自己尝试着做,一群在家里不会做饭的小伙子,在异国他乡反而都开始学习烹调家乡菜。首先尝试的是西红柿炒鸡蛋,因为市场上这两样东西非常普遍,但买完西红柿和鸡蛋后才发现,没有花生油,只有黄油和奶油。黄油就黄油吧,也没有炒锅,都是电炖锅,黄油入锅后咕嘟咕嘟冒泡,起浓烟,但鸡蛋液倒进去后并不凝结,反而跟着黄油混成一片黄色的稠糊,一起咕嘟咕嘟冒泡,西红柿炒鸡蛋宣告失败。后来他们在市场发现了六必居的固体酱油,爱吃而又聪明的中国人,总是能想出各种巧妙的办法满足味蕾的需要,这固体酱油就是专门为海外华人生产的方便食品。类似于东北大酱,买回来弄下一块加入开水,就变成了褐色的酱油。这简单的褐色液体解决了多少游子的思乡之苦啊,弟弟他们炖肉时候加一点,做汤时候也加一点,中国味就找到了。跟弟弟他们做邻居的是温州人,都说温州人是中国人最聪明、最能适应环境的,一点不假。当弟弟他们几个中原小伙还在摸索西红柿炒蛋的时候,温州人已经用固体酱油卤制酱猪蹄了。俄罗斯像其他外族一样不吃动物内脏,猪肉市场上的猪头、猪蹄、猪肝、猪肚之类基本是半卖半扔,温州人以极低的价格买回来猪下水,用固体酱油和糖、盐、酒卤制出来,跟北京的天福、苏州的陆稿荐不相上下。
在平常日子里饺子并不是稀奇物,甚至有些中国人根本不爱吃饺子。但到了特殊时间、特殊地点,最能表达中国情怀、安慰中国胃的,非饺子莫属,饺子馅又非韭菜莫属。有一年春节弟弟没有回家,在莫斯科过节,除夕年夜饭,大家怀着悲壮的心情一致决定:再难也要吃顿饺子。
弟弟所住的楼层住着三个地方的中国人,江浙人,中原人,东北人。别看都在俄罗斯混事儿,平时这仨地方的中国人并不团结,春节到了,仨地方的人都没回国,共同的味蕾让这一小撮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国人走到一起来了。大家商议一起过除夕,一起做年夜饭。
江浙人自告奋勇提供卤肉,东北人贡献出了自家腌制的朝鲜泡菜,别看泡菜不值钱,但在到处是黄油和牛排的地方,这加了大蒜、辣椒和醋腌制出来的朝鲜泡菜,就是珍馐美味。轮到弟弟这几个中原小伙,他们承揽了年菜里的重头戏——饺子,还必须是韭菜馅滴。
饺子馅的肉好解决,酱油也有,面粉也能买到,剩下最关键的就是韭菜了。俄罗斯人也吃韭菜,但他们对待韭菜就像我们对待芫荽,是用来调味的,一锅浓汤煮好了,放几根韭菜进去,既好看又调味。整个莫斯科也没有大批卖韭菜的,都是在地铁口的一些老太太,胳膊挎着小篮子,里面放着捆成一小捆儿一小捆儿的韭菜,每捆大概拇指粗细,有十几根,每个篮子里只放十来捆儿,卖完就走。
除夕那天一早,几个中原小伙起了个大早,拿出莫斯科地铁图,分配区域、制定买韭菜路线。他们兵分三路,挑选三条繁华地铁线,每一路直扑一条!为避免在蛛网般复杂的地铁里迷路,每组人都将自己的线路在地图上标注出来,写上汉语。并约定好,不出站,只在站口找到卖韭菜的老太太,买完韭菜原路返回地铁,继续下一站。就这样,弟弟和几个同事跑了一个上午,大约经过了几十个地铁站,小半个莫斯科,买了无数个老太太的韭菜,这才买够了包饺子的份量。
除夕晚上的大餐,经过艰苦卓绝的准备,终于端上餐桌,浓香四溢的酱猪蹄、猪大肠,开胃爽口的辣白菜,口味清淡的蔬菜沙拉,烤面包。午夜时分,最隆重的大菜——饺子上桌了,热腾腾的饺子一端出来,气氛就达到了高潮。韭菜馅饺子的鲜香,顿时弥漫这栋异国他乡的小楼。一个小伙子吃了几个饺子之后,突然趴在桌子上嚎啕大哭,众人惊问他怎么了?小伙子嘴里含着饺子,眼里含着泪,呜咽地说:我想我妈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