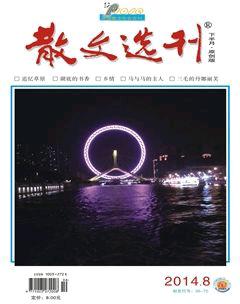十年读书得苎萝
方怀银
《<读书>十年》,是扬之水先生在《读书》杂志社工作十年日记的集子,从1986年12月18日到杂志社报到,至1996年4月调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皇皇三大本。十年光阴,她如何由作者变成编者,由开卡车的初中生转变成名物研究者,“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如此熟练地驰骋在文化学术的大道上”(沈昌文),透过这些拉拉杂杂的日记可窥得一二。
先生的工作生活较为简单,编杂志、买书、读书是主旋律。编杂志是其工作,也是“所不乐者”。在1989年1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
忙乱一周,终于可以坐下来静静读书了。年来过手之卷,怕也有千数了罢,读至忘情处,直是全然忘却书外的一切,唯此为乐。明白陷入其中是为大忌,但已知自己非学问中人,便做一书囊、书痴,乃至书橱,岂不也是人生一种。钱钟书有论:“读书以极其至,一事也;以读书为其极致,又一事也。”而今我即取此后者为事,就最得人生之趣,故长快乐。所不乐者,是仍需勉力工作,以赚取购书之资。好在供职于《读书》,总算不稍离于书。
读书与工作的矛盾是很多喜欢读书之人的两难选择,读书就要买书,买书得有钞票。以读书为谋生者毕竟少之又少,职业读书也不一定快乐。“窃以为读书本身就是生活,则乐在其中矣。至若视读书为了什么什么而为生活,则生活乃成苦事也。”(1987年4月20日,日记日期,下同。)
当然,她在《读书》,藉工作之便,还是较容易得到一些书。“得五册赠书,所喜者:《西周册命制度研究》《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黑格尔戏剧美学初探》。”(1987年1月20日)对于连张中行都甘拜下风,读书勤和快的“奇女”来说,这远远不够,买书便成了她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普通工薪家庭,有时也得掂量掂量。“在王府井曾见一部上下册的《说库》,意欲买下,一看定价36元,还是和志仁商量下罢。晚间与他说起,竟爽快同意,真是喜出望外。”(1987年1月27日)如小女孩得到心仪许久的洋娃娃。有时就没那么顺利,同年4月27日的日记中有记载:“在文物出版社服务部购得《明式家具珍赏》(一百二十元)。为购这一册书,与志仁不知磨过多少次嘴皮子。”当时的120元确实是个大数目,磨破嘴皮子,最终得逞。对于买书,她如同痴女子,多少钱也不惜。“书越来越贵了,却又不得不买。明日志仁归来,检点钱囊,不知将作何说?”(1987年4月23日)如同犯错的小孩,在想着如何向家长认错。
为了买书,当时北京的书店,她估计都走了个遍,日记中提及的就有琉璃厂、王府井商务服务部、人民服务部、中华服务部、沙滩的五四书店、东单中国书店、绒线胡同、隆福寺书店等。彼时书店的生意好,服务意识就弱,有时为求一本书,“少不得千恩万谢”。
除了赠书和买书,还有其他途径得到书。一是跑腿。那时联系方式不如今天便捷,很多事情诸如约稿、送稿等都需要人跑来跑去。“她年轻,肯走路”,主编沈昌文就经常派她做“交通”。“老沈又派我往社科院送邮件。酬劳是两本书:《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将饮茶》。”(1987年6月9日)二是偷书。秉承“窃书不算偷”的传统,老沈的办公室偷得《译余废墨》《量守路学记》(1987年7月24日)。
先生兴趣庞杂,文史、建筑、音乐等无所不读。刚来杂志社,为做新书录给杂志补白,杂七杂八都有涉及,读书也快。经常是逃会读书、闭门终日读书,甚至外出在车上“卧读”。到广州坐火车三十三个小时,“除三次去厕所外,全部时间‘卧铺,读《我与你》。”(1989年3月20日至21日)
大量读书丰厚了学养,让她能够不仅仅是以编辑的身份与“旧文人”往来唱和,师从众师,在这些顶尖人物中间“熏陶出来”。徐梵澄称其“小友”、“大妹”;王世襄认其作弟子,并引导其走上名物研究之路。
沈昌文曾意外这些作家学者,对她反映奇佳。“某次去取稿一篇,金老交来五篇,都请他代为处理。他对扬之水在文化上的信任,竟如此。”或许是她性格上的“讷于言”和“不从众”,读书上的“拙”和勤快,赢得了他们的赏识与提携。
她是个读书动物,虽然羡慕张爱玲“是一只鸟,不费劲地长大了,忒愣愣就扑翅射向蓝天。我却是一只变了几变的尺蠖,只能在地上慢慢爬呀爬,爬了一辈子,也还是在地上。”(1994年1月3日)但也在读书中清晰自己的理想人生,“想当年我也曾以做‘女强人为理想之人生,近年却尽弃此图,只求一庭花草,一帘清风,一窗明月,伴我数卷诗书。”(1990年10月28日)
《读书》十年,十年读书。离开《读书》,旧文人渐渐故去,她也年届花甲,唯寂寞对时人,读书消岁月。棔柿楼还在否?故乡诸暨山高水长,苎萝山上“数间茅舍,藏万卷书”,也是读书好所在。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