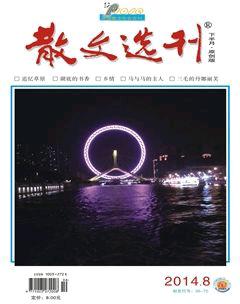日月恍惚
王芳
1
早晨,微雨,寒风割面,夹着雨丝,有凄凄的冷。
提着才买的一件棉大衣和羊毛衫,顶着风,走在横跨资江的大桥上。这桥,我还是十几年前读大学的时候认真走过,那时候喜欢看左右薄幅轻绡的水,看岸旁低矮破败的民房的灰背,想象小人物悲欢离合的故事,有无穷的趣味。可是这天我却没有闲情,因为要赶回去给父亲的老婆过生日。我原本并不记得她的生日,只是要回家看看新装修好的房子还需要什么家具,结果父亲怯怯地说,你阿姨生日呢,你也该表示点什么。
我在岁月里认输了,仔细想想,我不该嫌恶她,毕竟她也随父亲近二十年了,她并不曾对我施恶,相反,若没有她,父亲或许不能安然度过这许多岁月。只是她不够灵敏也无法贴心,且对她在我母亲去世三个月都不到就占据了我母亲的床这一点,我总无法释怀,觉得她享用了我母亲创造的一切,所以总也无法不漠然地对她。随着年龄的增长,当对生活局面的掌控权渐渐转到我的手里,我的居高临下与她的卑微迎合便那样漫不经心地在每一个我与她相处的时刻上演。
冷风吹来,我扯了一下衣领,不小心目光落到了河北岸的一栋楼上。十几年来,这条河流静静目睹着各种变迁:孩子长大,成人老去,有人生,有人死,房子拆了重新建起,店面不断被新的主人装修着……那些曾经无比熟悉的街道,已经不再是往日模样,前些天我再去,已经无法找到我当初刚刚与这城市接触时的那些树,以及在有些灰暗的楼道里追赶着嬉戏的孩子。
一栋建在河边的楼,六层,两室两厅,有公用的通道阳台和私人用的厕所,从房子里可以看到流动的资江水,而公共阳台上养着各家花,和一两只窜来窜去的小狗,冬天有太阳的时候,女人们坐在各家门口晒太阳,打毛线衣,神态悠闲,有一种睥睨一切的优越。毫无疑问,在当时这是富人区,住着既吃国家粮,又干着点个体户营生的那批人,他们的房子里,家具电器都是最新的,地板砖发出干净的釉光。
谁都不会想到二十年不到,这房子,会在一片高出许多的房子的阴影里存着,市声依旧,高地的优势会如此迅速地逝去,就像一个女人的容颜凋谢,甚至只需要一个昼夜。要知道,那时候,女主人的倨傲是那样理所当然。
2
这栋楼是我走进这个城市的第一个地标,也是一个乡村孩子对城市的第一次仰望,或者说试探。毫无疑问,这种试探是刻骨铭心的,比我经历的第一次爱情更让我魂牵梦萦,它深刻到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法逃过我记忆的那双眼睛。这当然得感谢我如今已风烛残年的父亲和对我开始谄媚微笑的继母。
当时,父亲还不算老,而继母还很年轻,三十四岁,比父亲整整晚生了十五年。她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看着我母亲留给她的三个孩子,眼神里竟没有丝毫惊诧,我甚至不知道她哪里来的勇气接下这样一个烂摊子,或许只因为她对未来根本没有预测,也不具有判断我父亲能够给出的幸福的能力?她素来木讷,从一开始就令我觉得她的人生比一只狗或是一棵树强不了多少。但我父亲喜欢她,比喜欢我聪慧的母亲要多得多。我看到他们恩爱白头的样子,决心永远离开这个家。
那年春天,母亲离开;夏天,她进来;秋天,我进入大学中文系。父亲说,除了开学要交的这些,我没有能力养你了。我看着他,眼神里写着恨,因为我知道,继母的儿子读书也需要钱,她用她那傻傻的神情毫不费力地从我父亲那里得到支持。我咬着牙说,放心,我会自己去赚,
那一年我十七岁。为了活下去,我到桥下批发市场一家一家门脸去问,阿姨,你们需要家教吗?一直问到一个化妆品批发店面,一个皮肤白皙的女人看了我一眼说,能教六年级吗?我使劲点头,能。她旁边一个男人,黑黑的脸,敦实的身材,横扫我一眼问,怎么算?我说,一百一个月,每周六,可以吗?女人与男人对视了一下说,可以。
就这样,我在毫无防备的情形下,进入了他们的豪宅,那栋有着长长的通道阳台的楼房。六年级的小女孩胖胖的,像她母亲那么白。她母亲说,那么你就周五晚上来,也顺便可以在晚上给她讲点数学,在这里吃晚饭。为了省一顿饭钱,加上有线电视的节目也吸引人,我也没有想她这其实是对我劳动的一种剥削,直到后来我成年才恍然明白这一点。小女孩属于比较笨的,由于她父亲是国家公务人员,而她母亲天天做生意,也没有谁过于在意她的成绩,所以,我也算度过了比较自由的一期,并且她也有很大的进步。
一个学期过去,四周一百,我该得五百。结果,结账时,女主人给我四百五十。我很惊讶,问,为什么?她说,说好了一百一个月呀!我无话可说,含着满满一眶眼泪离开了。在转身时,我对自己说,有一天,我也会住上这样的房子,过上他们的这种生活,并且,我会让我的继母尝尝见到我的房子却住不进去的味道。
第二学期,我接了三份家教,我也学会了与请我的家长讲价钱。我赚的钱足以让我生活得很好,并且有余钱买点我喜欢的书,或者在父亲来看我时,给他一两百。
3
在真正的城里人面前,我一直有着无法挥去的自卑,我会悄悄地对比他们的言行,然后发现他们对什么都不大惊小怪,买菜的时候会讨价还价,为了五毛钱可以与小贩吵上,但有时候他们又无比从容,面对一大桌菜肴的浪费毫不可惜。他们大多皮肤很白,穿的衣服即使很旧也会很干净,走路时显现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与优雅。
有一段时间我反复告诉自己,其实我也是城里人了,回到乡下去时,我表示出对土生土长的孩子的爱怜和对那些从地里长出的庄稼的欣喜,当然,这种欣喜不是源于我真正的亲近,而是要显示城里找不到这么干净新鲜且放心的东西。我的这种表现使我的父亲和我的继母逐渐发现了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他们只能是乡下人,而他们的女儿已经是一个城里人,在这样的城里人面前,他们开始表达欣慰和局促不安。但这样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多久,我便沮丧地发现,不管我怎么装,我还是那个我,装不了恨,也无法不真正热爱那些庄稼。
走下桥,那栋房子在视线中渐渐消失。我走向了乡下的家。
一下车,父亲和继母就迎了上来。我朝继母挤出了一个笑,用宽恕的语调说:“生日快乐,阿姨。”她接过我的礼物,一件送给她的羽绒衣,很感激地笑着说,还是我的芬儿记得我。我没有理她,转过头来对父亲说,爸爸,也给你买了羊毛衫,我帮你们试一下。
我先帮继母。最大码的衣服,她穿上去居然有点紧!我说,你太胖了,怎么可以这么胖?她不好意思又讨好地笑着,我也不知道,是在你们家过得太好了吧?你爸爸太会养人了。
父亲耳背,没听清,问,你说什么?她便尖声笑着娇嗔地白了父亲一眼,说,该听见的总听不见,说是你养胖的我!父亲嘿嘿地笑道,是的呢!语气里满是骄傲。
我皱了一下眉,她马上收了口去厨房做饭。我拿出羊毛衫,爸爸,你也试一下。
父亲顺从却艰难地脱下外套,我隐约觉察到他的手有些不方便,但七十岁的老人,也正常吧?羊毛衫总算套过头,穿进手臂,从后面扯下时卡在背上,父亲使劲去扯,左扯也扯不下,右扯也扯不下,便索性不管,任其穿得马虎就要穿外套。我笑着说,还没扯好呢,老人家。我伸手去帮他扯,一下子就扯好了。他笑了,说,老了,没用了啊!我不由一阵心酸,什么时候我这不服老的父亲,也只得承认自己的衰弱了?
去照照镜子吧,老头挺帅!父亲不好意思地笑了。
4
父亲的笑忽然使我无比难过,仔细想想,许多年来,当我为我的童年与少年遭受的种种不快而忧伤,为母亲的去世而恨意重重,把这一切清算到父亲头上时,他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他在贫穷中不可逆转地老去。他并没有为自己添半件新衣,或者杀过一只鸡独自享用,他吝啬地积攒着每一分钱,不在乎日渐佝偻起来的身材以及悄无声息爬上脸庞的皱纹。然后,在他七十岁这一年,一咬牙,拿出所有的积蓄装修房子。
我一直反对他修房子。人都这么老了,房子凑合着能住就行,可是父亲执意要修。他找到各种理由,让他身边的朋友和亲人帮他一起说服我。他说,其实他只是希望每年我们回家时不要急着离开,在他的概念里,有个好一点的地方睡觉,我便不会离开了。我曾粗暴地告诉他,即使你修好了房子,我也不会待在家里,我看着她就会想起我的母亲,我无法与她共同相处在一个屋檐下。父亲听到这样的话总是神色黯然,但他修房子的意志仍无比坚定。
房子终于修好,加了一间房,换了不锈钢门窗,吊了顶,贴了地砖,连外墙都刷白了,还加了一米多高的灰色线脚。为什么线脚不刷上绿漆呢?他说,一清二白,我喜欢这样,好看。我心里暗暗一惊,虽然已经离开城市五十几年,他却依然保存着城里人审美的直观感觉,但我没有说,而是在背着手检查时故意夸张地说,没想到这个老头还真不简单,房子弄得像别墅。我这么一说,父亲就得意地笑,还用手去捂下嘴,抹平那份得意。他一生最得意的事,是生了三个争气的孩子,如今这房子焕然一新,当然是他得意之二了。我终于懂得了一生节俭至于悭吝的父亲,花费所有积蓄完成他的房子,不过是圆一个梦,我终于懂得时光带给人的无奈。因为害怕死去时不能留给他的孩子一份属于他的骄傲与念想,他选择要造一个连年轻人都会羡慕的房子,让所有人知道他在这世上总算没有白走一遭!
我又想起了资江边的那栋代表着城市生活的房子,那曾经也是我的梦。我在一往无前地朝着梦前进时,父亲背上的担子那样重,梦,对于他而言,是渺茫而奢侈的,我那满怀着生命热情的父亲,何时丢下过属于自己的倔强呢?
照照镜子吧!我把父亲拖到镜前,他抬头看了一眼,低声说,老了,怎么穿,也是老了。年轻时候,有好样子,却只能穿城里的姐夫穿旧不要的衣服,有时候能够拿到一套完整的旧衣都觉得很幸福,如今有新衣服也是枉然啊!说到这里,父亲神情黯淡,像行将熄灭的烛火。我看到他的大拇指的指甲满满一指缝的黑东西,扯了他一把,说,爸爸,老了也要讲卫生,别把指甲弄得这样脏,你虽然是一个农民,但你是一个从城里下放到农村的诗人啊!
5
哦,这不是脏东西,是烟丝,烟丝里的血凝固,看上去就脏了。我拖过他的手,盯着看。然后我的腿骨开始一阵一阵痛,那种痛无比清晰,以至于我只能顺势坐下,因为我看到了父亲大拇指几乎砍掉了半边的伤口被那已经凝固的黑血糊成一团,血肉不分。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了父女连心。
父亲看我脸都白了,笑着说,没什么可怕的,前几天劈柴,不小心一刀砍在手指上,当时鲜血直冲,我还不觉得疼,扯了一把烟丝放上面,堵住血,谁知堵不住,流了一气。这样会发炎的,到时就不是小事了!父亲说,小意思,搁我年轻的时候,止住血还要做事呢,现在强多了,砍坏了手还能休息,柴也不劈了,只是穿衣服有点不方便。
为什么劈柴?不是给了钱烧煤么?液化气也可以。
柴可以省钱啊,你们赚钱也不容易,我不能老向你们要,再说,你们城里人不是都喜欢吃柴火饭么?我想你在家多待一些时间,所以堆点柴准备着。
我无语了。父亲,为什么在我们年少时,你不这样时时处处想着你的孩子?是你不懂得,还是我们太小不知道?而且,我出去再久,也不是城里人,我是你的女儿啊,在我的面前,你需要那样谨慎吗?
我知道,父亲从下乡的那一刻起,一直保持着对城里人的一种敬畏,但是,儿女成群的父亲,七十本该随心所欲的父亲,为什么还这样执著于这一生不能实现的城里梦呢?时光流过我们的面庞,难道不能改变的,除了山川,还有心中无法释怀的执意?我都说我与过去握手言和了,难道终于把房子修好的父亲至死也无法做到?
6
临走时,在寒风中,送我的父亲,猛烈地咳嗽起来。他感冒了。
感冒并且大拇指上有伤的父亲让我很难过,但我无法温和。我说,爸爸,不要抽烟了,这样咳,我怕你像去年那样大病一场,去年我被你害苦了,你不要再害我了啊!父亲怯怯地说,就戒烟就戒烟。那神态,像一个温顺的孩子。其实我想说的是,爸爸,时序流转,春秋代序,你的女儿已经长大,能原谅和不能原谅的一切都被抛到身后了,你如果爱我,就好好保重身体,在这世间多享几年福,以减少我在未来因失去你而生起的悲痛吧!
车子渐渐远去,远到不能看清父亲在时间深处留下的黑点,远到又回到资江边,看我少年所经历的一切,远到坐在桃花仑的十字路口,看来去的车辆,像海底虚幻的浮游生物,那些拼搏在这个城市的光阴又一层层地涌上来……
我看见岁月“轰”地一下,呼啸而去了,拖着带白烟的尾巴,渐渐彻底消失,无迹可寻。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