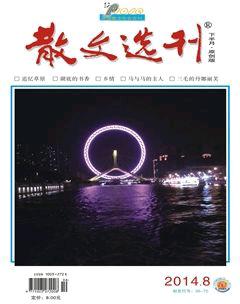月亮河
章勇
村外有一弯小河,月牙形状,父辈们都喜欢叫它“月亮河”。
我时常坐在河边,拔着绿绿的青草放在手心,柔柔地搓着,耳边传来洗衣的小媳妇那脆亮的说话声,随着棒槌的飞起溅入汩汩的水中。她原来是我家的邻居,叫甜妹,后来嫁到邻村去了,但洗衣还是在老地方,周边的村子大都在此洗衣浆晒。
我读初中的时候,她已经高中毕业回家务农了。她是家中的幺妹,一个哥哥在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那个时候,我经常找她教我不懂的功课,她也从不拒绝,我也没有感动过,因为她帮我时的神情告诉我,她就是我的亲姐姐,帮我就如她的本分一样。大约过了两年,甜妹就出嫁了,一开始她百般地不同意,嫌那男的没文化,但是男方的父亲是大队书记,如果不嫁的话,她的唯一的哥哥势必会丢了在当时还算不错的工作。
甜妹终是嫁了,在一个大雪飞舞的冬天。
我时常去邻村寻她,让她帮我解题。每次去她都热心地接待,她的没有文化的男人总是赔着笑,一边做家务,一边远远地观着我和甜妹。他们好像从未拌过嘴、斗过气,即便甜妹发脾气,他也只是站在一旁顺应着,由此一来,我倒喜欢上这个没有文化的大哥。
后来,甜妹夫妇生了一对双胞胎,并且是龙凤胎,公婆一家欢喜无常,对甜妹的生活越发呵护。生育两个小孩后,甜妹的肤色依旧润嫩,体态丰腴,更增添了风韵。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觉产生一种莫名的冲动,而且是原始的那种,我知道这是很危险的信号,因而在强迫地压抑自己时,去找甜妹的日子逐渐减少了。其实甜妹完全不知道我的心思,每次在路上碰见我,还是那么地热情和关心,堆满一脸亲切的微笑,弄得我甚至有些手足无措。有一段时间,甜妹却经常带着孩子长住娘家,尤其是暑假期间。她穿着单薄的衣衫,有时喂孩子奶时,也会掀起衣服,使我的眼睛无法躲避。
再看到甜妹,已是秋意浓浓的十月。此时的她发髻蓬乱,面色苍黄,看到我时目光不停地躲闪,像一只受伤的小鸟,羽翼折断,羽毛掉光。当我问起怎么弄成这样的时候,她总是摇头,眼睛仍然望着远方,仿佛我不再是从前那个她最关心的大弟弟,她也不再是以前那个我心底里最尊敬的姐姐。她始终没有言语,我也没有再继续追问,我们站在路边,任凭秋风抽打,秋叶满身。
秋夜里,我与母亲谈心。母亲告诉我甜妹的遭遇,说话时母亲眼圈都红了,她一边切着大白菜,一边愤恨地说,恶人终会得到恶报的!原来在我返校后,村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甜妹和她丈夫整日吵嘴打架,甜妹的身上伤痕累累,无一处好的。原因是甜妹与下放男知青有奸情,这个男知青在大队小学任教,生性厚道。甜妹喜欢看书,便常去向他借书,时间一久,村子里就闲话开了。无知的丈夫开始维护自己的尊严,没日没夜地折磨甜妹,而甜妹面对莫须有的臭名声,竟无处解释,百口莫辩。当时的大队支书更为恼火,一个下放知青居然与自己的儿媳发生奸情,于是一怒之下,免去男知青的教师之职,下到生产队劳动。从此,甜妹一直生活在没有欢乐的时光里,原本开朗的心房变得阴云密布。
此刻,我很想采摘一片天空中的云,很想暴虐一场劲雨,借一道闪电,撕开这黑暗的天空,成就一场风暴,成就一场雨淋,成就一场骨子里的蚕食,成就一场灵魂深处的挣扎与解脱。然而我不能,因为我还是个未跨出校门的学生,我身上唯一能帮助甜妹的力量,仅剩下愤怒,为莫须有的愤怒,也为那些长舌妇的愤怒。
离开村庄的那天,我与母亲专门去看了甜妹,甜妹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将我们迎进门,但却沉默着,似乎与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插图:周思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