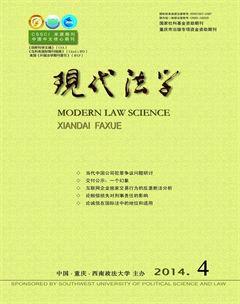对质权如何适用于科学证据

摘 要:Williams v. Illinois案反映了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的对质权应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专家证言形式的科学证据,尤其是一个专家基于另一个未出庭专家制作的法庭科学报告而出庭作证时该如何适用对质条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对质权如何适用于科学证据问题上各方观点存在严重分歧,揭示了科学证据与对质权的持续紧张关系、对质权适用于科学证据的各种处理模式以及不同处理模式所显示的刑事诉讼价值取舍与平衡。Williams v. Illinois案的判决意见对中国刑事鉴定意见对质制度的规范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对质权;科学证据;证言性陈述;《联邦证据规则》第703条;Williams v. Illinois
中图分类号:DF73
文献标识码:A
美国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在所有的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应当享有……与不利于他的证人对质的权利”,此即美国刑事诉讼中被告所享有的宪法性权利——对质权。 “Confrontation”这个单词,学界通常将其译为“对质”或“质证”。尽管对质原则已经确立并且为人们广泛接受,但是对于应当怎样广义地解释这一原则仍存在争论。(参见:克米特·L·霍尔. 牛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南[M].2版许明月, 夏登峻,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24-1025.)
198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Ohio v. Herschel Roberts一案确立了对质条款适用于传闻陈述的“可靠性标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Ohio v. Herschel Roberts一案中裁决,“传闻陈述者如果不出庭接受交叉询问,则对质条款通常要求证明其不能到庭并且该陈述具有可靠性保障,否则该传闻陈述不可采。可靠性保证可基于根深蒂固的传闻例外情形而予以推定,而在其他情况下,如果一项传闻陈述不具有特定的‘可信性标记,则该传闻陈述必须被排除”,此即罗伯茨标准,也称为“可靠性标准”。参见:Ohio v. Herschel Roberts, 100 S.Ct. 2531(1980),at 2534.
;2004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Crawford v. Washington 参见:Crawford v. Washington, 124 S.Ct. 1354(2004).
一案推翻了Roberts判例,将对质条款仅适用于“证言性陈述”;随后,联邦最高法院又分别在2009年及2011年通过Melendez-Diaz v. Massachusetts 参见:Melendez-Diaz v. Massachusetts,129 S.Ct. 2527(2009).、Bullcoming v. New Mexico
参见:Bullcoming v. New Mexico,131 S.Ct. 2705(2011).
两判例将“证言性陈述”从传统证人证言扩张至法庭科学报告(专家证言),对质权的适用范畴由此扩展至科学证据美国学者的文章中将科学证据(scientific evidence)与专家科学证据(expert scientific evidence)、科学的专家证言(scientific expertise)、科学意见(scientific opinion)、专家意见(expert opinion)、专家证据(expert evidence)视为同义语,认为科学证据属于专家证言的范畴。因此本论文及所涉判例将 “科学证据”、“专家证言”、“法庭科学报告”术语均视为相同含义术语而在不同语境下混合使用。
范畴,对质条款的适用范围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时刻。
然而,联邦最高法院始终未明确定义“证言性陈述”,由此导致“证言性陈述”的内核与边界含混不清,对质权多大程度上适用于科学证据范畴这一问题成为困扰联邦法院系统的梦魇。该问题在联邦最高法院2011年12月6日开始审理的Williams v.Illinois 参见:Williams v. Illinois,132 S.Ct. 2221(2012).
一案中得以全面显现。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被要求就一份DNA报告是否属于“证言性陈述”并受对质条款约束这一问题做出最终裁决。
Williams案集中反映了科学证据与对质权的持续紧张关系,全面展现了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在对质权如何适用于科学证据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揭示了对质权适用于科学证据的各种处理模式以及不同处理模式所显示的刑事诉讼价值取舍与平衡。
一、Williams v.Illinois案的基本案情
2000年2月10日晚,22岁的L.J被一陌生男子尾随并强奸。警方采集L.J血液样本及阴道拭子,并送至伊利诺斯州警察局(ISP)实验室。在初步检测确定阴道拭子上可能含有精液后,ISP实验室于2000年11月将阴道拭子送至马里兰州的Cellmark Diagnostics实验室进行检验,并于2001年3月收到了Cellmark出具的DNA检测报告。随后,ISP实验室的法庭科学专家Sandra Lambatos将Cellmark报告中的DNA图谱录入州DNA数据库并进行搜索比对,结果显示: Cellmark报告的DNA图谱与威廉姆斯的DNA图谱相符。2001年4月17日,警察组织列队辨认,L.J指认威廉姆斯为性侵她的人,随后威廉姆斯被以强奸、绑架、抢劫罪名指控,被告选择了法官审(而非陪审团审判)。
初审于2006年4月开始,涉及本案争议的即是控方专家Sandra Lambatos的专家证言。作为法生物学及DNA分析专家,Sandra Lambatos女士在主询问中就同一认定进行说明,即在对两个DNA图谱(即Cellmark报告中的精液DNA图谱与嫌疑人Williams的血液样品DNA图谱)进行比对过程中,一个DNA专家依赖另一个DNA专家的检验结果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二者是否比对相符的专家意见,这是一个普遍接受的实践。然而在辩方看来,控方对Sandra Lambatos进行的以下询问及Lambatos的回答是存在争议的:
控方:从受害人L.J处提取的阴道拭子中的精液中所检出的男性DNA图谱(即指Cellmark报告的DNA图谱)与威廉姆斯血液样品的男性DNA图谱经计算机比对是否相符?
Sandra Lambatos:是的,二者相符。
辩方认为,Lambatos并未参加Cellmark实验室的检验工作,也不知晓Cellmark报告中的基因图谱是否源自受害人L.J的阴道拭子;控方本应传唤Cellmark实验室人员出庭说明Cellmark的DNA图谱是否源自送检阴道拭子,然而控方并未传唤Cellmark实验室人员,而只是传唤Lambatos出庭,并通过Lambatos的推论性话语引入了作为传闻的Cellmark的DNA图谱,因此侵犯了被告的对质权。据此,辩方基于对质条款要求排除Lambatos有关Cellmark实验室检验环节的证言。
初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争点仅涉及证明力问题,而不涉及证据排除问题;同时,针对对质权异议,初审法院认为Lambatos援引Cellmark报告并非是为了证明所主张事实的真实性,而是为了解释(Lambatos的)专家意见所依据的事实基础这一有限目的,因此Lambatos的证言是基于Cellmark报告所作出的独立、客观的判断,Cellmark报告并不属于证言性陈述因而不受对质条款约束。据此,初审法院驳回了辩方有关Cellmark报告实质上构成证言以及Lambatos的专家意见侵犯了被告对质权的主张,初审法院判决认定威廉姆斯有罪。
威廉姆斯不服初审判决,分别于2008年8月27日、2010年7月15日上诉至州上诉法院、州最高法院,两级法院均驳回了辩方的对质权异议,维持了初审法院判决。2010年12月17日威廉姆斯向联邦最高法院申请调卷令,2011年6月28日联邦最高法院予以批准,并于2012年6月18日做出最终裁决。本文所关注的即是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及由此引发的争议。
二、相关历史判例及法律背景
(一)对质权适用于传统证言的历程:Crawford v. Washington (2004)—Davis v. Washington (2006)、Hammon v. Indiana (2005)—Michigan v. Bryant (2011)
200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Crawford v. Washington在Crawford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裁定,被告的妻子Sylvia Crawford在警察局询问中所做的陈述是证言性的,在被告因其妻子主张配偶特免权而没有机会进行交叉询问的情况下,下级法院采纳其妻子的陈述违反了宪法第六修正案的对质条款。
判例中指出,“对质条款禁止采纳未出庭证人的证言性陈述,除非陈述人不能到庭,并且被告人在先前已经被给予了交叉询问的机会” 参见:Crawford v. Washington, 124 S.Ct. 1354(2004) ,at 1359-1363.,确立了传闻陈述适用对质条款的“证言性陈述标准”,从而推翻了1980年Roberts判例所确立的“可靠性标准”。然而,Crawford判例对“证言性陈述”并未给出一个明确定义,联邦最高法院的意见是将定义“证言性陈述”的任务“留待将来” 参见:Crawford v. Washington, 124 S.Ct. 1354(2004) ,at 1374.。
随后,在Davis v. Washington在该案中,Davis因违反隔离令(no-contact order)并殴打被害人Michelle McCottry而受到刑事指控。审判时控方并未传唤Michelle McCottry出庭作证,而是使用了Michelle McCottry拨打911报警电话时就警察讯问所做回答的电话录音作为证据,Davis提出了对质权异议。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认定该案中911电话录音属于持续紧急情况下被害人针对警察讯问所作陈述,不属于证言性陈述,因而采纳该电话录音并未侵犯被告的对质权。
和Hammon v. Indiana在该案中,Hammon因殴打其妻子Amy而受到刑事指控。审判时控方并未传唤Amy出庭作证,而是使用了警察到达现场后在隔离开Hammon和Amy的情况下对Amy所做的、经宣誓的正式讯问笔录作为证据,对此Hammon提出了对质权异议。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认定该案中Amy针对警察讯问所作的、经宣誓的正式讯问笔录是证言性陈述,因为讯问目的不是针对持续紧急情况,而是为收集指控证据,因此采纳Amy的书面证言侵犯了被告的对质权。
两起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进行合并审理并在判决中指出,“如果陈述是在警察讯问的过程中做出,而当时的情形客观地表明讯问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警察应对持续的紧急情况,则该陈述就不是证言性的(即不受对质条款约束)。如果当时的情况客观地表明没有持续的紧急情况,而且讯问的主要目的是为日后刑事诉讼提供指控证据,则该陈述就是证言性的(即受对质条款约束)”。 参见:Davis v. Washington, Hammon v. Indiana,126 S.Ct. 2266 (2006) ,at 2273-2274.
此即“证言性陈述”定义的“主要目的标准”依据上述界定,“主要目的目标”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子标准,即“紧急情况标准”(the ongoing emergency test)与提供审判证据的“指控标准”(the accusation test),前者不属于“证言性陈述”(即属于“非证言性陈述”),后者属于“证言性陈述”。,通过该界定,对质条款仅适用于证言性陈述,并通过“主要目的标准”初步勾勒出“证言性陈述”的内核与边界,解决了对质权适用范围的问题;随后联邦最高法院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根据克劳弗德案……对质条款不适用于非证言性的庭外陈述” 参见:Whorton v. Bockting,127 S.Ct. 1173,1184(2007).。
但是,证言性陈述的“内核”与“边界”在何处、有无一个清晰的界线,戴维斯标准与克劳福德标准均未解决这一问题。这一问题在2011年联邦最高法院审理Michigan v. Bryant案2001年4月29日凌晨3:25,密歇根州警察受理一起枪击案报警,随后在底特律一处加油站停车场发现了因受枪伤而生命垂危的Anthony Covington。在救护车到达前几分钟,警察询问Covington有关枪击案发生过程、地点及枪手情况,Covington均予以回答并说“Rick”是枪杀他的凶手;随后,Covington被迅速送医院抢救,但于几小时后不治身亡。该案初审时值联邦最高法院的Crawford判例及Davis判例最终判决之前,警察出庭就被害人Covington临终前向警察所作陈述出庭作证,依据该证言及其他证据,陪审团以二级谋杀裁定Bryant有罪。涉及对质权异议的是Covington临终(激情)陈述是否属于证言性陈述,联邦最高法院经审理后认为,Davis判例是类似本案情形的有约束力的先例,Covington临终前向警察所作陈述不是证言性陈述,因此初审法院采纳该陈述并未侵犯被告的对质权。
时再次显现,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裁定死者Anthony Covington向警察所作临终陈述不是“证言性陈述”,因为警察的讯问目的在于回应“持续紧急情况”。联邦最高法院在评估何为“持续紧急情况”时,不再仅仅依靠对被害人所造成的危险,而将其评估重点转向于对执法官员及公众造成的持续危险 参见:Michigan v. Bryant, 131 S.Ct. 1143,at 1146-1149.
,因此Bryant案扩展了戴维斯案就“持续紧急情况”的认定范畴。这一判决招致斯卡利亚、金斯伯格大法官以及众多评论者的批评,他们认为,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对“持续紧急情况”的扩展性解释,无疑敲响了克劳福德的丧钟,批评者担心控方不经对质而使用几乎所有陈述,只要警方辩称其获取证言是为了应对针对公众安全的潜在威胁这一目的,因此对质条款为被告设计提供的保障功能事实上不能为被告提供任何保障 参见:Richard D. Friedman,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the Bryant Decision[EB/OL].[2014-03-01]. http:// confrontationright.blogspot.com/2011/03/preliminary-thoughts-on-bryant-decision.html.。
上述判例体系反映了对质权适用于传统证言(尤其是警察讯问)的历程,然而由于“证言性陈述”标准的不确定性,其势必导致对质权适用范围模糊不清,预示着对质权适用于科学证据时可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
(二)对质权向科学证据领域的扩张[1]:Melendez-Diaz v. Massachusetts(2009年)、Bullcoming v. New Mexico(2011年)
在Crawford的里程碑式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始终未回答法庭科学实验室检验报告这类科学证据是否属于“证言性陈述”从而应当受对质条款约束这一问题。2009年联邦最高法院在Melendez-Diaz v. Massachusetts案中首次裁定科学证据属于“证言性陈述”的核心内容,其后更是通过Bullcoming v. New Mexico(2011年)一案强化了Melendez-Diaz案所确立的判例原则,从此,对质权的适用对象从刑事案件中的传统证人证言扩展至科学证据范畴。
Melendez-Diaz案中涉及对质权异议的是一份由法庭科学专家出具的可卡因检验报告,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该法庭科学报告显然符合对质条款关于“证言性陈述的核心分类”,因为其具备明确的证据目的:该法庭科学报告必然使得一个客观的证人(an objective witness)可以合理相信该报告将必然用于以后的审判。最高法院据此裁定,被告有权对出具报告的法庭科学专家进行交叉询问,被告的对质权也并不因为法庭科学报告或法庭科学专家具有如下特质而免除:法庭科学专家既不同于传统目击证人,亦不同于指控性证人(“accusatory” witnesses);法庭科学报告具有中立性、科学性保障;法庭科学报告属于官方及业务记录的传闻例外。
Bullcoming案中涉及对质权异议的是一份由法庭科学专家Caylor签名的血液酒精度检测报告。与本应传唤Caylor出庭对质的正确作法不同,控方却传唤同一实验室内另一个并未实施或观察该报告实际检验过程的专家Razatos代为出庭提供证言。联邦最高法院遵循Melendez–Diaz先例认为:用“代理专家”来替代检验分析人员出庭并不能满足对质条款,“被告的诉讼权利就是与出具检测报告的分析检验人员本人当面对质”。
上述两案均以5:4的微弱优势裁定对质权适用于法庭科学报告,反映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在对质权如何适用于科学证据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这一态势在Williams v. Illinois案中更是集中显现。
(三)关于《联邦证据规则》第703条
根据《联邦证据规则》第703条规定,“专家意见所依据的事实或者数据,可以是该专家意识到或者亲身观察到的案件中的事实或者数据。如果特定领域的专家就某事项形成意见时将合理依赖这些事实或者数据,则不必要为了采纳专家证言而要求这些事实或数据已作为可采证据提交换言之,专家证言本身是诉讼证据,当然涉及证言的可采性问题;但专家证言依据的事实或数据并不是诉讼证据,因此不必将其可采性作为采纳专家证言的前提条件。(参见:Ross Andrew Oliver,Testimonial Hearsay as the Basis for Expert Opinion: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Confrontation Clause and Federal Rule of Evidence 703 after Crawford v. Washington[J]. Hastinqs Law, Tournal, 2004,(5)1552.)
。但是如果这些事实或数据本来不可采,则只有在其帮助陪审团评价专家意见方面的证明价值明显超过其损害效果如混淆争点、误导陪审团等风险。
的情况下,专家证人才可以向陪审团披露上述事实或数据。”参见:Rule 703. Bases of an Experts Opinion Testimony.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2013).
由于刑事案件中个体识别技术(如嫌疑人同一认定、枪支同一认定等)、死因、中毒原因分析等常常依赖作为专家意见基础的其他实验室专家的检验数据,因此一个专家以另一个专家出具的法庭科学报告为基础而形成其专家意见的情形在刑事诉讼中颇为常见,在Roberts规则时代,这些专家意见更因其“可信赖性”标签而成为“根深蒂固的传闻例外”;然而,作为刑事被告人所享有的宪法性权利,在Crawford规则时代,对质条款又要求对传闻陈述者进行交叉询问,因此,《联邦证据规则》第703条与克劳福德的对质要求间的冲突已成不争事实。然而,Melendez–Diaz及Bullcoming先例均未涉及703规则情形下作为专家证言基础的庭外陈述该如何适用对质条款的问题,这导致下级法院适用Melendez判例的做法混乱纷呈。
多数法院认为,作为专家意见基础的未出庭专家的庭外陈述并不必然暗含被告人的对质权,因为其目的并不必然是为了证明所主张的事实真相,而仅是为了阐述专家意见的形成基础;此时,作为专家意见基础的庭外陈述并不属于证言性陈述,因此不受对质条款约束。参见:Ian Volek Federal Rule of Evidence 703: The Back Door and the Confrontation Clause, Ten Years Later[J]. Fordham Law Review, 2011,(80):993.
这无疑削减了Melendez–Diaz及Bullcoming判例所确定的对质权适用范围,显示了下级法院对于科学证据可靠性的过分信赖及对法庭科学专家的袒护。同时,《联邦证据规则》第703条也成为控方利用专家意见规避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对质条款的常用手法。
但与之相反,纽约州上诉法院参见:People v. Goldstein,843 N.E.2d 727, 732–34 (N.Y. 2005).
及马里兰州上诉法院参见:Derr v. State,29 A.3d 533 (Md. 2011).
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裁决,认为对质条款禁止采纳庭外专家证言,即使《联邦证据规则》第703条情形下作为专家意见证言合理基础的其他未出庭专家的法庭科学报告也不例外,从而坚守了Melendez–Diaz及Bullcoming先例将对质权无一例外适用于所有专家证言的基本立场。
现在,联邦最高法院在Williams v. Illinois案中再次面对这一分歧,并有机会裁定作为专家意见合理根据的庭外专家证言(本案即指Cellmark报告)是否构成证言性传闻从而应当受对质条款约束。
三、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Williams案”中的各种不同意见
2011年12月6日,联邦最高法院对控辩双方的口头辩论进行听审,驳回了辩方的证据排除动议,确认了Lambatos证言及Cellmark报告的可采性与证明力,而将双方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对质权异议:(1)“传闻目的”审查:Lambatos证言中援引Cellmark报告是否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真实性为目的?(2)“证言性”审查:Cellmark报告是否是证言性的?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及相关学术文献中,在不同语境下交替使用“证言性陈述”或“证言性传闻”,二者含义实质相同,在确定一项庭外陈述是否属于克劳福德的“证言性陈述”或“证言性传闻”时,就必须从“传闻目的”与“证言性”两方面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属于对质条款的适用对象。
2012年6月18日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终审裁决,以下是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不同意见的简要归纳:
(一)阿利托(罗伯茨、肯尼迪、布雷耶)的相对多数意见判决
阿利托大法官撰写了本案的多数意见判决,裁定Cellmark报告不属于证言性陈述,被告的对质权未受侵犯。作为第一个争点,阿利托法官认为,Cellmark报告中所包含的、被法庭科学专家Lambatos披露的任何事实并不是为了真实性证明之“传闻目的”,而仅限于用来确定Cellmark基因图谱与数据库中某个前科人员基因图谱是否相符这一“有限目的”。作为第二个争点,阿利托法官认为,即便Cellmark报告是为了真实性证明之目的,其也不属于证言,因为“Cellmark报告并不具备对实施犯罪的特定嫌疑人进行指控的主要目的”。因为Cellmark报告的主要目的是为(紧急情况下)抓捕危险的强奸犯,而不是为获取审判中针对本案被告Williams的指控证据,既然那时候Williams既未被拘禁也未进入侦查人员视野。最后,阿利托法官还认为,“在审判中使用一个现代化的、经过认证认可的实验室专家所出具的DNA报告与历史上对质条款意图消除的、传统证人庭外陈述的不可靠性状况完全不存在相似性,这意味着Lambatos援引Cellmark报告并不违反对质条款。
(二)布雷耶、托马斯的协同意见
布雷耶对多数意见判决表示协同,但既不充分相信多数意见,也不充分相信反对方意见,他坚持认为,就法庭科学报告而言,为满足被告的对质权,需要深入论证以决定在何种情况下、何人必须出庭作证。在缺乏进一步的论证的情况下,法庭科学报告应当被推定免予对质条款约束。他对这一点观点的论证更多的建立于现代法庭科学实验室对法庭科学报告的科学可靠性考察,他认为这些法庭科学报告都是由经过认证认可的实验室出具,法庭科学专家也是在“无知的面纱”之后诚实、勤勉地实验检验工作,因此,如果认证认可都不能阻止采纳一些错误的法庭科学证据,那么交叉询问的方式也不可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因此专家证言属于传闻例外,构成了证据法几十年来的重要内容参见:Williams v. Illinois,132 S.Ct. 2221,at 2248-49.。托马斯仅赞同判决结果,而明确反对多数意见者的第一个观点。他认为,披露一项庭外陈述(本案中指Cellmark报告)以帮助事实审理者评估专家意见与披露一项庭外陈述就是为了真实证明目的,这二者之间并无实质差别。托马斯同意多数意见者第二个观点,即Cellmark报告不是“证言性陈述”,但并不赞同多数意见者所持理由。他认为Cellmark报告之所以不属于证言性陈述,并非基于多数意见者所谓“特定嫌疑人”理由,而是因为Cellmark报告不具有正式性、庄严性特质(即书面报告中未有宣誓证词)。参见:Williams v. Illinois,132 S.Ct. 2221,at 2261-63.
(三)卡根(金斯伯格、斯卡利亚、索托马约尔)的反对意见
作为第一个争点,卡根反驳了多数意见者的“非传闻目的”观点。卡根认为,Williams案中Lambatos证言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Cellmark报告的真实性;卡根同时严肃地指出,通过对《联邦证据规则》第703条的退让,多数意见者允许检察官以借口或迂回的方式规避对质条款,这无疑是从克劳福德判例全面倒退。参见:Williams v. Illinois,132 S.Ct. 2221,at 2268-72.
作为第二个争点,卡根反驳了多数意见者所谓Cellmark报告不属于证言性陈述的观点。她认为,Lambatos的证词从功能上完全等同于Bullcoming案中的“代理人证言”,Bullcoming判例应当成为对本案判决有约束力的先例。参见:Williams v. Illinois,132 S.Ct. 2221,at 2265-68.
卡根对多数意见者(如阿利托、布雷耶法官)关于DNA证据的高可靠性与对质豁免论调也提出了严肃批评。她援引Melendez及Bull coming判例的多数意见指出,“法庭科学报告属于证言性陈述的核心范畴”参见:Melendez-Diaz v. Massachusetts,557 U.S. 305, 129 S.Ct. 2527.at 2532;See Bullcoming v, New Mexico,131 S.Ct. 2705,at 2717.
、“科学证据是否值得信赖,不是由法官决定,这是因为对质条款规定了刑事审判中证言可靠性的审查程序,这一程序就是交叉询问;仅因为证言可靠而免除对质,这无异于仅因被告明显有罪而免除陪审团审判”。参见:Williams v. Illinois,132 S.Ct. 2221,at 2273、2275.
基于上述各种不同意见的介绍,四位反对意见者及多数意见者中的托马斯大法官似乎更倾向于对质权无一例外地适用于科学证据托马斯在Melendez-Diaz、Bullcoming判例中均显示出支持对质权适用于科学证据的一贯立场,而在Williams案中之所以认为对质权不适用于Cellmark报告,仅因为Celllmark报告不具备宣誓书的庄严特质,如果Cellmark报告具备宣誓书的形式要件,托马斯定会认为其符合“证言性陈述”标准而受对质条款约束,从而加入支持对质的一方。,反对对质的法官数量相对较少(仅阿利托、肯尼迪、罗伯茨、布雷耶)。而布雷耶法官似乎更倾向于DNA类科学证据属于罗伯茨判例规则下“根深蒂固的传闻例外”而假定免受对质条款约束,复活了早已宣布死亡的罗伯茨判例的“可靠性标准”,显示出克劳福德的重大瑕疵。然而,正是由于托马斯、布雷耶对多数意见判决的协同,导致了本案“不合法的微弱多数判决”——即该判决一方面纵容法官获得他们希望看到的裁判结果,另一方面既不改变现有法律也不对未来提供指引,这无疑会使下级法院在决定遵循哪方观点时面临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涉及科学证据的对质案件中,下级法院很可能依赖于Williams案中各方意见的不同论点来寻求指引,在Melendez-Diaz、Bullcoming、Williams先例及Crawford以来有关“证言性陈述”标准的各种混淆观点中小心翼翼地进行选择。因此Williams案判决中每种观点的缺陷都变得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将不可避免地使Williams判例以后的对质学说更加混乱。
四、对质权如何适用于科学证据:基于Melendez-Diaz、Bullcoming、Williams判例体系的分析
Williams案自进入联邦最高法院审理之日起,就引起了法律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该案与Melendez–Diaz及 Bullcoming案共同构建了科学证据与对质权的关系框架,在此判例体系下,科学证据与对质权呈现何种关系状态?在对质权如何适用于科学证据问题上,当前是何种处理模式?反映了刑事诉讼价值取舍或平衡的何种变化?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
(一)科学证据与对质权的持续紧张关系
Williams案集中反映了在对质权应在多大范围适用于科学证据这一问题上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激烈的意见冲突。
反对对质的一方,往往强调科学证据的可靠性、抱怨对质程序增加了检察官及实验室专家的工作负担、导致实验室专家出庭率上升、实验室案件工作积压、浪费国家有限的专家资源、颠覆了90多年来关于科学证据的采纳规则以及至少35个州及6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传统做法参见:Melendez-Diaz v. Massachusetts,557 U.S. 305, 129 S.Ct. 2527.at 2543-2558 (Kennedy, J., dissenting).。而支持对质的一方,往往认为科学证据是“证言性陈述”的核心内容,无论其可靠性多高都应当接受严酷的交叉询问对质,这是出于对刑事被告人宪法性权利保护的需要。在Melendez案中,支持对质的一方认为反对方的观点危言耸听,也缺乏可靠的论证理由,为此,支持对质的一方更是从辩护律师心理、辩诉交易的影响、实践中“通知与请求(专家出庭)程序(Notice-and-Demand
所谓“通知与请求程序”是指控方就是否在审判中将实验室检验报告作为证据使用事先通知被告,在给予被告合理的考虑期后,被告可以请求传唤实验室专家出庭,如果专家不出庭则被告可以提出证据排除动议。参见:Ga.Code Ann. § 35–3–154.1 (2006); Tex.Code Crim. Proc. Ann., Art. 38.41, § 4 (Vernon 2005); Ohio Rev.Code Ann. § 2925.51(C) (Lexis 2006).
)”的积极作用以及实证分析的角度予以反驳,说明将对质条款适用于科学证据并未导致实验室专家出庭率激增、案件积压及被告滥用请求权的现象,因此也不存在削弱刑事司法系统的弊端。参见:Melendez-Diaz v. Massachusetts,557 U.S. 305, 129 S.Ct. 2527.at 2540-2542 (Scalia, J.,plurality).
事实上,在对质条款是否应当适用于科学证据这一问题上,上述激烈的意见冲突并不是在Williams案中才凸显出来,下表即反映出了Melendez、Bull coming、Williams判例以来联邦最高法院系统在科学证据与对质权适用问题上的持续对立而又旗鼓相当的激烈意见冲突(附表),这势必给下级法院适用对质条款带来极大的困扰。
(二)对质权适用于科学证据的各种处理模式
从Melendez–Diaz、Bullcoming及Williams的判例体系看,在对质权如何适用于科学证据问题上,显示出三种不同的处理模式:
其一,针对单纯形式的法庭科学报告(如可卡因检验报告、血液酒精度检测报告等),该类科学证据在案件中作为实质证据提交,该法庭科学证据将直接使被告归罪或免罪。在专家证人能够到庭的情况下,往往适用Melendez–Diaz及Bullcoming先例,对质权无一例外地适用于法庭科学报告,毕竟Melendez–Diaz、Bullcoming先例针对此种情形给出了清晰的裁决意见。
其二,针对Williams个案本身的特定案件情况,或者专家证人确实不能到庭(如审判期间死亡等)而所涉法庭科学报告的可靠性又极高的情形,则法庭科学报告应假定为传闻例外对待,从而免受对质权约束;只有当对实验室专家的资格、中立性或法庭科学报告的可靠性存在充分怀疑理由时,假设性的传闻例外才将消失,由此可以要求控方的相关专家证人出庭对质。
以Williams个案为例,由于现代法庭科学技术在DNA鉴定技术领域的高可靠性,加之该案并不缺乏有关Cellmark所检精液源自L.J阴道拭子的充分可靠的证据,因此DNA同一认定比对相符的专家意见可靠性极高,此时,作为该专家证言合理根据的庭外专家证言(如本案的Cellmark报告)一般应当推定免受对质条款约束。但是,比对不相符的检验结果却未必一定可靠,因为完全存在比对样本弄混的情况,此时对质豁免条件消失,由此可以要求专家出庭对质。这恰是布雷耶大法官协同意见所主张的处理方式。
对于这种可靠性极高的科学证据情形,Williams案相对多数意见判决无不显示出对质权适用于科学证据时适用范围的缩减,以及向罗伯茨判例的可靠性规则或隐或现的靠近。种种迹象表明,联邦最高法院系统开始削弱Melendez–Diaz、Bullcoming判例将对质权过度扩张至科学证据领域的不利影响。
其三,作为专家证言合理根据的未出庭专家制作的法庭科学报告(即703规则情形)该如何适用对质条款,往往由法官自由裁量。703规则情形下该如何适用对质条款?是适用Melendez–Diaz、Bullcoming判例的“指控标准”(其主要目的是为日后审判提供证据)?还是适用Williams个案的“特定嫌疑人标准”?还是适用托马斯法官的“庄严性标准”?抑或不加区分地、笼统地适用Williams案相对多数意见而裁定所有作为专家证言合理根据的法庭科学报告均不受对质条款约束?由于Williams案含混不清的裁决理由及各方意见的严重分歧,各下级法院适用判例的做法大相径庭,这就为下级法院的自由裁量留下了空间。事实上,在williams案裁决后不久,这些不同作法即在Hall v. Texas参见:Nos. 05-10-0084-CR, 05-10-0085-CR, 05-10-00086-CR, 05-10-00087-CR, 2012 WL 3174130 (Tex. App. Ct. Aug. 7,2012),at **7-8.[ZW)〗、Wisconsin v. Deadwiller参见:Nos. 2010AP2363-CR, 2010AP2364-CR, 2012 WL 2742198 (Wis. Ct. App. July 10, 2012),at *5.
、United States v. Pablo参见:No. 09-2091, 2012 WL 3860016 (10th Cir. Sept. 6, 2012),at *8.
等案中显现出来,预示着对质权适用于此类复杂科学证据问题时并不明朗的前景。
(三)科学证据的对质与豁免: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取舍与平衡
在涉及科学证据的对质案件中,决定何种情况下、何人应否出庭对质,这并非纯粹是一个对科学证据可靠性进行法庭审查的技术操作程序,不同判例情形所作判决往往反映了正当程序、真实发现与诉讼效率三大主要刑事诉讼价值目标间的平衡与取舍。前文有关对质权适用于科学证据的几种处理模式无不体现了不同情形下各有侧重的诉讼价值目标追求:
其一,对于单纯形式的法庭科学报告,在专家证人能够到庭的情况下无一例外地适用对质条款,主要强调正当程序法律要求及交叉询问的真实发现功能,而诉讼效率目标往往被弱化。
其二,针对Williams个案本身中作为专家证言基础的可靠性极高的法庭科学报告,或者专家证人不能到庭(如死亡、离职等)而其庭前证言又具备极高的可靠性保障时,此类科学证据往往不受对质条款约束,此时主要强调真实发现、诉讼效率的价值目标,而正当程序价值目标往往被弱化。
其三,对于703规则情形的复杂法庭科学报告,对质权是否及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此类复杂科学证据,法官往往依据个案情况及对既往判例中各方观点的自由选择以确定是否适用对质条款,此时正当程序、真实发现与诉讼效率的不同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取舍或平衡完全由法官自由决定。
五、Williams判例对于中国刑事鉴定意见对质制度规范化的启示
在美国,对质权是刑事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同样,这一权利也为《欧洲人权公约》所确认参见:3(d), Article 6 ,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也是绝大多数国家赋予刑事被告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在我国,法律上虽然未采用“对质权”这一术语,然而鉴定意见作为科学证据的核心范畴,鉴定人出庭作证并接受控辩双方询问无疑属于刑事被告人对质权的核心内容。通过Williams案及Melendez–Diaz、Bullcoming先例不难发现,科学证据与对质权的复杂关系不仅是中国诉讼法律程序关注的问题,同样也是一向注重正当法律程序的对抗制诉讼制度所关注的问题,事实上也是大陆法系国家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科学证据的对质判例所反映出的三种处理模式以及不同刑事诉讼价值的取舍与平衡,对于合理借鉴域外经验,理性看待并分析科学证据与对质权的关系,剖析并解决中国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自身的特殊问题,从而实现刑事鉴定意见对质的规范化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刑事鉴定意见对质的中国问题
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前,针对鉴定意见对质,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实践中鉴定人很少出庭,未出庭鉴定人的书面鉴定意见很少被排除;二是鉴定意见质证的空洞与形式化,出不出庭与鉴定意见是否采信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反映出裁判者预断对鉴定意见采信的影响以及对于科学证据的盲从。
新《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该条文强化了鉴定人的出庭义务,规定了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情况下鉴定意见的强制排除,对于促进刑事鉴定意见的法庭对质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的调研状况却表明,鉴定人出庭率并无明显提升,鉴定意见的法庭对质效果也并无实质好转[2]。具体表现如下:
1.批准鉴定人出庭的条件过于苛刻,法院享有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
依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87条,决定鉴定人应否出庭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当事人异议及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出庭必要性,这种做法反映出职权主义的证据调查传统。但是何为“有必要”?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相关司法解释,都未给出明确规定,这就为裁判者滥用决定权留下了空间。
2.刑事鉴定意见的对质实践混乱无序,对于何种情况下、何人应否出庭缺乏必要规定。
这可能导致本来具备不能到庭的不可抗情形却将鉴定意见排除的情况,更多情况下则是应当出庭却不出庭或者根本不知道该类情形下是否应当通知鉴定专家(或非鉴定专家)出庭。在此以笔者调研过程中所获得的鉴定人出庭对质情形进行说明。
被告因多次向卧底警察销售可卡因而被刑事指控,涉及鉴定人出庭争议的是由该局鉴定人A和B共同署名的可卡因检验报告。但是不巧的是,在审判期间,出具报告的两名鉴定专家一名在审判前已离世,而另一名也已离职,于是由同一实验室的另两名专家基于前述未到庭专家的可卡因检验报告出庭接受控辩双方质询。此种情况下出庭专家的证言是否可采?
另一情形是,在法医鉴定领域,经常要依据医院或其他实验室出具的化验单、病理切片检验报告、毒物分析报告等出具最后的法医检验报告,此时,一份专家报告往往涉及层层叠加的、类似中转接力的、一个专家依据另一个专家的检验报告而得出最终专家意见的情形,此即Williams判例中的703规则情形,那么在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下,是否有必要传唤所有涉及的几十名技术专家出庭作证?
上述法律规定及实践情形均表明针对刑事鉴定意见的对质尚缺乏充分有效的保障,也显示出鉴定人出庭对质问题的复杂性,更突显了对何种情况、何人应否出庭进行规范的现实必要性。
(二)刑事鉴定意见对质的规范路径
针对中国刑事鉴定意见对质的不规范现象,笔者认为应借鉴美国有关科学证据的对质实践,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破解刑事鉴定意见的对质难题,从而实现对质的规范化:
1.放宽鉴定人出庭必要性条件限制,借鉴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将鉴定人出庭必要性审查仅视为可选条件,充分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对质权,体现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
之所以降低必要性审查的门槛,是因为刑事鉴定意见本来就已表现为由控方垄断的单边主义特性参见:Wes R.Porter,Expert Witnesses:Criminal Cases.
,如果在申请鉴定人出庭对质问题上进一步设置苛刻的“必要性审查”条件,势必进一步加剧控辩失衡态势,不利于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亦不能满足正当法律程序及公正审判的要求。
2.对于何种情况下应否传唤鉴定人出庭对质做出必要的规定,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在笔者看来,可以通过完善司法解释的方式,从消极、积极两方面对鉴定人出庭必要性审查进行规范,从而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消极方面规范可以借鉴《刑事诉讼法》有关证人不出庭的规定,即“鉴定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无法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其不出庭:(一)在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二)居所远离开庭地点且交通极为不便的;(三)身处国外短期无法回国的;(四)有其他客观原因,确实无法出庭的。具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可以通过视频等方式作证”。
而积极规范可如是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通知鉴定人出庭:(一)鉴定结论明显存在疑点的;(二)鉴定文书阐释不清或存在明显矛盾的;(三)鉴定意见与其他证据材料相反或存在严重分歧的;(四)存在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等多种鉴定意见情形,且鉴定意见间不一致的情形;(五)鉴定意见所涉问题专业性很强的;(六)鉴定意见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七)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八)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人民法院已决定鉴定人出庭的”。
3.适度确立对质权适用豁免的传闻例外情形,优先保障刑事诉讼效率与真实发现功能,实现刑事诉讼效率、真实发现与正当法律程序间的合理平衡。
考虑到刑事诉讼追诉犯罪的需要,在处理对质权与鉴定意见的关系时,若鉴定人(或专家)确因前述消极原因不能出庭或者涉及诸如层层叠加的以公共业务记录面目出现的专家意见,在其庭前证言可靠性极高的情况下,应当借鉴罗伯茨规则“根深蒂固的传闻例外情形”而适用对质豁免,从而优先保障刑事诉讼效率与真实发现功能,实现刑事诉讼效率、真实发现功能与正当法律程序间的合理平衡。
参照美国有关科学证据的对质豁免情形,这些根深蒂固的传闻例外可以是《联邦证据规则》的下列情形:第703条(作为专家意见证言合理根据的“准传闻规则例外”[3])、第803(6)条(日常业务活动记录例外)、第803(8)条(公共记录例外)以及第804条(陈述人因死亡而不能出庭作证或者陈述人缺席审判或听证,且不能通过传票或其他手段促使其到庭)等。
尽管如此,由于“法庭科学制度,包括研究和实践都存在严重问题”[4],从远景考虑,解决刑事鉴定意见的对质问题仍需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本身进行刮骨疗毒式的治理,否则,当下刑事鉴定意见对质中的顽疾仍可能得不到彻底治理。
参考文献:
[1] 王跃.对质权演进评述——以克劳德判例为观察起点[J].当代法学,2014,(2):111-112.
[2] 龙宗智.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半年初判[J].清华法学,2013,(5):136-137.
[3]约翰·W·斯特龙麦考密克论证据[M].汤维建,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617-618.
[4] 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美国法庭科学的加强之路[M].王进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
Abstract:The Williams v. Illinois case reflects that to what extent the confrontation right provided in the Sixth Amendment of U.S Constitution can be applied to the scientific expertise,especially when an expert witness testifies on the basis of a forensic lab report prepared by another expert who is absent in the trail. The U.S Supreme Court is widely divided on the topic of how the confrontation right apply to scientific expertise,which reveals the continuous tension and their relation patterns between scientific expertise and confrontation right,also shows its selection or balance of criminal procedural virtues. Undoubtedly,the Williams` decision has important instruction and reference value to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criminal appraisal system.
Key Words: confrontation right;scientific expertise; testimonial statements; FRE 703; Williams v. Illinois
本文责任编辑:周玉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