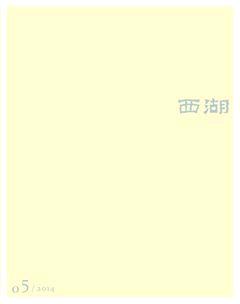一个星期里的家什杂碎
苏建平
[星期一 水龙头]男人是被女人的话吵醒的。一大早,女人在厨房里叫了起来:“这个水龙头也不行了!”一开始,女人的声音比较远,感觉像是楼下人家在说话,朦朦胧胧的。这声音把男人从梦里拉回到半醒状态。接着,伴随着踢踢踏踏的脚步声,这个声音渐渐大起来:“喂,你倒是听到没有?死掉了啊?”男人睁开眼,看着女人叉着腰,正在床边盯着他。他很想说句话回答女人,但他不但没有说话,连嘴皮都没动一下。那可不是他的本意,但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为什么没有回答。他重新闭上眼睛。女人在床边喘着粗气,突然一跺脚,“咚咚咚”地走到客厅里。男人听到“咣当”的碰撞声,大概是椅子撞在了木地板上。紧接着第二个声音传了过来:门在极短暂地开了一下后,响亮地碰上了,撞得墙壁在微微震动。
男人又睡了一阵才起床。放了隔夜尿后,他去拧水龙头。这时,他才想起大小两个卫生间的水龙头早就坏了。一直没修。没修的后果是:早上的洗漱都转移到了厨房。他走进了厨房,一眼看到水龙头的下部在往外滋水,水不大,直接滋进了水槽里,发出轻微的“嘶嘶”声。
男人快速地洗了脸,又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根香蕉,最后泡了一杯浓茶。他坐在厨房边上的餐厅兼书房,打开笔记本电脑,点开一个空的word文档,写下了文章的标题。这一天厂里放假,说穿了是遇到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厂里不景气,生意有一搭没一搭的。男人早就计划好要利用这段暂时下岗的日子,写一篇构思已久的文章。标题写完后,男人愣着,想第一句话该怎么写。这时,厨房水龙头水往外滋的“嘶嘶”声传了过来。他皱皱眉,这声音就好像越来越响。他起身察看了一下,龙头里的水没有变大,使水声变大的是周围的一片寂静。他拉上了厨房的门,本以为不听为静,但他很快发现,这水声硬是犟头犟脑地穿透了门,钻进了他的耳朵。他想了想,找了一个水桶,接了满满一桶水,便把水龙头总闸给关了。
他第三次坐在电脑前,开始与文章搏斗。厨房水龙头没了滋水声,室内重新回到一片宁静。但这片宁静没有为他带来灵感:水声虽然消失了,但在写出文章的第一句话之前,早上由水龙头坏了而引发的女人的叫喊声和桌椅的砰砰撞击声却抢先浮现了出来,牢牢地占据了他大脑的想象空间。这令他更难对付:滋水声可以关掉,但大脑中女人的声音却怎么也关不掉。他在电脑前呆坐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写下一个字。
上午将近十点时,他知道这一天算是废掉了,便关闭电脑,找了一本书,到阳台上看书。天气非常好,阳光温暖。书看到第五页时,原本消失的女人声音又在阳台上出现了,像一群苍蝇或蚊子在绕着他嗡嗡叫。在这嗡嗡声中,还渐渐加进来工厂里一直窝在他心里的破烂杂碎事的嗡嗡声。他感到无限疲倦,手中的书刚一放下,就在一片暖阳中沉沉睡去了。
[星期二 水管] 早上,女人是用隔夜接在桶里的水洗漱的。她虎着左右两边脸,拿放什么东西都“砰”的一声,像是故意要撞坏它们。洗漱完毕,女人逃也似地出门上班去了。
男人起床后,发现水桶里的水竟被女人用了个底朝天。他想速战速决,接一桶水,简单洗漱,用早餐,然后转入文章当中。今天无论如何要写下一些段落,运气好的话,甚至可以写完。这篇还没写成的文章,他打算投在报纸副刊上,多多少少可以挣一点稿费。更重要的是,如果顺利,从这篇文章出发,或许可以写更多的文章,挣更多的稿费。
打开水龙头总闸门,他注意到,厨房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比平常要小得多。他并未多想,也许是水压的缘故吧。但他马上发现了原因:水声不仅来自水龙头,水槽下面柜门里的声音更响。还没等他拉开柜门,水就从柜门缝里冲了出来。厨房里顿时一片水洼。
水槽下面的水管竟然爆了。
他马上关了总闸门。水管爆了,比龙头坏了更糟糕,根本没法用水。他盯着厨房的水洼,耳朵里迅速钻进了女人的叫喊声和砰砰声。他摇摇头,通过小区门卫联系了水电工。
水电工看了一番,下了结论:水管破了,要换。
男人提出来:连龙头一起换吧。
水电工说:“龙头也坏了?”
男人说了前一天水龙头的情况。水电工点点头:“这就对了。你昨天关了龙头总闸门,今天突然又打开,因为水管老化,水压变化,水管一下子破了。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水电工一边算要换的水管长度,一边问:“这水管好多年了吧?”
男人说:有十年了。
水电工又点点头:十年了,该换了。小区里每户人家都这样,十年是个坎,是个换东西的坎。不仅水管,水龙头,还有电视机,空调,都是如此。
水电工停了一下,眨眨眼又说:十年了,男人换女人,女人换男人。都是正常事。
男人委托水电工去代购水管、龙头。对这些东西,他并不精通。虽然他也知道,委托别人,在价格上会被水电工做一些手脚。
水电工拉开架子修水管和龙头时,厨房里一片狼籍。男人什么都不能做,只好看水电工东敲西转,看这个战场般的厨房。他本想抽根烟,但想想又放弃了。烟还是放到写文章时抽吧。对于抽烟,女人不仅有意见,甚至摆出了势不两立的态度。这也是他和女人生活中的重大分歧之一。某种意义上,他作了一些让步:尽可能少抽,少抽烟意味着可以多省些钱。
水电工整整干了一个上午。结束时,从窗口飘进来小区里某些人家炒菜的油香味。这阵香味引得男人的肚子一阵蠕动,并袭上来一阵疲倦。他甚至感到自己比水电工还要疲倦:这个本该静下心来写文章的日子,又作废了。
他还作了比较:坏了的水管、龙头可以修好,但废了的日子,废了就废了,没有人能修好,拉回。这使他感到更加疲惫。
[星期三 浴缸] 女人一回家就喊累。男人注意到,女人脸色有些淡黄,像营养不良似的。她虽然穿着早晨上班时的衣服,但他想象得到女人在工厂生产线上的情景:一身蓝色的工装,在一片单调的嗡嗡声中,一刻不停地捡起又放下电子元器件。这捡起又放下的动作,大概耗时五秒钟,一小时大概要做720次,一天十二个小时要做8640次,一个月二十六天(除去四天周末休息)要做224640次。女人一个月工资奖金合起来3100块,算下来,女人一次捡起放下的动作,计价钱1分3厘。这是男人心底里为女人算过的一笔账。
他特意做了女人爱吃的菜:芹菜炒肉丝、红烧鲫鱼。他做的菜女人还是爱吃的,而且总说除了做菜,他还有什么本事呢?况且,这个家里,就两个人,没有孩子。如果有孩子,还可以带来无尽的热闹。没有孩子,说什么好呢?好像什么话都早已说光了。说光了,就得靠其他东西了:衣服啊,菜啊,等等。
吃过了晚饭,女人活泛过来,脸上的淡黄变成了淡红。她坐到电视机前,看一个又一个的综艺节目。在她看电视时,男人收拾洗涮了餐具,然后坐下来看书。这一天,他仍然没有写成文章,因为白天有一阵他突然闹肚子,上了好几趟卫生间。不上卫生间的时候,肚子总鼓鼓胀胀的。这种情况下,男人没法集中注意力,不但没写,连书都没看成。
但是,晚上男人还是没看成书:因为电视综艺节目的声音,加上女人的笑声,一波一波地分散了他的心。他引以为恨的是没有书房,如果有书房,他就可以躲起来,不受干扰地看书,写作。从一开始,他对写作抱有雄心,但在踮起脚买了房、结了婚后,他的写作伴随着油烟气和电视里的吵闹声,不再是雄心,而变成了结实的稿费。
不过,男人没有把心中的不快说出来。他看着电视机前的女人,觉得不应该给她添烦恼。后来,他索性合上书,坐到女人身边,陪她看电视。
九点半左右,综艺节目结束了。女人起身去洗澡。女人一向把洗澡当作一种享受,喜欢放一大缸热水,浸泡在水中。趁这个时候,男人重新打开了书。
将近半个小时,突然从卫生间里传来“砰”的一声,接着,女人在里面哭了起来。
原来女人在浴室里滑倒了,滑倒时,她的胳膊结结实实地磕在大理石洗手台的角上,磕破了一块皮,殷红的血流了出来。男人把女人抱进了房间,找出红药水,仔细地给涂上了,又找药用棉纱布扎了一下。他问女人:要不要去医院?女人摇摇头。
安顿好女人后,男人到浴室察看。他发现浴缸里的下水口仍然塞着,可是浴缸里的水在缓慢地减少,减少的水从浴缸与瓷砖地相连接处的缝隙往外流,流了一地,地上的水又沿着斜坡,流向浴室地面的下水口,发出清晰的声音。他还注意到,流进下水口的不仅是水,还有越来越淡的一丝女人的血。无疑,女人没有发现浴缸底部出现裂缝,在跨出浴缸时,滑了一下,一头栽倒。
男人回到卧室,告诉女人:浴缸与瓷砖地面之间开了一条缝,水是从这条裂缝里流出来弄湿地面的。
男人的话没有得到回应。女人闭着眼,身体一起一伏,似乎睡着了。
他想:继水龙头、水管之后,浴缸也出问题了。接下来还会有吗?
[星期四 移动门] 一大早,太阳热辣辣地照下来。那种热度,不仅在室外能感受到,在室内也可以感受到,似乎季节一夜之间从春天跨入了夏天。也许是感到卧室里十分闷热,女人起床后,顺手去推通向阳台的木框移动玻璃门,门“哐哐”地一阵抖动,却没有移开来。她“咦”了一声,干脆伸出两只手再推,门还是没有打开。
女人踢了一下床,说:“起来,门好像坏了。”
男人也已经起床。他试了试,也打不开门。
这门是吊轮吊着的移动门。装修时,木匠在门框上面做了一条槽,槽内安上一条不锈钢轨道,而门上则装了滑轮,把滑轮嵌入轨道,门就舒活了。十年来,这门从未卡住过,一向灵活异常。一直到女人在浴室受伤的星期三晚上,它仍好好的,丝毫没有要坏的迹象。
才过了一个晚上,它就像一个病人一样,说卡就卡住了。
男人研究了半天,感到应该是滑轮坏掉了,要不然就是轨道出了问题。两者必居其一。通过更进一步的研究,男人还发现:不仅这扇门卡住了,通往阳台的另一扇门也卡住了。这回门卡住的原因十分明确:木地板竟然弓了起来,直接顶住了门的下端,门一往上耸,上端就死死地顶在了门框的轨道上。上下都卡。
看着两扇咬住了不松口的门,女人什么也没说,带着一脸阴沉去上班了。
男人一个人的时候,想:是把浴缸和移动门的问题解决了呢,还是等上几天,先写文章?
后来,他决定:先修坏了的东西。
他先是在上午联系了水电工。水电工告诉他:浴缸见缝这个问题,靠小修小补解决不了,要把浴缸敲掉,重新再安装浴缸;或者干脆不用浴缸,只装个淋浴莲蓬头。水电工看了半天,进一步作了结论:就应该这么办,但他是不会来弄的,因为贴瓷砖这活他是不做的。结束时,水电工说:劳务费三十元。
这让男人心里很堵,什么都没解决,就几句话,水电工就挣到了三十块钱。但他还是付了这钱。整个上午他的脑子就在这三十元钱里转,写不成文章,看不成书。到了下午,他又联系了木工。
木工对两扇门有不同的看法:对因地板拱起而造成卡住的那扇门,他手一摊,表示无能为力,因为要弄好这门,除非把地板撬掉,再铺平地板,才能让门自由移动,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另一扇门,他的看法跟男人一样,应该是滑轮出了问题,可以修好。
木工修门其实非常简单:他站在梯子上,反复看门上部滑轮和轨道的状况,显得非常认真。看到后来,木工要男人找个碗盛些色拉油来,然后他用一把小刷子蘸了油,伸到轨道里抹了一阵。
抹过了油,门活络了。木工一副劳苦功高的模样,开口要劳务费。
这是第四天,上午和下午都在修东西。而晚上,女人一回家,晃着一张过分疲惫的脸,令男人几乎不敢相信那就是女人了。男人的计划再次被打乱。
东西修好的,花了钱,没修好的,也花了钱。与此相对的是男人感到郁闷和羞愧:这几天里,他一个钱也没挣到。那个已写了标题的文章,除了标题,仍然空空荡荡。
但最重要的是,有的东西竟然修不好了。一想到这点,男人愣了一下,全身皮肉和心脏都很不舒服。
[星期五 电话机] 男人准备妥当,开始敲键盘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女人打来的电话。电话里,女人说:“家里的电话机怎么打不通?拨了号码,一点动静都没有。”
男人“嗯”了一声。
女人又说:“会不会是我早上起床时,不小心把电话机碰落了,弄坏了?”
男人又“嗯”了一声。
女人说:“你检查一下吧。还有,晚上你做个豆腐鱼汤吧,买些小的鲫鱼,实惠一点。”
女人挂了电话。男人仍旧坐在电脑前,没有马上起身。他虽然盯着电脑,可是电话机像一块多余的石头,压在他的心里,怎么都搬不去,更要命的是,晚上等着下汤的几条小鲫鱼,睁着小眼睛,摆着小尾巴,吐着小泡泡,欢快活泼地在他的大脑沟回里游来游去。他呆坐了一阵,叹了口气,不得不去检查电话机。
一开始,他先检查电池。电池果然松脱了,于是他把电池按进去,让弹簧把电池死死咬住。可是他猛然想起,电池的作用仅仅是显示来电号码,与电话机能否打通毫无关系。
他掏出手机,拨了一下电话机的号码,只听到一阵比平常更快一些的“嘟、嘟、嘟”的声音。那是打不通电话时常有的急促信号声。
男人愣了好几分钟,脸上浮起恶作剧般的笑:又来了,从水(水龙头、水管)到门(移动门),再到电(电话机),排着队一个个坏下去。他想起星期二水电工格言般的话:十年是个坎,是个换东西的坎。家家户户都这样。
它们不仅自己在坏掉,如果人不小心,只要稍微碰一下它们,它们就抢着坏掉,然后一脸无赖地瘫在那里,像一坨狗屎或牛粪。
男人下午去菜场买小鲫鱼时,顺手带着坏掉了的电话机,看也不看,就丢进了小区路边的垃圾桶里。
[星期六 微波炉] 这一天,跟男人造反的是微波炉。当时,男人在热东西,他设定了两分钟的时间,可是到半分钟左右的时候,微波炉在一阵“嘎嘎”的声音后,“叮”的一声停止了工作。
这一天,早餐和中餐,男人都吃了冷饭。他觉得,天气已经开始在热起来了,冷东西吃起来其实也并不算冷。
他决定:这一天,他不去碰家里的任何东西,也不会去想任何其他事情。他要坐下来,写脑子里模模糊糊存在的那篇文章。差不多一个礼拜了,那篇文章仍像一开始他写下题目时一样模糊。
除了其他家什,他唯一要碰的东西是电脑。想到电脑,电——电——电。他坐在电脑前,不由自主地双手合十,拜了拜电脑。
这一天,电脑好使得不得了,平时在处理文档时经常出现的小问题,一个都没发生。他集中起所有的注意力,在题目下开始打字。
上午结束时,他已经写了两千多字,他的构思一点点地露出眉目来,好像一个怀孕的妇女,在三个月前,肚子一般都能遮住,过了三个月,肚子才发生质变,变得非常显眼。他边写边重读写下的字句,感到它们与他的设想完全一致。就是这个模样。
中午吃冷饭时,他下意识地瞄了微波炉一眼。一根神经跳了一下。
到了下午,他再次坐在电脑前,往下写时,竟意外地卡住了。上午结束时,最后一个句子是以逗号暂时结尾的,似乎后面有更多的句子在叫喊,要涌出来。那时他满怀信心,似乎只要看一眼这个逗号,后面的句子就会自动跳出来。现在他发现这些本该喷涌而出的句子竟失踪了。他对自己说:不能急。急也不是办法。于是他开始抽烟。
他连着抽了三根烟,仍未奏效。这个时候,他几乎无意识地头一转,目光恰好撞到微波炉上。紧接着,一丛神经跳了一下。
他想起了中午有一根神经跳了一下。那时他正好看了微波炉一眼。肯定是那一刻,微波炉像一团淤积的垃圾,堵住了思维的管道。现在,一根神经变成了一丛神经,就是说,这团垃圾变得更大了。
男人没有再写下去。他先是在屋内走来走去,后来,不知不觉出了门到了小区里,接着又走上了大街。大街上的店铺生意都非常好,似乎丝毫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车辆越来越多,即便在白天,一些路段也在堵车,轮子滚动声和喇叭声组成了繁华的交响曲。
他漫无目的地走着。走到集集小镇连锁店时,肚子竟“咕噜”叫了一声。这才想起中午他其实只吃了半碗饭。他进去要了一份甜豆浆。
一个老人坐在了他的对面,喘着气。他喝完了豆浆,拿餐巾纸擦嘴时,老人看着他,好像在自言自语:“车真多啊!吓死人了!”
男人点点头,算是回答。
老人的神色生动起来,继续说:“这么多车,他们哪来的钱买车啊?经济危机了,我们没钱,经济危机之前,其实也挣不到钱。总是没钱。”
是这样啊。男人想。他没马上走,因为感觉到老人还想说话。这也好,反正他什么事也没有。老人沉默了一阵,又开口了:“你文诌诌的,是文化人吧?会写文章吧?是的话,你要写写我们啊!”
这回,男人迅速站了起来,往外走,并对老人说了一句话:
“不,我是一个工人。下岗了。”
[星期天 电饭煲] 星期天,是应该休息的日子。女人本该在这一天休息,可是,虽然很多工厂在减产和停产,女人所在的电子厂生意却意外地好,她不得不在星期天加班。
男人早早地起床了。他打算重新找回写文章的感觉。他先通读了昨天写的两千多字。令他奇怪的是,经过一个毫无波澜的夜晚后,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这些文字毫无征兆地变得陌生了,原先的生气勃勃一扫而光,代之以一片死气沉沉,像沙滩上干掉的小鱼尸体。
那些文字死掉了。
那些文字是他整整一个星期里,与所有坏掉了的家什、与自己搏斗的结果,是仅存的硕果。现在,它们像另一堆坏掉的家什,横在他面前,不出一声,蛮横倔犟。
男人又读了一遍,确定它们已经死去。他关上文档,右击鼠标,删除文件;又打开回收站,再次右击,彻底清除文档。
在确定文字已死、彻底清除文件的过程中,那些坏掉的家什,那个说着格言般的话的水电工,那个集集小镇店里的老人,尤其是脸色发黄上班、一身疲倦下班的女人,一齐涌上他的心头。他感到,另一些文字,正在从细胞开始,不断呼吸,逐渐长大,并像一阵清风一样向他吹来。他闭了闭眼,在朦胧的黯淡光线中甚至看到了这些文字正轻快地跳着舞。
他陷入了另一个文档,像钢琴家演奏那样,敲得键盘“嗒嗒”作响。中午时,他没有停下来,只是找了一包饼干,边吃边打字。到傍晚六点多的时候,他写下第一篇文章的最后一个句号。并且,他又写下另一个标题,写完标题后写下第二篇文章的第一句话。那是他在写第一篇文章时自动跳出来的另一个想法。他决定让这个新想法在大脑里呆一个晚上,因为它不会逃走。
女人要七点左右才下班回家。他淘了米,意外地发现电饭煲在不知不觉中坏了。不过,现在他觉得,一个电饭煲坏掉,不是大事。
他有了主意。
女人回家后,他的第一句话是:“到外面去吃吧。”
女人没反应过来。
他补充说:“电饭煲坏了。能修就修,不能修就买新的。”
他又说:“今天是星期天。很长时间没到外面吃了。去吃热气腾腾的骨头煲!”
他搂着女人的肩膀,先是感到女人的身体有些僵硬,接着感到女人一阵微微的抖动,身子变柔软了。于是,两个人走进了华灯初上的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