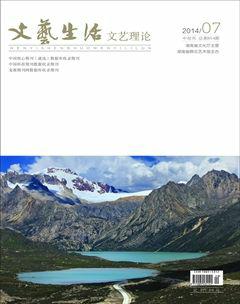齐匪与秦匪的撞击
——莫言与贾平凹土匪写作之比较
徐聪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齐匪与秦匪的撞击
——莫言与贾平凹土匪写作之比较
徐聪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80、90年代,中国文学处在一个巨大变革期,新时期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风貌,土匪叙事成为一个热潮,在意识形态对文学束缚降低,新历史主义兴起以及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的契机之下,土匪叙事呈现出了一番别样可观的形态。莫言和贾平凹都是这个时期土匪叙事上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们的土匪叙事各具特色但又有相通之处,本文将以地理文化内涵为核心点,从地理位置、故乡情愫和故乡文化等方面来探讨莫言和贾平凹笔下齐匪和秦匪的不同之处,进而探析这相异背后更深层的文化内涵。
莫言;贾平凹;土匪
20世纪80、90年代的文学朝着多元化方向不断前进,在多元化的文化形态下,作家们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边缘化人关注的创作视角营造出了千姿百态的土匪形象。在众多的土匪写作中,莫言的《红高粱》一直被认为是土匪写作的扛鼎之作及华丽的开端,其中充满文化活力和生命力度的“土匪形象”也为即将到来的90年代土匪写作热潮做了最精彩的开头。而贾平凹作为一位跟莫言经历相似的作家,在90年代土匪写作热潮中,也塑造了一批别样的土匪形象。贾平凹笔下的土匪形象经过作家的处理已经摆脱了传统土匪的残暴和凶恶的形象,而幻化为书生式的土匪。
莫言笔下的土匪余占鳌,“宽肩细腰”“青白色的结实头皮”,完全一个硬汉的形象。贾平凹笔下土匪,在《烟》中,土匪新大王“眉细眼长,鼻准圆润,腮帮有红施白地细嫩”。①《白朗》中的白朗“想起了这以为美若妇人的白朗大王,他的俊秀的眉目和清朗的笑声并不是可以让你联想一种色相的愉悦。”②他说着话的时候声音柔脆,美目飞动,和颜悦色。莫言笔下的土匪是硬汉般的热血之士,贾平凹笔下土匪却是一个有着书生气息的侠义之士。本文主要以地域文化为核心,来探讨两位作家对土匪不同的勾画。
一、地理环境的影响
莫言生长于东北高粱之地,这片北方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地势开阔宜于战事,历来是兵家相争之地,从上古、中古到近代,多少战争在此打起。因此,民风剽悍,盗匪丛生,历来多慷慨悲歌之士。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山东大汉血性的在这片中国正统文化规范儒教的发祥地,让他们更习惯于比较豪放粗疏的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高密这片神奇的热土让生长于此的莫言形成了豪放的感情表达方式,所以在他笔下的土匪,始终是带着原始的野性和豪放的气魄的硬汉!
贾平凹长期生长在一种丘陵地形之内。这种丘陵地形带着浓郁的南北交融的气息。特有的山水,特有的气候,养育成商州人特有的情感观念和生活文化方式。贾平凹以敏感的心灵领受这份地理,领受这份文化,商州这种民风淳朴的野情趣使得贾平凹笔下的土匪呈现出一种浪漫的书生气息。他们也有残暴的时刻,但是更多的形象是翩翩风度、侠骨柔肠的美男子形象。
莫言和贾平凹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环境影响着两位作家对土匪描述,更进一步的地理文化内涵当然还包括这两位作家对故乡的态度,这种精神面貌也影响着两位作家笔下土匪形象的描述。
二、故乡的情愫
莫言和贾平凹可以说都是根植于自己家乡那片土地上进行创作,在自己故乡土地上汲取着养分来塑造自己的文学殿堂,但是,两位作家对故乡的态度却是有着明显差别的。
莫言对故乡是逃离再回归,回归的时候仍然是带着“仇恨”。他说他恨透了这个地方,也爱透了这地方。“假如有一天我能离开这块土地,我绝不会再回来。当汽车停在一个离高密只有三百里的军营,带兵的人说了目的地时,我感到十分失望。”③由于在故乡所经受的苦难,莫言对故乡在早期抱着一种深深的恨意。但是,当他离开这片土地之后,他却恍然。尽管他恨这个地方,但是他没有办法割断与这个地方的联系他的根在那里,潜意识里对它的眷恋也是挥之不去的。所以当他再次踏上故乡这片热土的时候,他心中却是那样激动,“当我看到满身尘土、眼睛红肿的母亲……我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故乡对一个人的制约。对于生你养你、埋葬着你祖先灵骨的那块土地,你可以爱它,可以恨它,但你无法摆脱它。”④莫言对故乡这种既爱又恨的感情让他用一种宣泄甚至狂放的姿态来写高粱地里的人和事,赤裸裸地描述我爷爷这位土匪的衷仆罗汉大爷被剥皮的惨烈现场,毫不顾忌地描写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的自然欲望的宣泄,残忍地安排我二奶奶和她女儿被日本兵残忍的猥亵和杀害,这些围绕着土匪所写的人和事都是一种狷狂和野性的姿态。
贾平凹对故乡则是一如既往地热爱和眷恋。“我最愿意回到生我养我的陕南家乡去,那里是我的根据地,虽然常常东征西征,北伐南伐,但我终于没有成为一个流寇主义者。”⑤在漫长的二十年里,慰藉以这颗灵魂安宁的,是门前屋后那重重叠叠的山石,和山石之上的圆圆的明月。贾平凹在充分挖掘了故乡生活体验之后,曾长期客串商州各县各乡,他走遍了商州七县和丹凤家乡的许多山村,贾平凹对故乡的热爱使他不但不远离家乡反而更进一步地去发掘家乡的魅力和神秘。所以贾平凹对故乡的态度使他探索乡民的心灵美,总是以美和善的角度来勾画人物,而不是像莫言那样用狂野来处理各种矛盾,他对故乡的情感让他笔下的土匪这样矛盾集中和传说中凶残的人物都变得诗情画意、风流倜傥了。
由上可见,莫言和贾平凹对土匪形象的叙述和定位深受两位作家对他们对生养他们故乡所持态度的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故乡不同的感情和定位使得他们对农村特有的土匪形象叙事产生了这样的区别。
三、故乡承载的文化内涵
莫言所处的高密东北乡的山东,是孔子之乡,儒家文化的兴盛之地,莫言生活在此,势必会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一种入世哲学,所以在《红高粱》中,作为土匪的余占鳌在面对家园临难,带领着自己的队伍去抗击外敌,也许他并没有怀抱着拯救家园,把自己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的显性的言行,但是在其潜意识里面,这样的情愫已经融进其血液里面了,他们抗击貌似看来就是为了自我的生存,但是,这样的生存显然是深受儒家思想所影响的。但是儒家思想所形成的对人们的束缚又是莫言很蔑视的。在高粱地土匪的描写中,莫言使生命力在发光发热,在这种热狂之中,莫言使自己的精神得到解脱,被人誉为“酒神精神”,莫言这样的豪放是因为他从根底上蔑视因为儒家文化的糟粕之处让乡民们成为了软弱的人,所以在高粱地里土匪是那么的血性,那么的粗狂那么的火爆。他讨厌这片土地上儒家文化给大家带来的软弱和苦难。而且,莫言在面对西方文化袭来之际,从西方文化中吸收了大量养分,莫言企图以西方文化和原始文化来改造现代中国,他的语言、精神多有西方风范及欧化效果。这也造就了莫言在土匪叙述中把土匪描述成一个铁血硬汉的形象。
不同的文化对历史有不同的感受方式,一种特定的地域文化,地理人文给人们带来特定的想象方式。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乡土社会,地理文化对一个作家的影响是十分深厚的,农村经济让土匪在他们笔下有了存在的基础,共同的农村经历让土匪自然而然成为他们叙述的对象,但是不同的地缘文化和人文气息,让莫言和贾平凹笔下的土匪形象却又如此相异。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⑥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文学承接着社会的习性,也透露出乡土性的特征。中国文学多根植于农村乡土这片土地上,所以,不同的土地文化当然会孕育出不同的文学文化,文学也在地缘文化的各异下发展出千变万化的特点来。莫言和贾平凹两位作家生出在北方不同的地理文化下,共同的农村经济基础让他们有了共同的书写对象,不同的地理文化内涵让他们对土匪的描写呈现出别样的风格。他们对西方文化接受、美学观念、宗教理念都影响着他们的土匪叙事,但是在所有因素中,最基本的就是他们生与斯长与斯的土地文化,这个影响着他们的成长和人生观的形成,在这个基础上,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文化接受模式、美学观念以及宗教理念。
综上,莫言和贾平凹对土匪形象的描写,在根本上是受到了地缘文化的影响,在各具特色的地理文化影响下,他们对土匪的叙述也呈现出了各自独有的特色。
注释:
①②贾平凹.五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179页.
③④孔范今,施战军.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⑤雷达.贾平凹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⑥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页.
I206
A
1005-5312(2014)17-0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