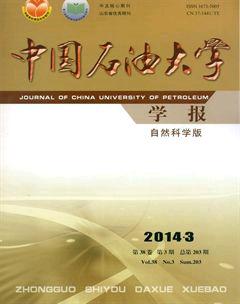论《正义论》中基本善的作用及其存在的必然性
张祖辽
[摘要] 罗尔斯在其义务论的道德哲学中区分了两种善理论,即善的强理论(the thick theory of good)和善的弱理论(the thin theory of good)。前者以良序社会中的正当原则为基础,并在正当优先于善的义务论框架中被广泛讨论。后者则以基本善为核心范畴,以此构建其道德哲学的实践推理基础。不过,他对基本善的设定由于游离于其义务论框架之外而未能得到足够关注。然而,《正义论》对基本善的设定却是理论的必然。该理论在《正义论》中有两个应用层次:首先,它是罗尔斯的道德契约论的推理起点;其次,没有基本善的存在,罗尔斯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将难以在道德层面获得足够的稳定性。
[关键词] 善的弱理论;基本善;正当原则;稳定性
[中图分类号]B7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3-0054-05
《正义论》一书所阐发的道德理论上承康德的道德哲学,罗尔斯在此书中推论出的两个正义原则不但具有类似于绝对命令的纯粹性,亦赋予在康德那里只能以纯粹理念的形式而存在的道德命令以现实的可操作性。因此,罗尔斯也往往被冠以经验主义义务论者的名号。正当与善的关系问题是罗尔斯道德哲学的重要方面,不过,善理论在罗尔斯那里却被明确分为两段,即善的强理论和善的弱理论。而由于善的弱理论所设定的五种基本善,使得罗尔斯的义务论立场相对康德来说少了许多纯粹性。然而,如果对罗尔斯的道德哲学体系进行深入辨析,就会发现基本善的设定乃是无法避免的理论结果,因为基本善不但是他的道德契约论的推理前提,也是正当原则得以获取稳定性的理论基石。本文即试图逐步梳理和辨析基本善在《正义论》中的上述两种应用层次,以此勾勒出其在罗尔斯的整个正义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作为公平的正义:一种独特的义务论
正当与善的关系问题是贯穿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一条主线,围绕正当与善何者优先,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大致形成了目的论和义务论①这两条各自独立但又相互影响的探究理路。在前者看来,善优先于正当,也就是说,人们所欲求的各种利益和目的应当被预置为有待实现的前提,而“正当”的标准则取决于人们在实现这些利益和目的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和手段能否将其最大程度地实现。后者则认为任何一种利益或目的的实现都不能被先行赋予任何独立价值,其合理性标准仅仅在于对这些利益、目的的追求过程和实现方式是否严格遵照了正当原则的要求。
近代以来,功利主义是目的论的典型代表。如,西季维克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被安排的能够达到所有属于它的个人而形成的满足的最大净余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被正确组织的,因而也是正义的。”[1]这种理论模式将善作为制度设计的最终指向,而衡量正当(正义)的标准即是取决于这种所谓的“最大净余额”能否得到实现。义务论则在康德那里体现得最为明确和充分。康德认为,道德哲学不能单纯讨论善的实现,因为道德价值在实质上更加取决于人们是否无条件地按照善良意志所颁布的绝对命令行事。
罗尔斯的道德哲学通过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复归到康德式的义务论立场。首先,罗尔斯分别就公民政治权利的平等和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两方面提出两条正当原则,并赋予其相对于善的优先性。与康德不同的是,在罗尔斯那里,正当(正义)原则摒弃了先验的理论架构,转而依据经验论的理论立场,在契约式的思想实验中加以构建。而在正当原则的构建过程中,罗尔斯对正当与善之关系问题的表述却呈现出不同于传统义务论的复杂性。具体表现在:就整体表述和理论目的而言,罗尔斯的道德哲学以正当优先于善的义务论立场作为其根本归宿,但为正当原则的推论而设定的作为人们动机的基本善却在一定程度上使他的正义理论倒向了目的论。而以基本善为基点,整个善理论被截然分为两条进路:其一,基本善的设定解决了原初状态中立约各方的基本动机,结合契约论的论证理路,原初状态下的人们在订约过程中参照基本善选择出两条正当原则,从而使正当(正义)原则的理论推导得到合理的说明,这条进路就是善的弱理论;其二,依据合理性(rationality)理念推论出来的基本善只能作为其整个善理论的前导,因为它没有涉及人类生存的更高层次的要求以及诸如美德、正义感等道德性的善。相反,这些善则必须由正当(正义)原则反过来加以说明,而这些内容则是善的强理论的作用范畴。简单地说,除了作为动机的基本善之外,其他善理论的意义都是由两个正当原则赋予的。因此,我们可以把罗尔斯看作义务论者,但其义务论立场却并非如人们所理解和期望的那样一以贯之,而是在其特殊的方法论要求之下向目的论有着某种程度的回归。
二、基本善:道德契约论的基本动机
基本善的设定离不开《正义论》的方法论框架,我们可以在罗尔斯的论证方法——假然契约理论中发现设定基本善的必然性。
首先,罗尔斯所设想的社会契约不同于古典社会契约理论。他认为:“我的目的是要提出一种正义观,这种正义观进一步概括人们所熟悉的社会契约论,使之上升到一个更抽象的水平。”[2]11为明确“更抽象的社会契约论”这一说法,我们不妨先行反观古典契约论的基本理论形态。
从古典契约论的理论形态来看,一个完整的契约理论包括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和制度结构三部分,这三部分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一种政治哲学的理论体系。自然状态乃是理论家所假想的前政治社会中人们的实然生存状态;而这一前政治状态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迫使生存于其中的人们不得不另立契约、组建政府②;所谓的制度结构,便是针对人们在契约中的相互约定而设计出的一整套制度化的实施方案。以上就是古典契约论的一般论证程序。然而,罗尔斯却以“无知之幕”这一构想取代了近代契约论的论证传统。罗尔斯认为,社会契约的目的是要为那些介入社会合作的人们提供能够被他们一致同意的公平合作项目。因此,“绝对公平”成了罗尔斯的契约论的理想形式和订约起点。其前提则是参与订约的人们具有绝对平等的选择地位、能力。这样一来,设计绝对公平的立约环境就是罗尔斯契约论的首要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更抽象的契约论”的确具备康德式的合理性和契约理论的首创性,因为它不再以想象中的前政治社会中不平等的实然状况为基础,而是首先将平等作为政治社会的根本价值,并以人为方式建构一种绝对公平的理想选择状态。
其次,古典契约论者试图从假想的自然状况之弊端出发,从应然的角度推论出自然状态中的人订立契约并转变为社会公民的必要性。而罗尔斯的思想实验却并非意在揭示假想中的前政治社会的某些经验事实,而是首先设定人类自身应当珍视和保障的某些特定道德价值,立约的目的就是通过契约这一程序将这些道德价值明确地确定并选择出来。因此,罗尔斯的契约理论之实质并非利益的衡平和妥协,而是一种实质上的道德契约论。
然而,古典社会契约论并没有单独提出基本善,那么为什么在罗尔斯的道德契约论中,基本善的设定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依然可以在他的契约论中找到答案。绝对公平的订约环境(原初状态)是罗尔斯的道德契约的订约前提。而在无知之幕下,订约主体的另外两个特点——“理性(rationality)和相互冷淡”则意味着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每个个体的内在心理倾向,只是在无知之幕的遮盖下,人们并不知道适合于自己的特定的善以及自己在追求善的过程中诸如地位、偏好、能力等各方面的优势,也就是罗尔斯所描述的:“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无论是阶级地位还是社会出身,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先天的资质、能力、智力、体力等各方面的运气。我甚至假定各方并不知道特定的善的观念或他们特殊的心理倾向。”[2]12因此,出于理性的权衡,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无知之幕的制约下进行一种选择的冒险。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理性的考虑,“我”不能简单地代表“我”这个个体,而是必须将“我”置于与他人同等的位置上进行同等程度的权衡,就此,罗尔斯提出“最大的最小值原则”。既然所有选择主体的基本意愿都是希望在无知之幕揭开后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利益和偏爱,那么作为理性的个体,他们只能基于自身最基本的利益诉求,依据一种“审慎的合理性”选择一种对所有理性主体而言最具普遍性的正当原则。
然而,作为一种选择理论,任何一种契约理论都必须首先明确选择主体在原初状态中的基本动机,否则,人们将找不到订立契约的理由。那么,原初状态中的选择主体具有何种基本动机?问题的关键还在无知之幕。既然无知之幕将所有个体都通约为自由而平等的理性选择主体,而在无知之幕揭开之后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利益和偏爱是每一个理性主体的基本意愿,那么作为理性个体,首先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具有谋求基本生活以及进一步发展的基本保障,以便在无知之幕揭开,自己的能力、偏好等特征为自己所知之后,如果自己正是罗尔斯所谓的“最不利者”,至少有保障自己最低基本道德人格的能力。因此,罗尔斯将对基本善的追求设定为原初状态的基本动机,因为正是对基本善的占有能够确保人们在正当原则的约束之下能够有谋求更大发展的可能性。
罗尔斯认为,正是对基本善的占有能够作为对“自己最低的基本道德人格”的基本保障。他在《正义论》中给基本善以清晰的界定。该界定认为,所谓基本善,就是“权利和自由、机会和权力,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2]93。正是由于对基本善的设定,人们才得以明确其订约动机,并在契约论的前提下达到对两个正义原则的一致认可。
此外,随着《正义论》的不同版本对动机的修订,罗尔斯也随之对基本善进行了不同的解释。罗尔斯在《正义论》的初版主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阐述基本善的不可或缺。在修订版中则转而诉诸具有两种道德能力的道德人理念,并把发展两种道德能力作为道德人的最高关怀。也就是说,立约人在原初状态中虽重视自己的各种特定的善,但更重视成为道德人的能力和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恰恰是基本善能够确保的。
重要的是,以基本善为切入点,我们可以看到罗尔斯的道德哲学内部存在的张力,基本善的设置先行于两个正义原则,对基本善的无条件欲求也是契约得以成立、正当原则得以被承认的先行条件。然而,对独立于正当原则的基本善的先行设定是与义务论背道而驰的,因为这样一来基本善便不在正当原则的规导之下。因此,基本善的设定在某种程度上向罗尔斯一直批评的目的论有所回归。不过,根据上文的分析,基本善的设定又是不可避免的,否则罗尔斯的论证框架就无法成立,对两个正义原则的推导更是空中楼阁。罗尔斯显然很清楚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他特地置“弱”字于基本善这种善理论之上,并对其作用范围做出了明确界定。即,“我们需要假定各方在原初状态中的动机。由于不允许这些假定危及正当概念的优先地位,善理论在正义原则论证方面就几乎不起作用”[2]396。也就是说,“弱”字在这里体现为动机上的某种普遍性,以此作为契约选择的普遍起点。由于这一理论的提出,罗尔斯也遭到诸多批评。对其批评的要旨基本为:即便在现代的立宪民主社会中,上述基本善的条目也无法作为普遍的选择动机。基本善的设定不但意味着他对目的论有所回归,而且也使其进一步背离了经验论立场,转而寻求形而上学的声援。
对上述批评及回应的梳理和分析并非本文的题中之义。笔者在此只想说明,基本善在《正义论》中的第一层作用是为订约主体设定无条件的选择动机,从而成为整个正义论的理论铺垫。不过,在对正当原则和善理论推理框架中,基本善的作用就此止步了。罗尔斯在动机确立之后转而诉诸正义原则规导下的善的强理论来诉求和完善其义务论立场。
三、基本善:稳定性理论前提
作为一种选择理论,稳定性论证是契约论的必要步骤。因为“一个缺乏稳定性(stability)的正义原则,必然没有正当性(legitimacy)。换言之,稳定性是正当性的必要条件”[3]。在笔者看来,《正义论》中的稳定性论证包含两个层次。首先,罗尔斯必须说明原初状态中订约各方选择两个正当原则的必然性,这一层次的论证是在与功利主义理论的比较中,由契约推理的方式做出的。如上所述,基本善的设定为契约推理提供了基本选择动机。因此,本文将这一层次的稳定性称为选择的稳定性。不过,这一层论证并不足以说明对正当原则的遵循和坚守是良序社会中每个公民的自律性倾向。因为人们即便在良序社会中也仍然可能成为以正当原则为手段来使自己获利的利己主义者。也就是说,利己主义者也完全可以公正地行事,但公正的行为结果却不见得纯粹出于公正的理由。这样一来,正当原则完全可能沦为利己主义者的精致的获利手段,从而破坏人们坚守正当原则的信念。因此,罗尔斯转向稳定性的第二层次,即诉诸良序社会中理性人的自律。这意味着生活于良序社会中的人们普遍将出于正当原则而行事当作一种善,即自己的理性欲望,而这样的行为来自于对正义感的自觉认同和坚守。因此,这一层次的稳定性可称之为自律的稳定性。在这一层次中,行为主体是与利己主义者不同的行为公正的人,对他们来说,依照正义原则的自律是其行为原则,而这种自律又是无条件的。因此,罗尔斯必须说明,这种无条件的自律何以可能?以及人们为什么能够把对正义感的肯定当成一种无条件的善?根据上文的分析,在《正义论》的语境中,这个问题同样需要在善的弱理论的层面上加以证明。这就是基本善在《正义论》中第二层次的作用。
在稳定性的自律论证中,罗尔斯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出说明:
第一,罗尔斯从心理学的角度展开论证。良序社会中,正当原则的公开、公正等特征能够对利己主义者形成心理上的负罪感,而这种负罪感是与人们的道德情操紧密相联的。如果说在一个非正义社会中,制度的非正义和其他人的龌龊行为尚能使利己主义者减轻罪恶感,那么良序社会则消除了这种侥幸的可能性。因此,罗尔斯认为,在正义社会中,两个正当原则既然能够保证人们自由的尊严和平等的地位,那么对利己主义者来说,将正当原则当作手段的所得远远不能补偿其心理上的所失。
值得注意的是,罗尔斯在权威的道德、社团的道德和原则的道德这三个阶段的逐层过渡中用心理学原则解释了普遍的正义感的形成。这三个阶段中,公正的制度背景是共同的制度前提。在道德发展的前两个阶段,人们发展出的是一种对制度和他人的具体依恋关系,而最后一个阶段则排除了个人对于他人及团体的具体联系,从而摆脱了这些道德上的偶然性并被选择出的正当原则塑成。因此,这三条法则体现的是良序社会中孕育的以德报德的内在心理倾向。而正义感发展的三阶段论则是负罪感得以产生的理论前提。因此,在这样一个正义的制度约束中,正义感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私有社会中的个人都有其私人目的,这些目的不论是相互冲突的,还是彼此独立的,都没有道德价值,制度本身也仅仅被看作可资利用的手段。而罗尔斯构想的良序社会则是超越了私人社会的社会联合。罗尔斯在这一点上返归到古典政治哲学的立场,认为亚里士多德原则体现着人的社会联合的本性,人实际上分享着某些最终目的,并应当把制度和公共活动本身视为一种善。在由社会联合而形成的共同体中,由于每个个体自身的局限性,任何单个个体都不可能获得完满的善。而在共同体中,人们为一个最终目的的相互合作能够产生出更大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使得在合作中每个人的潜力和幸福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现实化。为了享受这种生活,就必须把共同体中的正当原则作为生活的调节性观念,这就意味着人们必须首先肯定他们的正义感。
第三,罗尔斯诉诸对正义论的康德式解释,认为公正的行为是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者所乐于去做的行为,因为对两个正当原则的肯定保证了自由和平等这两种价值的实现。在康德那里,道德的行为体现为遵从道德律的绝对命令,而这种行为在每个人身上的体现就是理性的自律。罗尔斯将康德意义上的自律和绝对命令进一步做出经验化和程序化的解释,试图以原初状态的立场说明公正的行为是我们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者乐于去做的行为。其根据有两点:首先,原初状态中的各种特定知识是被遮蔽的,人们无法依照诸如自己的社会地位、自然禀赋等知识来选择他律原则,相反,他们所选择的行动原则完全不依赖社会和自然的偶然因素,订约各方仅仅作为知道有关正义环境的自由和平等的理性个体而达到他们的选择,而当选择的结果能够确切地表现出他自己的本质时,他就是自律地行动的。其次,对两个正当原则的论证除了依赖基本善这一理性的本质性需求以外,并没有对人们的其他善观念作出过强的预设。因此,在罗尔斯看来,以弱的基本善为动机而选择的正当原则本身就是康德意义上的绝对命令。
上述三点就是罗尔斯为两个正义原则的自律的稳定性所做的论证。上述三点论证中,最后一点是最根本的,因为对两个正义原则的遵循体现的是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存在者的本质。这种对人的价值预设也是罗尔斯整个正义理论的最终落脚点。我们说过,罗尔斯的论证方法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契约论,这种契约论着意在对最值得人们珍视的道德价值进行选择和辩护,而这些道德价值在罗尔斯看来就是宪政民主社会中的自由和平等等理念。在本文讨论的稳定性的自律性论证中,我们得知,肯定这样一种正义感,也就是肯定人作为自由而平等的存在者的本性。而这种正义感恰恰能够在基本善的层面上作为人们的基本动机加以说明。
四、意义
基本善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重要预设。通过将基本善作为推理起点,罗尔斯义务论的理论大厦得以建构起来。然而,基本善的先行预设意味着善对于正当的优先性,这样一来,罗尔斯的义务论立场就不可避免地遭到诸多质疑和批评。不过,上文已经分析到,罗尔斯并不是没有看到这里的矛盾之处,相反,罗尔斯对这一预设有着极为敏感的理论自觉。否则,他就不会在《正义论》的整个第三部分中反复强调基本善乃是属于善的弱理论的范畴,以及善的弱理论(the thin theory of good)和善的强理论(the thick theory of good)之明确区分。
然而,罗尔斯预设基本善的意义还远远不止于此。我们知道,义务论(道义论)和目的论(效果论)被普遍认为是近代以来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两条进路。这种划分当然能够在诸如理论特征、思想进程及论证思路等方面对近代以来的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做出某种程度的概括,从而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另一方面,对理论的这种二元对立式的划分却难免使人们在看待一种理论形态时陷入一定程度的僵化和简单化。比如,我们一般用“义务论”的标签来标示康德的道德哲学,但严格来说,康德的义务论立场同样不是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纯粹,因为康德那里也有契约主义的方法论特征,只不过在他的语境中对善的预设相对罗尔斯而言弱了许多。以霍布斯主义为传统的契约理论则有着比罗尔斯更强的目的(善)预设,尽管这些契约论者也多数被冠以义务论者的标签。因此,以罗尔斯的基本善为出发点,我们对近代以来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研究在对上述二分式思路的继承之下不妨试着超越这一视野,以另一种思路来看待康德以来的“义务论”传统和由功利主义发展而来的“目的论”传统,淡化这两种不同理路间的区分,更多地发掘和强调这两种理路间的贯通和融合,以使理论研究更加贴近“人”本身。
注释:
① 义务论(deontology)又被称为道义论,而“目的论”(teleology)则不能与古典哲学,如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目的论混淆。本文所讲的“目的论”乃为近代以来的功利主义思想所具体阐发,因此又被称为“效果论”。
② 当然,这种说法难免有片面之处。比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虽明确认为自然状态是为了理论目的做出的假想,但该著作中列举人类社会之实例以作为自然状态之佐证的说法也并不鲜见,卢梭那里大致也是如此。不过,就近代社会契约论的发展脉络和理论实质来说,将自然状态作为人类历史之实然这种看法虽能见于几位思想家的著作,但论证地位却始终很弱,康德以后,这种论证方式则基本淡出了契约论者的视野。
[参考文献]
[1] 西季维克.伦理学方法[M].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27.
[2]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M].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3] 周保松.自由人的平等政治[M].北京:三联书店,2010:144.
[责任编辑:夏畅兰]
Abstract: Rawls distinguished two kinds theories of good, which are the thick theory of good and the thin theory of good. The foundation of the thick theory of good is the principle of right, which was discussed widely in the frame of deontology meaning that right is prior to good. On the other side, the core category of the thin theory of good is the primary good and Rawls established his starting point of practical reasoning. And the theory of good hasnt gained enough discussion because it is out of the framework of deontology. But the theory of primary good is unavoidable in the theory of justice. In the book, that theory has two existent levels. Firstly, it i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Rawls practical reasoning; secondly, if the thin theory of good does not exist, it is hard for the two principles of right to gain its sufficient stability in the level of morality.
Key words: the thin theory of good; the primary goods; the principle of right; st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