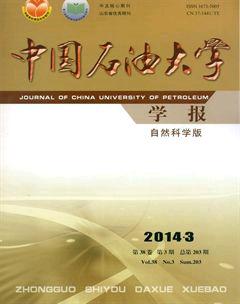论刑法中的推定承诺
涂欣筠
[摘要] 推定承诺作为刑法中的正当化事由,已为各国刑法理论和实践所普遍接受。但因其与被害人承诺、紧急避险的相似性,使得学者们对其性质、正当化依据、成立条件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推定承诺是基于被害人承诺延伸的独立正当化事由。推定承诺的正当化依据是对被害人的法益保护,其成立需满足严格的条件,包括与被害人承诺相同的成立条件和特殊的成立条件:被害人对法益有权承诺、被害人具有承诺能力、被害人承诺的客观不能、被害人承诺的当然可能性,行为人具有推定承诺的认识、行为人出于正当目的。
[关键词] 推定;被害人承诺;推定承诺;正当化依据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3-0039-05
一、推定承诺的概念及正当化依据
推定承诺是指行为人在行为的时候,认为权利人已经同意或者认为如果权利人在场就应该同意的情况。
[1]由此可见,推定承诺是行为人在行为时对权利人主观心态的一种推定。其前提是客观上无法获得权利人的权利处分意志,且行为人的行为侵犯了权利人的权利。将推定承诺作为刑法上的正当化依据,最先是由德国刑法学者梅兹格提出的。推定的同意是一种习惯法上的正当化依据。但是,推定的同意并不是随便发展起来的,而是以对这种同意思想的一种最终思考为基础的,从其本身来说,这种思考应当是从宪法性保障的行为自由(《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中推导出来的。[2] 534
世界各国及地区的刑法理论虽普遍认可推定承诺是刑法上的正当化依据,但除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刑法典》外,少有刑法对此有明文规定。因而在这些国家及地区,基于推定承诺的行为是以超法规的正当化行为形式存在的。
[3] 397 同时,各国及地区对推定承诺作为超法规的正当化依据的理由不尽相同。
大陆法系一般将推定承诺作为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但对为何能阻却违法的解释却不相同。德国刑法学者克劳斯·罗克辛将推定承诺作为“出于允许性风险的正当化根据”:在信条学上,这种推定的同意存在于同意和正当化的紧急状态之间,但保持了自己与两者都不同的独立性。[2] 532与此类似的有韩国刑法理论:除在韩国刑法上被实定化的各个违法阻却事由以外,能够在超法规上认定的违法阻却事由只能全部作为第20条“社会常规”中的正当行为被正当化。如果是这样,立足于被容许的危险原理的推定的承诺这一违法性阻却事由,也将此视为不违背社会常规的正当行为的一种是妥当的。[4] 313 意大利刑法学者杜里奥·帕多瓦尼则用“无因管理”权利行使的理论来解释推定承诺的正当化依据:为权利人的利益而推定的同意,可以纳入negotiorum gestio(拉丁语,即民法中的“无因管理”)的范畴(民法典第2028条),并因此而成为排除犯罪的原因。但是,这种情况不构成犯罪的法律依据,不是刑法典第50条,而是刑法典第51条第1款规定的依法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因为无因管理行为开始于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因而是一种权利,但管理行为一经开始,行为人就负有适当管理的法律义务)。[5] 中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学者蔡墩铭亦认为推定承诺“实与民法上之无因管理行为相同”:民法上之无因管理既可阻却民事违法,则在刑法上其亦应可阻却刑事违法。[6]
英美法系将被害人承诺作为免责理由,但如果缺乏被害人的承诺不是犯罪的法定要素时,承诺一般不能用作抗辩理由。在美国,同意被认为是某些种类的袭击罪的抗辩理由。实际上,袭击罪形式上常被界定为一种未经同意的接触,缺少同意是该罪的一个犯罪要素。[7] 类似地,缺乏同意亦为强奸罪的法定要素。不幸的是,“同意”(或“不同意”)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同意”可以理解为一种态度上或内心的思想状态。[8] 但只要证实或推定了此种作为被害人承诺的同意,就成为强奸罪的“缺乏要素抗辩理由”。在英国,被害人承诺可作为人身伤害的免责理由,但法律依伤害程度规定了承诺的界限范围。同时,若承诺是在事后“被威胁或为了减少损失”的情况下做出的,则行为时对承诺的推定是不成立的,因为这时刑法的威慑力将被大大削弱。缺乏同意同样是英国财产犯罪的法定要素。针对财产犯罪的1971年《刑事损害》法令第1条虽未将“缺乏被害人同意”表述为犯罪的必备要素,但第5条第2款a项规定:“针对财产损害的行为人有一个免责理由,如果在有关时间内其确信有权同意财产损害或破坏的人有此种同意。” 因此,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推定的承诺作为对被害人同意的一种推定,其并不是可适用于所有犯罪的一般抗辩理由,而是一种针对特殊犯罪的“缺乏要素抗辩理由”。而缺乏同意是否作为犯罪的法定要素,取决于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内容。
依上述观点,推定承诺作为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其正当化依据大致可归纳为三类:一是认为推定承诺是一种“被允许的风险”;二是认为推定承诺是民法中无因管理的一种权利行使行为;三是认为推定承诺是对犯罪法定要素缺失的一种推定。这三类依据虽各有其道理,但前两类均仅从“推定”为何合法的角度出发,而未从推定承诺与被害人承诺之间的关系出发进行分析,第三类则未解释推定承诺的效力为何等同于犯罪法定要素的实际缺失。同意推定承诺是对被害人现实承诺的一种推定,因此,推定承诺与被害人承诺在刑法上的正当化依据首先应是相同的,其次才是解释“推定”的正当性问题。
古罗马法即有“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的法律格言。被害人的承诺阻却违法性的根据何在?这样的问题与对违法性的本质、刑法的任务、机能的理解有密切联系。对于违法性的本质存在法益侵害说和规范违反说的分歧。从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生活利益即法益,而不是维持国家的道德伦理秩序的近代刑法观来看,应当说,以法益的比较衡量为核心的“法益衡量说”以及“个人自由和侵害利益比较衡量说”更加恰当,值得支持。刑法之所以将某种利益作为法益加以保护,主要因为其是个人自己决定或者说自我实现(人格发展和完成)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是实现该种目标的必要条件。所以,被害人自愿放弃其能够处分的利益,在以个人的自我实现作为刑法的终极目的的现代刑法当中,应当允许对侵害该种被放弃的利益的行为,不能作为犯罪而加以处罚。应当说明的是,推定承诺可能存在被害人事后不追认承诺的情形,在被害人真实意志与推定意志相反的情况下,依推定承诺的行为并不能反映被害人对法益的放弃。这就需要解释,为何推定承诺此时仍是刑法上的正当化事由?笔者认为,推定承诺是特殊情形下对被害人意志的一种推定,其适用需满足严格的条件。在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下,之所以允许行为人依推定承诺而行为,是因为当时依推定承诺行为对被害人法益保护更具意义。从此意义上讲,推定承诺,在允许行为人冒着可能违反被害人的真实意思的风险而自行行为的意义上,具有“允许危险”的特征。但这本质上仍出于对被害人法益保护的目的。综上,推定承诺的正当化依据是实现对被害人的法益保护。
二、推定承诺的成立条件
推定承诺作为一种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阻却了对被害人侵害行为的违法性,因此对其适用需进行严格限制。推定承诺作为被害人承诺的一种延伸,其成立条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被害人承诺相同的成立条件;二是推定承诺特殊的成立条件。
(一)与被害人承诺相同的成立条件
被害人承诺欲成立需满足承诺主体、承诺对象、承诺时间、承诺表示、承诺目的等多方面条件。但由于推定承诺适用于被害人承诺客观不能的场合,故其不要求具有与现实承诺有关的成立条件。推定承诺与被害人承诺相同的成立条件包括:被害人对法益有权承诺、被害人具有承诺能力。
首先,在刑法上,能够承诺的事项,主要是个人能够处分的个人法益,被害人不能对侵害公共法益的行为进行承诺。一般认为,财产法益个人能够自由处分,人身法益通常情况下也是个人可自由支配的,但生命法益并不是被害人承诺的对象。因为生命法益是个人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个人对法益拥有自我决定权的前提。如果允许生命法益作为承诺的对象,将剥夺个人今后对其他法益进行处分的权利。这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毁灭性后果,因而显然是不合理的。在美国,在一些针对个人伤害的犯罪案件中,缺乏同意并不是犯罪的法定要素。这些犯罪包括:谋杀罪、重伤害罪等,在被害人承诺的情况下仍可能成立。因为人的生命和重大人身安全涉及的不仅是个人法益,更是社会和公共利益。应当说明的是,虽然财产和人身法益均可作为推定承诺的对象,但针对此两类法益侵害的推定承诺,其特殊成立条件却是不同的,对此将在下文具体论述。
其次,推定承诺是对被害人法益处分的一种推定,故同样要求被害人具有对法益处分的承诺能力。此处所谓被害人必须有承诺能力,意指被害人有相当成熟的辨别事理的能力。亦有学者认为,具有承诺能力是指具有准确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笔者认为,这样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因为被害人承诺不能简单等同于民法上的意思表示行为,且推定承诺并不要求被害人具有现实的意思表示。即使被害人欠缺准确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但只要其具有与处分法益相当的辨别事理能力,亦可对其法益处分的意志进行推定。然而,对被害人是否具有相当的辨别事理能力的判断,是复杂的个案判断问题,且在推定承诺的场合涉及判断主体、判断依据等具体问题。
(二)推定承诺特殊的成立条件
除上述与被害人承诺相同的成立条件外,对被害人主观心态的推定要求推定承诺具有特殊的成立条件。这些特殊的成立条件,是对推定的一种限制,亦体现了对被害人法益保护的负责任态度。
1.被害人承诺的客观不能
如前所述,推定承诺仅可适用于被害人承诺客观不能的场合,即因客观原因无法获得被害人的现实承诺。当一个人的法律领域应当受到侵犯时,只要有可能对这个人进行询问,就不存在任何理由可以允许对法益承担者的真实意志作出错误认识的风险。[2]534被害人承诺的客观不能通常发生在情况紧急的场合,如:交通事故中重伤昏迷的被害人需立即手术,但其无法就是否手术为意思表示,在此情形下医生擅自决定对其进行手术,就属于一种推定的承诺。
但推定承诺的成立是否一定要求情况紧急?通说认为,推定承诺要求情况紧急。如果情势并不紧急,行为人完全可以征求被害人的意见却不征求,擅自采取行动,就是对被害人自我决定权的侵犯,自无适用基于推定承诺行为的原理,成为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的可能。[3]410然而,亦有学者认为情况紧急的要求也存在例外。当被害人被侵害的法益并不非常轻微,而且,行为人的行为也不具有紧急性的场合,也可以根据对被害人的了解而推定其同意。如擅自将朋友的自行车骑走;暂时挪用正在外旅行的他人的现金等。当然,这里又有严格的限制性要求,前者是经常存在以该种方式借用该朋友的自行车的情况,否则不能认可推定同意;后者则是二人同住一屋,关系很好,平常就有互借现金的事实,否则也不能认可这种推定的同意。[9] 145 这样的解释虽不无道理,但擅自骑走朋友自行车及暂时挪用他人现金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上的侵害行为尚存疑问,行为人虽侵犯了被害人的财产,但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此种基于熟人关系的推定同意,仅是在认定侵权行为成立与否时应考虑的因素。被害人承诺,应该是刑事被害人的承诺,行为人的行为是对被害人人身、财产造成重大侵害的行为,因此需要紧急情况才可成立。若非紧急情况,不可对被害人人身、财产利益的处分意志擅自推定。
2.被害人承诺的当然可能性
所谓当然可能性,是指如果被害人在场,也会当然地作出承诺的意思表示。推定承诺是对被害人意志的一种推定,如果行为时不具有此种当然可能性,也就缺乏了推定的事实依据。被害人承诺当然可能性的判断应当是行为时的具体判断。但此种判断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依行为时行为人的意志还是依事后被害人的意志,学界存在分歧。有观点认为,推定承诺是行为时行为人对被害人意志的一种推定,故应依行为时行为人的主观判断;另有观点认为,被害人承诺阻却违法的依据是被害人对个人法益的放弃,故应依事后被害人的意志进行判断,若事后被害人表示其不具有承诺的可能性,推定承诺不可成立;亦有观点认为,这种合理的推定,既不是从行为人的角度,也不是站在被害人的实际立场,而是“在社会观念上一般能够推定出被害人承诺的状况。”[3]411
推定承诺作为违法阻却事由,其成立与否的判断是一种对行为人行为的法律评价,其评价标准应是客观而非主观的,不可仅依行为人或被害人的主观意志进行判断。若依行为人的主观意志,其自然认为自己的侵害行为具有被害人承诺的当然可能性,这将导致该判断标准形同虚设;若依被害人事后的主观意志,则事后被害人同意行为人的侵害行为,其行为就不具有违法性,这将使对行为人的主观考量失去意义,也是不合理的。行为时被害人是否具有承诺当然可能性的判断,行为人是判断主体,被害人的主观意志是判断对象。推定承诺的正当化依据是对被害人的法益保护,故判断标准应是对被害人法益保护是否有益。通常情况下,若一般人认为一定限度内的侵害行为对被害人法益保护是有益的,即可认为具有被害人承诺的当然可能性。
德国刑法学者克劳斯·罗克辛认为,应依推定承诺的法益类型分别确定推定意图的标准。他将推定承诺行为分为“在他人利益中的行为”和“在自己利益中的行为”。“在他人利益中的行为”指为被害人利益的行为,“在自己利益中的行为”指为行为人利益的行为。“在他人利益中的行为”依侵害的法益可分为:与物品有关的决定、与人格有关的决定、现有的决定(与生命和死亡有关的决定)。不同决定所依据的推定意图,其判断标准是不同的。对与物品有关的决定就适用下述规则:一个人,在客观权衡中考虑到法益承担者明显具有优势地位的利益,是能够以推定同意为根据的,除非,这个行为人知悉了那些表明法益承担者相反意见的情况。[2]537与人格有关的决定,正好适用与物品有关的相反的规则:行为人不允许从一种推定的同意出发,除非,特殊的情况产生了这种认定,即法益承担者是同意这种侵犯的。[2]538在现有的决定的情况下,若条件允许等待被害人现实承诺时,就不能对其意志进行推定。在所有其他的情况下,人们就必须通过推定的同意,将拯救一名当时无法表达自己意志的患者的生命的手术正当化。[2]539 至于“在自己利益中的行为”,他则认为应当适用“与人格有关的决定”的判断标准。
笔者认为,罗克辛的上述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与物品有关的决定仅涉及被害人的财产法益,故可允许行为人依一般人观念对所侵害和挽救的法益进行比较,若挽救的法益大于侵害的法益,在无相反意见的情况下,被害人即具有承诺的当然可能性;与人格有关的决定涉及的是被害人的人身法益,由于缺乏客观标准且人的思想具有多样性,故无法推定他人对自己人身法益的处分意志,推定承诺仅为特殊情况下的例外;现有的决定事关被害人的生命法益,无论被害人事前是否有承诺、有何承诺,都应从挽救被害人生命法益的角度进行推定并采取行动。而“在自己利益中的行为”,行为人是牺牲被害人的法益挽救自己的利益。对于被害人而言,由于客观优越利益不存在,被害人表示同意的可能性比较低,因此,根据推定承诺而否定社会危害性的,应当仅限于极其例外的场合。
3.行为人具有推定承诺的认识
推定承诺要求行为人具有推定承诺的认识,即要求其对被害人的承诺进行了推定。如果行为人行为时没有此种认识,即使该行为获得了被害人的事后追认,也不可阻却其违法性。这与被害人承诺的侵害行为中,行为人需认识到承诺的存在的要求是一致的。如果实施侵害的行为人没有认识到被害人允许其实施侵害行为,那么,他就是在一种应受谴责的心理状态下实施客观的侵害行为,对于这种性质的违法行为,法律不能将其正当化。
行为人具有推定承诺的认识,并不是对被害人承诺与否的准确判断,而是依事实情况对被害人承诺的当然可能性的一种推定。此种推定作为一种主观认识,就可能存在认识错误的问题。即:不具备推定的现实条件,行为人错误地认为具有此种现实条件,并依此认为具有被害人承诺的当然可能性。虽然不具备推定的条件,但如果行为人错误地认为条件具备的话,将成为假想的推定承诺。这种情况,行为人如果存在良心上的审查,将会不问及错误问题能够在整体上排除违法性进而被正当化;如果不存在良心上的审查,将探讨对客观的前提事实的错误成立问题。[4]318应当说明的是,此种良心上的审查,仅是在假想的推定承诺场合行为人的一种审查义务,并不是推定承诺成立的条件。推定承诺作为正当化事由,不应当要求行为人的审查义务。这种义务导致了这样一种无法得到坚持的结论:有人并没有充分地审查正当化的条件,但是,在存在一种正当化根据和行为人在认识该根据的存在中行为时,自己却必须由于故意构成行为而受到刑事处罚。[2]412一个人在认定一种能够对推定同意加以肯定的情况之后,只要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即使他丝毫没有进行事后的审查,也能得到正当化。如果这种由行为人轻率地认定的推定同意的条件并不存在,那么,他就是以对一种正当化根据的事实条件认识错误进行行为的,根据限制性罪责理论,他的故意就被排除了,并且会使由于过失的构成行为而进行的惩罚成为可能。[2]540
4.行为人出于正当目的
行为人实施推定承诺的行为需出于正当目的。何谓“正当目的”,学者们的理解存在分歧。英国有学者认为,“正当目的”应为反对无意义的牺牲。在对其他人或社会无明确益处的情况下,将否认个人遭受损害的自由。且有判例认为:互殴的被害人承诺不成立,因为公共利益不允许人们因不正当理由承诺伤害各自身体。在大陆法系国家,有的学者认为,“正当目的”是指为了被害人的利益。在某种紧急状况下,之所以能够推定被害人会允许侵害行为,是因为实施侵害行为是为了实施另一个对被害人有利的行为。如果某一侵害行为完全不是有利于被害人的,那么,就不成立推定的承诺。因为虽不排除被害人为他人利益牺牲个人法益的情况,但为挽救自身一法益而牺牲另一利益才是人之常情;也有学者认为,“正当目的”不仅指为了被害人的利益,还包括为了行为人和第三人的利益。之所以允许存在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推定法益主体的同意,并不是基于客观的利益衡量的原因,而是从法益主体自身的意志去推测,正是由于这种行为可能得到法益主体的意志支持,该行为由此才能被正当化。从客观的角度看,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种行为恰恰是同意案件中常见的类型。[9]144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即:“正当目的”既包括为被害人利益,也包括为行为人和第三人利益,因为被害人的真实意思可能即为牺牲个人法益维护他人利益。在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应当充分考虑人们行为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充分尊重个人法益处分的自由意志。在推定承诺的场合,不可简单依人之常情对被害人的意思进行推定。应当说明的是,虽为被害人利益和为行为人或第三人利益均为推定承诺的“正当目的”,但出于不同目的而实施的推定承诺行为,被害人承诺当然可能性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对此,上文“被害人承诺当然可能性”部分,已有详细论述,故不再赘述。
行为人出于正当目的,还要求行为人实施推定承诺的行为仅出于正当目的,不可有其他任何非正当目的。表现在行为上,即要求侵害行为与正当目的实现具有相当性。如果甲男为抢救负伤昏迷的乙女,将其衣服撕破为乙女包扎伤口的行为,可说是符合社会相当性的行为,但如果甲男在此过程中,肆意对乙女进行抚摸、亲吻等猥亵行为,则行为不能说正当。[3]412 笔者认为,由于缺乏客观的判断标准,不宜将行为符合社会相当性作为推定承诺成立的一般条件,而应将其纳入行为人是否出于正当目的的判断中。
三、结语
《庄子·秋水》中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故事。该故事中,庄子虽非鱼,却由“知之濠上”而得出“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的结论。可见,在事物可知论的基础上,能够依观察对他人的主观意志进行合理推定。推定承诺即为对被害人主观意志的一种推定,其作为刑法上的正当化事由,正当化依据是对被害人的法益保护,核心是个人法益的自由处分权。然而,因该正当化事由阻却了法益侵害行为的违法性,故其成立需满足严格的条件。具体而言包括:被害人对法益有权承诺、被害人具有承诺能力、被害人承诺的客观不能、被害人承诺的当然可能性、行为人具有推定承诺的认识、行为人出于正当目的。其中,被害人承诺的客观不能要求情况紧急,行为人出于正当目的要求行为与目的之间具有相当性。
[参考文献]
[1] 邓子滨. 刑事法中的推定[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135.
[2] 克劳斯·罗克辛. 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M]. 王世洲,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5.
[3] 田宏杰. 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0.
[4] 金日秀, 徐辅鹤. 韩国刑法总论[M]. 郑军男, 译.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5] 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M]. 注评版.陈忠林,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141.
[6] 蔡墩铭. 刑法精义[M].第2版.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5:197.
[7] 保罗·H·罗宾逊. 刑法的结构与功能[M]. 何秉松, 王桂萍, 译.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5:78.
[8] 约亚书·德雷斯勒. 美国刑法精解[M]. 王秀梅,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539.
[9] 车浩. 论推定的被害人同意[J].法学评论, 2010(1).
[责任编辑:陈可阔]
Abstract:Deduced consent as a cause of justification in criminal law,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by criminal law theory and practice in various countries. But because it is similar to victims consent and the act of rescue,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character, the legitimate ground, and the establishment condition of it. Deduced consent is an independent cause of justification which extends from victims consent. The legitimate ground of deduced consent is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legal interests, and it should meet the strict conditions, including the same conditions with victims consent and some special conditions. Victim entitled to consent, able to consent, objective impossible but subjective possible to consent. Actor convinces the consent and acts out of proper purpose.
Key words: deduce; victims consent; deduced consent; legitimate gr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