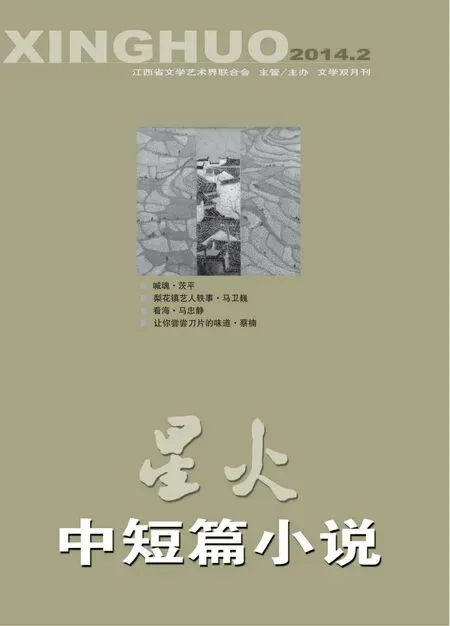困顿者(短篇小说)
□曾 平
1
对着镜子,第一次发现自己如此懦弱。我懦弱于看到他却放慢脚步,躲在没有围墙的世界里,用手中的纸屑堵住嘴,然后不加思索地转身离去。往回走时,我几次扬起硕大的手掌,试图狠狠地扇自己几耳光,但是我知道,即使我那样做,内心也没有丝毫羞愧。
在我的记忆里,这是第五回了。远远地看着家门却永远不敢光明正大地走进去。我对自己说,在那里,我害怕的东西,害怕的人实在太多。我对朋友说,在那个世界里,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后就会迷失,乃至堕落。在众多的朋友之中,没有人会对这个说法有意见,唯独他,严信,我最要好的朋友和老乡,令我捶胸顿足。
那天,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指着我额头、眼睛、鼻梁、下巴和胸膛骂我心虚,骂我虚伪得令他毛骨悚然。我起初认为他是拿我开玩笑,当我看到他那张比往常严肃千倍的脸时,我知道平时喜欢开玩笑的他这次是认真的,我也知道那天大家都没喝酒,他也没喝。听完阿信的话语后,我感觉自己喝了酒,而且醉了。但我很明确地告诉你,我从不脸红。霎白的脸,总是保持我自始至终的体面和尊严。
就这样,一场盛大的毕业晚宴就这样被我们两人赤裸裸地搅黄了,闹得不欢而散。这是我未预料到的。所谓“期望之中,预料之外”。我没有抱任何的期望,反而生发出了从未有过的失望。耳边传来一阵一阵的“干杯”声,杯子碰杯子的声音,还有男女生吆喝着“在一起……在一起”的声音。而我的周围,每个人脸上都是沉默与忧郁。我没有预料到的还有自己竟然也在那个时刻变得目光呆滞,不喜欢搭讪,喜欢独处。
大学毕业是结束,结束的是那段蜗居宿舍、困乏教室、屁颠屁颠地冲向食堂只为挑几个好菜的时光;也是开始,开始一个人的远行,奋斗,拼搏,甚至哭泣。当提着厚重的行李,走出宿舍,慢慢在林荫小道上踱着步子,站在校门口,沉重地踏上车,才恍然发觉,其实四年的生活就如离别时脚下的路,很短却耐人寻味。望着汽车把我远远地从校门口带离,感觉只是梦过一场,顿时知觉全无。
来时,我成了陌生的城里人,远方的乡下人。归时,我转换了角色,成了远方的城里人,陌生的乡下人。我就是这样,渐渐地想重新找到回家的感觉,以便见到故乡不至于如此混沌与落寞。然而事实上,当我走出车站,踏上生养我十几年的土地,我才知晓,一切的人情世态都是虚无缥缈。在这里,可供游子呆立的角落消失了,供游子思念的背景也褪去了。淡了味的故乡,不再是我心仪向往的城市;变了形的街道,不再是我悠闲徜徉的天堂。一种别有的情感,如打翻了的五味瓶,呛入口中,滚进胸腔。
与其说这是繁华都市对我的礼貌拒绝,不如说是这个世界的渣滓尘埃令我望而却步。辗转几回,掰掰自己的大拇指,估算着流落的时日与场景。其实在我眼里,流浪是一场没有目的的旅行。但我更适合于流放自己,目的明显,悄然无声。就这样,跟随着日月星辰花草虫鱼的步伐,一阵一阵地抚平断断续续的思绪,亲近遥远。
2
那晚,夜色渐凉,山边寂寥。没有人知道我会回家,就连爱操心管闲事的母亲也置之度外。月光静静地照着我孤独的身影,风一股劲儿地往身上吹,身旁的草木微微颤动。我提着即将散落的行李,踉踉跄跄地来到门边,重重地丢下右手的包裹,脚不自然地跺几下,五指撒开,伸缩了两回,用宽大的手掌连续拍打着大门,回音阵阵。
许久,门没有动静,依旧挡在眼前。我甩掉绕在左手的塑料袋,正准备双手并举拍打时,只听见门后的凳子“砰……砰”两声倒下,门开了。透过缝隙,里面漆黑一片。走进去,墙壁四面闪出两道微芒的白光,我记得那是房子竣工时,外公送的匾,镀了层金的表面,更多的是掉了颜色的黑圈。我轻声地像贼似的走进房间,硬邦邦地躺在铺了床单的木板上,回想起自己刚才的举动,瞬间的黑暗就无声息地将我吞噬。
这是我第六回采取这样的方式回家,其中五次是用这样的方式告别。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严信口中所说的,是踩着心虚的节奏,是披着虚伪的外衣。相反,我感觉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活生生的世界。我害怕白天被母亲拦住,嘘寒问暖,而自己却要强忍着说,在外的这段时间里一切安好;我胆怯于遇见乡亲,问长问短,而用脸上的微笑抵御内心的彷徨;我更痛恨于见到同村的严信,这并不是我们发生不愉快一幕的缘故,而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而今却有天壤之别。毕业晚宴那晚,他签了一家单位,据说是一家国企,他也俨然成了实在的城里人,人人羡慕,我却保持异常的淡然。他尽情地笑着,离席唱和着,时不时地回头看我一眼。那时,我感觉自己的眼睛、身体、灵魂都渐渐麻木了。所以当他破口骂我时,我已然找不到方向,全然不知所措。
所有的场景都被灌注脑中,一幕一幕接连不断地放映着。窗外的月光皎洁柔和,斜穿进房内,定格在床沿边的方形木桌上。我用双手捂住眼睛,强迫自己忘记,不要忆起。在梦里,我听见母亲的咳嗽声,一阵连着一阵,有时她拍打着胸脯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有时她坐在床上,眼睛盯着墙壁上的那张老照片,照片中有我,还有姐姐。她看一会停下来,用瘦骨嶙峋的手端起床边冰凉的白开水,大口大口地吞咽。有时候大厅内沉睡的老狗会被母亲的声音吵醒,但她似乎并不在意。时间就是这样,一波一波地把人变老,忘记了生活的节奏,而母亲就是最好的牺牲品。
一切都是恍恍惚惚的,但足够让我惊喜又惶恐。梦里的父亲脚步迈得很快,我能试图看到的只有背影。从小到大,他从没有回过头,从没有对着我笑过,他在我眼里是好人,也是害怕遇见的魔鬼。我曾有几次在背后骂他,甚至打他,而他总是不还口,不还手,任我一个人在风里哭泣与哆嗦。因此,白天回家我惧怕看见家四周的一切,实则是惧怕看见父亲,他背手踱步的姿势总是让我毛发耸起。母亲说,这是骨子里对父亲的敬意和尊重,而我却认为这是最好不过的违抗与背叛。
最后的梦境,随着几声鸡鸣应声而始。房内的墙壁上像学校放电影一样显示出阿信的模样。圆圆的脸蛋,短发竖起,黑眼睛里总裹着光芒,西装革履打扮,脚上更是锃亮的皮鞋,就连鞋底都能看见那防滑的波纹。他站在墙壁上对着我笑,嘴里叼着一根香烟,左手拿着一沓材料,右手不停地指上指下,指向我,指向我后面的亮光。我掀起被子蒙住头,他却歪头歪脑来回地在被窝伸展,用眼里散发的光对准我,大笑,然后指着我说,你怎么又回来了?你不是不敢进家门吗?冷汗直逼手掌,我慌乱地抹抹额头,用力地蹬开被子。转眼间,梦里的现实就被光秃秃地敞开在了黑夜里。
窗外渐渐地亮了,夏季的风吹来,地上的碎纸扬起,一同镶嵌在没有装饰过的门窗里。透过门缝,我看见对面房间的门开了,开得很小很小,小到只够挤进母亲的身体。
3
走出房间,大厅内的座钟敲了九下,停了。屋前的山枣树枝繁叶茂,像一位打扮过的即将出阁的少女,风姿绰约。我穿着凉鞋,双手叉在腰间,缓缓地移动着步子,地上的沙子被踩得滋滋作响。老狗横躺在屋檐下,睡眼惺忪的姿态,我恨不得上去踹它几脚,还我世界的安宁。不远处,母亲正提个菜篮在地里左顾右盼,弯下的腰,像一张弓,却失去了箭的锋利。
我蹲坐在地上,旁边的泥土总是有种粪土味,呛鼻得很。但我天生就喜欢,常常玩弄于手掌,即使是饱餐一顿之后,也总想用卷起的舌头舔舔。我只是舔舔,不敢大口地吞下去,否则站在背后的父亲会用牛鞭抽打我。他从来不告诉我吞下去的后果,只是不顾一切地狠狠地抽我。其实我知道,吞下去会屙不出屎,屙不出尿,然后活生生地被憋死,这是阿信从小就告诉我的,我从不怀疑。
现在我就坐在这粪土之间,抓起一把,直勾勾地盯着,张大嘴巴正准备尝尝。忽然,眼前就出现一条鞭子,朦胧地听见了鞭子抽打时发出琐碎的声响。阿信也在一旁监视我,用诱惑的词语怂恿着我,用不屑的口吻鄙视我,“你敢吗?不!你什么都不敢!”“你吞个试试!滋味肯定美。”两种声音相互交杂在一起,我紧紧地捂住耳朵,下意识地低下头,闭着眼,学做老狗的姿势。
总算安静下来了,脑袋还有些模糊。母亲的身影从我身旁掠过,我急促地把头抬起,看见的是正在寻觅食物的老狗。它摇晃着的尾巴像母亲扎的小辫子,它走路一前一后的姿势正合上母亲的步调,就连嚎叫和呻吟都像极了。我跟在它身后,摸索着它走的线路,然后用同样的动作,蹲坐,俯瞰,平躺着。若是同村的人看见我,一定会感到惊奇和难以置信,因为他们不懂狗的内心,但我懂。若是母亲见此状,她一定会拍手叫好,因为她成了儿子的榜样。尽管我不能够用恰当的词语来形容那时的情景,但我能够揣测出她内心的欢喜。就如一旁的老狗,对着躲在角落里的满脸是污渍却不能独立行走的小狗抽搐般大笑。
一切都超出我意料之外。母亲她没有微笑,脸上的表情显示出她很痛苦,像是躺在手术台上,被人用针一针一针地扎下去,但她忍着。重重地把菜篮摔在地上,里面的红辣椒滚落一地,我准备用手捡起,却发现都被自己踩在脚下,我来回地进退了几步,腐烂的图画就毫无保留地展现在眼前。我快速利索地用手抓起,不一会,一阵麻麻的酸痛在我身体里蹿动。我跑开了,头也不回地跑开了,躲在一个看不见光的角落里搓动手脚。从缝隙里,我看见菜篮子不见了,满地的粪土还在。
我不敢直视,蒙住头,告诉自己,这是在梦里。但母亲的呼喊声又让我胆战心惊。我开始怀疑,但不敢询问。我害怕结果,哪怕是好的结果,我也害怕,害怕太过真实,亮瞎我双眼。屋外艳阳高照,我不知道为何自己看见的会如此黑暗,难不成自己在这家里做了一回牲畜,弄不懂春夏秋冬。
4
其实,我是知道这个季节的。只是我不太确定。我几次站在母亲面前,结结巴巴地问起。她总是回避我,用其他的事情搪塞我,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把我看作家里的怪物一般,就连老狗的目光,鼻子里呼出的气,都掺杂这意味。后来我学聪明了,我自己一个人去找。走到屋门口的千年古井前,纵深一跳,只见“扑通”一声,而后就是“咕噜咕噜”几声,我试图伸长脖子,看看外面的动静,母亲的反应。围观的人都来了,只要是生活在屋子里的有生命呼吸的东西都来了,围在井口,拼命呐喊,乃至尖叫。
我听不见任何声音。我只看到母亲晃动的人形,长短不一面目狰狞靠近水面,试图靠近我的脸。我怔了几下,就闷头躲进水里了。水很凉,但自从我进入它的身体后,我发现它变热了,有点沸腾的感觉。我的身体从上到下都是温暖的,除了在水里依旧散发光芒的眼睛。只有它还充满着血丝,越积越多,越浓越密,而后我就完全失重了,四周的黑暗裹着我掉落,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房间里,全身上下都是新衣服。有几件我是很熟悉的,特别是那件印着骷髅形状的黑色的衬衫,我喜爱极了。我每次回家都喜欢拿出来穿一次,站在镜子前左摇右摆,然后赶紧脱下藏在我房间衣柜不起眼的角落里。那里黑黑的,灯光照射不到,眼睛也看不到,那样我才安心。此时此刻,我已穿了它一晚上,甚至超过了二十四小时,我想着想着,心里越加恐惧。我恐惧于胸前的骷髅会跳出来,紧紧地掐住我脖子,断了呼吸之后,就开始用嘴撕裂我的身体。啃碎了的骨头,血淋淋的皮肉,还有血迹斑斑的眼球,依次摆在床头挂在墙上。然后阿信就会喊家里的老狗过来尝尝鲜,它每伸出尖尖的留着涎水的舌头,我就会随声附和着阿信傻笑,然后唯独自己发出凄清的惨叫。
没多久,母亲端着饭菜走进了房间,放在床边。我迅速地直立起身子,贴在她耳边说,这是夏天。她朝我笑笑,扭转头去,不再搭理我。我心想,母亲以前肯定不知道,听了我的话之后才明白的,所以她才会默默地承认。本打算偷偷地躲在母亲身后看看她的表情,但当我走出房门时才发现,母亲站在浅浅的水缸前俯身啜泣着。我不敢靠近,只能远远注视着。突然,门口的老狗狂吠着,盯着一条黄毛竖起的小狗。我跑过去,拿起旁边一把锋利的柴刀,用力地投掷过去。只听见对面“嗷嗷嗷”传来几声尖叫,那似乎是一个人,走近一看,我整个人都吓傻了,手脚有种被剁了的感觉,麻麻的,软软的。我看见他几次想爬起,几次却又倒下,他想试图抓住我的手,我本能害怕地拒绝了。当我转过身子不再去看时,一只手拍了拍我左肩,右肩。
“是我。”
是母亲。
就这样,我像狗叼肉一般地被母亲拉拽进了房间里,她一声不吭地看着我,用嘴吹吹手中熬好的汤,红红的,像从活生生的老狗身上抽取的。我不敢把嘴送过去,只是用鼻子来回在碗的边缘闻闻,我害怕里面浓浓的血腥味。母亲的脸色变了,她生气了,我清晰地看见她额头上的皱纹在蠕动,嘴唇在不停地哆嗦,手也在抖动。忽然,碗落了,砸在地上,“砰砰”的声响在屋里作响。我指着地上的碎瓦片,它那闪光的划痕让我目不忍视,汤药就这样在我四周流窜,此刻,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从我身体里流出的血,臭气熏天。
5
我呕吐得差点撞墙的那天晚上,母亲不在家。等她半夜回来一瘸一拐地提着药来房间时,我早已倒在床头艰难地呼吸着。她看见我痛苦的面孔,就把药甩到一旁,两步当一步地伏在床前,用双手轻轻地拍打我脸颊。在昏黄的灯光下,从我还留有一丝亮光的眼睛里,我看到母亲表情里所坦露的惊慌和不敢面对的绝望。随后,她用颤抖的口吻在我耳边说道:“伢子,你……你感觉好吗?”我先是摇了摇头,随后又点了点头。她把手背贴在我的额头上,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再接着,我也迷糊了,许多黑幕从天而降,蒙住眼睛,就连我双手所触摸到的也是空空的。
我以为就这样一辈子不省人事,灰溜溜地躺在房间里,眼睛闭着,生命苟延残喘。然而,习惯打破了这个看似不好的僵局。第二天,太阳升起,我也习惯性地从蔓延着诸多气味的床上爬起。还没等走出房间,透过糊了泛黄的纸的窗户里看见母亲带一老头进了屋。老头六十上下,不高不瘦,满脸的胡子,特别是下颚的白胡须,总给人一种神秘感。我踉踉跄跄地走过堂屋,老头不眨一眼地直勾勾地瞅视我,十根手指不停地在来回拨弄。清晨的阳光洒在脸上,有些迷糊,有些清醒。
没过多久,母亲就把我带到屋后一个小木屋门前,我走进去,她怔怔地站在门口。小木屋里,有两张凳子,一张桌子,墙壁能够透光通风缝隙很少。坐在正中间的就是那老头,端庄严肃,面无表情。他左手端着一碗水,透过极其微少的光看见在那上面浮着一层米,右手执着已然修理好的笔,笔尖挺直地指向我。我后退了几步,不敢向前。他起身了,信步走在我面前,吸了一口水,间隔几秒又吐了出去,然后拿起笔就在我面前晃动。就这样,两个小时里,他做着相同的动作,娴熟至极。
走出木屋,天外的亮光刺眼,顿时感觉火辣辣的。母亲正和老头轻声细语地说着听不懂的话,并且时不时地看看我,不知为何,那时我精神甚是恍惚。我恍惚于眼前出现幻觉,它把我固定地围困在荒凉的思维情境下,让我失去了辨识的能力,让我丧失了对未知世界感知的勇气。我总是把自己藏在一个了无人烟的角落里,任母亲的呼唤在墙外流传,而我却将其视为另类。以至于现在我会把那老头看作是父亲,他们交谈甚欢的表情正合我意。然而事实上,我痛恨至极。
自从这次的“驱邪”行动之后,虽说我脸面上展现出的精神尚好,但内心我知道,我仍然依附着别人的灵魂让自己行走,乃至存活。我的身体是腐烂了的,那由头到脚所挥发出的死亡气息毫不吝啬地穿透众人的心胸。我希望第一个屈服于自己的是阿信,然后是囚禁在牢笼里永远走不出的那个自己。因为在我观察的世界里,痛苦就是对幸福的最好放纵,而余下的远远比不上如此。
6
五天之后,那老头又出现在屋后的木屋里。我趁母亲在厨房生火的间隙,偷偷地逃离了房间。蹲在远处的老狗看见我的身影从门后边遁去,就站立起来,不停地狂吠,追了我好一段路程。我几次回头抓石头扔过去,丝毫没有效果,最后我跑过村里的桥,把木板撤了,这才彻底断了它的念头。
于是,我放浪疯跑在村庄的田地里,穿梭在村庄的房子间。我看见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或摇头晃脑,或用鄙夷的眼光注视着我。起先,我把头抬得老高,慢慢地,我便低着头,最后脸色苍白,用手蒙住嘴走进村人的视野。他们目光寒冷而刺人,像刀片一样划过脸颊、心胸、皮肉和不可预知的面孔。偶尔,从不远处传来他们的谈笑声。
“那不是桥北林海家儿子吗?”
“是啊。大学毕业,刚回来不久。”
“据说在外面犯事了,回家避避风头。”
“据说得了一种怪病,有时候疯疯癫癫的,有时候清醒异常。”
“祖辈手里造的孽……估计坟被掏空了。”
就这样,一层层有关这样的声音不断地循环在脑中。我重新加快了脚步,毫无目的。正当我苦苦思索不知所终时,我迷迷糊糊地看见了阿信,他就站在离我不远的田埂上,嘴里嚼动着一根随手取下的稻草,左手插在口袋里,右手不停地上下晃动,似乎指向我,指向我额头上那老头给我画的线头和符号,然后就是对着我发出一阵阵阴沉的笑。我想伸手去握住他的手,他拒绝了。最终我们没有任何的交谈,就这样擦肩而过。我是恨他的,从这一刻开始。我也知道,他也是恨我的,从很早的时候就有。
我是疯子,很多人这样说我。包括阿信。
那天我问他,他没有任何表示,我便认为这是默认。我几次用手捶打着头,手脚不停地狂舞,有时撞向墙壁蹦蹦作响。越是用力,头脑中越是闪现村人说话时的那神情。那天,母亲狠狠地抽了我两耳光,深深的五指印挂在脸上,像极了五色花。我蹲在墙边蓬头垢面,脸上露出狰狞的表情。母亲哭了,她站在我面前,哗哗地落泪,不停地蒙住嘴巴,呜呜地狡辩说我不是疯子,不是疯子,是大男孩,是家里的好帮手。我凝视着地面,眼珠子瞬间变得坨大,血丝密布。
老狗伸出舌头从身旁走过,毛茸茸的尾巴摆在脸上,肉体便有种瘙痒。我看见它时不时回头,眨了眨眼,我踹一脚过去,它也没有反应,只顾摆正屁股,对准堂屋正中的那张八仙桌。于是我赶紧跑进房间,把门窗紧闭,双手按在地上,背弓得很弯,就这样来来回回地把自己训练成狗的样子。毋庸置疑,老狗不是疯子,所以当我熟练地学会它的动作时,我高兴极了,我终于可以堂而皇之地告诉村人这个天大的秘密。
我不是疯子。
但我不是疯子,我会是什么呢?
母亲说,我是孩子。孩子年少不懂事,喜欢闯荡、流浪,擅长幻想、游离。当被生活的困难所阻扰就会丧失心智,然后就封闭自己。然后母亲说,我是病人,需要每天吃药接受治疗,不然就会神志不清,走路跌跌撞撞,需要别人提醒。听后我脑中一片混乱,猛地塞住耳朵,长叹一声。
我不是疯子吗?
不!我是。
7
关于自己,我被诸多的往事拖入泥沼之中,难以自拔。因而有时我会独自一人封闭在房间里,对着镜子发呆。我看见镜中的自己,额头凹陷得很深,眼珠子里藏有污垢,脸颊多是划痕。似乎这是生活给我的装饰物,或者垂死挣扎过后的战利品。
就这样,我欣赏着自己。正如老狗守着骨头,母亲盯着我。我被四周的景物监视着,就连呼吸是否均匀,放屁是否和谐都在这个世界的掌控之中。我所能清楚的是我有手,有脚,还能独立行走,还可以耍几样把戏,让老狗也会狠狠地瞪着我就像瞪着一根即将到手的咸骨头。
其实,在这之中我是反抗过的。我曾慌乱地逃离到了父亲的身旁,围在他身边,抓起一把沙土就朝我厌恶乃至痛恨的人丢去,我看见他们脸色变了,变得异常迅速,让我一时还无法判定是喜欢还是愤怒。只是停留了一会,眼前的泥土就被我掏了一个大窟窿。瞬间,我的脑海里就倒映出父亲的模样,他告诉我,他有些冷了,尽管那是在炎炎夏日。我仔细揣摩着父亲的言语,我顿时感觉心热了,热血沸腾。
为了此事,我也去找过阿信,让他给我说说儿时的故事。然而,他讲到一半就借口回家然后再也没有来看我。听母亲说,他走了,去了别的地方,离家很远。我猜想是不是去了我们一起上大学的那座城市,擦肩而过的身影总是闪过眼前。索性我也找个时间,背起回家后还从未打开过的行李,磕磕碰碰地远离。却不知母亲早早地守在我自认为天堂的十字路口,她背弯得很下,像是在给儿子鞠躬,或是乞讨。
最终,我离开了。走过一个个驿站,停留的街角成了城市腐烂的战场。那令人眼花缭乱的高楼,那催人情绪兴奋的酒吧,那穿梭于红绿灯之下来来往往的过客。阿信,他藏起来了,藏得很深。或者他就坐在路边,扮演了一回地地道道的城里人,我却闻不到乡人的气息。于是,我也失踪了。我困惑于为何我走的路总是没有尽头,舒展的路径就似乎是我的神经,走一段,神经绷紧了一些,最后没有归宿,不知所终。我以前见到的阿信不是这个样子。他嘲笑我,他让整个世界的人都觉得我是他最无能的朋友,最丢脸的老乡。所以他才会落下我,一个人抛弃于尘世的烟火,萧然而去。
即使现在我也无法改变自己在他心目中的样子。丑陋,低能,落魄。我曾想找个时间告诉他,我恨他,实实在在看不起他。但当我被眼前的情境淹没了思绪之后,我看不起的其实是自己。我自责于自己的狂妄,就如父亲,他完完全全地掌控这个家,掌控每个人的生活。所以,每当我想要逃避时,内心底就有种别样的动力,那是一股早已该喷发出的勇气。然后不自觉地学着众人的口吻说,我是迫不得已。我是为你好!
的确。父亲为我好。他把生活的脏话都藏在心里,又用文明的动作示范给我。他用牛鞭抽打我的样子,他在枣树下踹我就像我踹老狗用力时的样子。但是我常常茫然,我设想自己就是一头牛,一条老狗,守在村庄的土地上却忘了用力嘶叫,乃至迷失在希望的田野。
我是虚伪的。我虚伪到把自己掌掴之后而不去四处宣扬。然而现在的我再也做不到了。回到村庄的日子,见到的都是真实的。不管是人,还是老狗,甚至是种在屋门口那棵不会开花不会结果的不知名的树。我感觉我是醉的,没有喝酒却胜过数杯烈酒。醉过一场虚无人生,醉过一回生死诀别。最后,在困顿的环境里,所有的一切都只剩麻木的记忆,那似乎就是爱与恨的交织。
8
梦里醒来,已是凌晨四点。
深夜的楼道里,依旧是嘈杂的脚步声。我四肢僵硬地躺在床上,身体被高高的棉絮垫起。相邻的病床上,左边是一位患有高血压的老人,右边是一个刚上小学就得了癌症的孩子。老人眼睛紧闭着,脸上始终露出温和的微笑。亲人时刻守在床头,按摩、喂饭、暖手、谈心。孩子在母亲怀里撒娇着,有时从父亲手里夺过玩具,调皮地在床上欢呼。
墙上的时钟滴滴答答地走着,窗外的月光落了一地。回过神时,大姐站在我面前,母亲坐在床沿,手不停地擦拭着眼泪,大姐轻声细语地说道:“弟,一切都好起来了,好起来了。你知道吗?母亲守在这四天四夜了,那天知道你在学校出事后,我们就匆忙地从家里赶过来……”
听后,我迟疑了好久,随后捂着脸,大声地哭着吼道,“阿信!阿信呢?他……他还好吗?我……我对不起他。”
“那晚出事之后,他就再没醒过,挨到清晨的时候,就落气了。昨天村子才匆忙地为他办了丧事,很隆重……”大姐的声音低沉着,脸上强忍着平和的姿态。
我侧过脸,打开抽屉,随手翻开印有雪白花纹的日记本。用冰冷的手写下:
“我是疯子。疯于困顿。
困顿于裸露的生命,死去的人。”
合上的时候,一张黑白照片落于手心。那是十五年前,父亲留给我的笑脸。十五年之后,我情愿当一回疯子,甘心被这微笑鞭打,被我与世界的“仇恨”围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