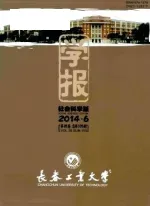汉赋与中国文学自觉关系探讨
李晓红
(山西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工商管理系,山西 太原030031)
一、前言
近代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为寻找民族自强的出路,开始了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各种政治理论的探索与借鉴。西方理论学说直白、简洁的语言表达方式对知识分子形成了很深影响。一时间,知识分子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探讨风起云涌,许多人认可了外国文学舶来品的价值,而将中国儒家文化视为政权衰颓和思想腐朽之根源,最终进行了深刻的文学革命,形成了简单通俗的现代文学。而这种调整使得中国文学自身特色与美感大打折扣,几千年文明精粹不得彰显,令人扼腕叹息。本文对汉赋进行管窥,寻找中国古代文学自觉意识形成和繁盛的遗迹,来揭示中国古代文学深厚的造诣,借以提升自身的文学修养。
二、汉赋实现了文学地位的变迁
(一)文学不再附庸于其他目的
汉代以前的文学主要以满足政治、宗教和道德教化的需要为目的。如《论语》主要内容有礼义廉耻、忠诚孝义和君臣德行,主要为道德教化和政治管理服务,再如西周的“祷”“语”是介绍宗庙祭祀的文章,“辞”“诰”用作上下级之间的交流,“命”传递君主意旨,主要是为宗教和统治者服务,都不是为了纯粹的文学而创作,而是作为一种表达和宣扬某些特定目的辅助工具,形式载体。先秦文学是文学发展的初级阶段,其观念尚未完全觉醒,体系还不完全,处于一种迷惘和懵懂的摸索期。“赋”是在西汉时期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文体,所谓“赋”原本是将登高时的见闻,赋以其形状,铺陈描述事物形态特征的文学形式,它的出现究其社会原因,是由于西汉初期到汉武帝、汉宣帝时期,对思想的束缚较少,从而为自我意识的觉醒提供了沃土。[1]
“赋”的产生和繁荣体现了文学从重实用到并重审美;从重政教到重人的思想和情感;从公共责任意识到主体个性解放的转变。赋成为与诗、诸子政论、经、史同等地位的独立文体形式,表明文学已经从对政治、宗教、道德的依附关系发展成与其对等的关系。
(二)文学形成了其独特的价值
汉赋对中国艺术形成了一种新的启发,它以大胆的想象、华丽的辞藻、夸张的修辞极力营造的“巨丽”之美,赋成为一种艺术的文体,表现了赋家对艺术追求的重视。汉赋作家已经初步形成了“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认识,突出了自觉创造艺术美的价值追求和文学艺术性本体的回归。
汉赋以一种包罗万象、纵览宇宙和发掘人性的视野描述这个世界,其眼界的开阔可谓前无古人,更为后人所瞻仰。这种文体独立于经传之外,又为经史所引用,使内容的实用性和形式的艺术性结合起来,并逐渐形成了体制完善、普遍认同的艺术文学体式。词赋家由于对艺术追求笔耕不辍的实践和创造性的探索开拓,使辞赋逐渐形成一种民族性的共同文体。
(三)改变了文人的地位
汉朝帝王宗亲都推崇辞赋,许多藩王大量网罗辞赋专家,梁孝王、淮南王就是典型代表,形成文人雅士“朝夕论思,日月献纳”的创作热潮,促进了辞赋风气的盛行。帝王重视和奖励学士,甚至委以重任,士大夫和官宦阶层都竞相进行赋词创作,尤以汉灵帝为代表,改变了以经学来评价人才的习气;创设了鸿都门,专门收纳辞赋文人高手,并时常进行考核,优秀者拜官授爵,极大地提高了辞赋家们的地位,使得文学学者不靠经学也能出世为官。有的皇帝和藩王还自己参加辞赋创作,为辞赋创作蒙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2]
三、汉赋彰显了文学的艺术性
(一)表现手法呈现多样性
汉赋体系完整,因此分类多样。从体裁上看,汉赋有骚体、散体和四言赋之分。西汉初期,汉赋家主要受楚辞影响较多,此时汉赋骚体赋为主,内容主要是表达自己的政见和感慨身世际遇,手法上已使用了铺陈夸张之手法,已经由骚体开始向赋体转化。西汉中期到东汉中期是汉赋发展最繁荣的时期,以散体大赋尤为盛行,其特点是结合了当时盛世繁华和皇室奢华享乐的特点,盛赞国运昌盛、物阜民丰的同时讽喻劝戒,形成一种复杂文体。从内容上看,汉赋又可分为叙事赋、抒情赋、说理赋和咏物赋。汉赋家们为追求赋的美感,在形式上多采用韵散夹杂的骈偶句式,讲究错落有致、朗朗上口,声韵上注重平仄和押韵,讲究抑扬顿挫、悦耳动听。修辞上,运用了排比、设问、虚拟、比喻、夸张、对偶、叠声词、拟声词和引用典故等多种手法,力求气韵贯通、声色俱靡、华美绮丽、变化多端。虽有堆砌辞藻之嫌,却真正将文章的形式美发挥到了极致。[3]
(二)意境上突出形象性
辞赋家们在炼字造句上,引用了许多艰深生僻的字,精雕细琢、博彩炫奇,力求通过字句技巧性的使用,拓展文章丰富的内涵和深渊的意境。赋通过极尽铺陈造势,夸张和想象,将看得见的事物和看不见的情感都赋以声、色、味、态、形、貌、体。将平淡化为鲜明,化普通为神奇,以动述静,以一景而生万象,动人心魄,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想象空间,衍生出余韵悠长、意趣渊深、蕴涵广袤的意境。
(三)词句上追求优美性
赋通过使用精致绝伦的语言,运用苦心孤诣的句式,于质朴之物润以外饰,赋予其千变万化的色彩,华丽多姿的线条,明丽动人的声韵。为了实现词句的美轮美奂,赋在字数、平仄声律和韵势上都极为讲究,以字的酝酿深邃美,以比喻展现生动美、以排比营造气势美,以对偶展现对仗美,以夸张营造鲜明美,以叠词营造声韵美,以拟声词营造象形美,以物之铺陈营造博识大气美,势必要将情感的表达,物之描述的感染力渗透到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五官感觉之中。让人参与到文采的盛宴和无感的享受之中。
四、汉赋引导了人们的精神追求
(一)形成了新的人文风貌
汉朝初期,学者们产生了经传学和辞赋的分流,而统治者重经学,以经学作为录用人才的标准,赋作家们的地位较低下,“为赋乃俳,见视如倡”乃是对其地位贬斥的评价,赋家为提高自己的地位纷纷兼修经学。而辞赋文体的盛行,又使得经学家们向赋家靠拢,形成兼采经学之实用与赋学之华美的格局,使其相得益彰、融合交流。由于经学本身以明经理政为主要职责,因此在汉赋中产生了讽一劝百的文体形式。
赋一开始以咏物为主体,后发展到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以曹丕为首,提出了“文以气为主,诗赋欲丽后”的观点,强调言止而意犹未尽,即在言的表象下,注重“言外之意”的体会,体现了一种哲学思辨和对含蓄美的追求。不受理法的拘束,自由表达真情挚意,是魏晋时期人们的文学追求。同时,这一时期由于文体多样化的形成,不同作家创作特点和观念不同,出现了文学批评之风。在鸿都门学影响下,形成了通俗的文风。
(二)衍生出新的理想目标
在先秦时期,学者们以文立说,重在辅助政治、人伦教化。到了汉代,赋家或为了歌功颂德,或为了讽喻政治、表达政见,或为了描述自然风物,或未了遣怀身世,不一而足。有了积极的创作动力和自由的创作意向,不再受到特定目的的束缚。将创作作为了毕生的追求和人生理想,赋家在构思时不再盲目被动,下意识地开始皓首穷经的创作,表达出自己对文学的独特构思和情感寄托。以作赋为代表的文学家们层出不穷,走向纯粹的文学探索征程。
(三)开阔了人们的审美眼界
赋作为一种文字表达形态,是有灵性的,不是实质上的物,但它通过将这个世界的一静一动、一行一态,将这个世界的纷繁复杂、多姿多彩通过千变万化的语言展现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滋润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在人们眼界中创造出一种艺术的价值观,将人性的真、善、美,物体的变、微、宏,潜移默化地注入人们的审美中,深化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悟体会和热爱。营造着人们发现美、欣赏美、追求美的人生志趣和审美愉悦。
五、汉赋标志着创作热潮的叠起
从西汉到东汉,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市井平民皆以诗赋创作为乐,并为此自铸新词,不断根据新事物进行创作。在创作上体现出了一种反复推敲、深思熟虑的严谨态度和创作风貌。如汉赋的群体性研究创作,是从西汉时期藩王诸侯处发端形成的。后藩王势力被削弱,作家群向京都聚拢,使创赋之风在中央也发展盛行起来,帝王将臣也都纷纷投入到辞赋的研究创作中,许多作家一生都致力于创作汉赋,大量作品得以问世。[4]而这些作品表现手法都不拘一格、形式各异,传达出各不相同的思想和心境,形成一种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例如东方朔笔调幽默诙谐,却抒发了自身不得志的抑郁情绪;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则写得直率旷达。曹氏三父子都是辞赋高手,曹操的《铜雀台赋》、曹植的《洛神赋》都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引领着一代文学新风尚。
这一点还可以从帝王的重视中看出。汉武帝读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时大加赞赏,汉宣帝时诏令辞赋家打猎游玩,命其作辞赋以较高下,以次第论赏,诵读辞赋的风气还在后宫盛行。光武帝因为赏识杜笃的诔辞而对其免刑。汉和帝因贾逵推荐李尤赋作,召其作赋,并授以官职。汉朝王室宗亲广招赋词专家云集其藩地,还亲自创作,赫赫有名的如汉武帝的《李夫人赋》。
六、结语
汉赋作为一种新的文体,体现了汉代作家文学的心血和精华,它预示着纯文学独立和繁荣时代的到来,它体现了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终于破茧成蝶,摆脱了附庸地位。汉赋家们在掘词运句上竭尽创作之极致,对后世的开放学风和文学大家们在文学造诣上的专研形成了深刻影响和启发,对词汇的丰富和语言学的发展贡献重大。汉赋对文采和意境审美的追求启迪了人们的艺术价值观念的形成,竖起了文学自觉时代的旌旗,并为唐宋文学的灿烂辉煌奠定了基础。
[1]高士琦.汉赋与文学自觉[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2.
[2]冯良方.汉赋、经学与文学自觉[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1,(11).
[3]蒲日材,侯艳.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0,(3).
[4]蒋文燕.20世纪汉赋分类研究述评A集[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