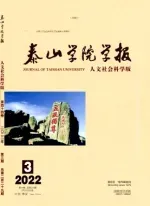邓小平根本否定“文革”与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丁龙嘉
(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 济南 250001)
十年“文化大革命”进行到晚期,其理论错误、实践失败,已成有识之士之共识。中国如何走出困局、汇入人类文明大道,由谁来带领人民承担这一历史重任,深为有识之士所忧虑。历史选择了邓小平。邓小平担当起并完成了这一历史重任。深入研究这一段距今并不遥远的历史,对于当下全面深化改革,颇有现实意义。
(一)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面临着两条路,一条是毛泽东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确定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引的老路,一条是另辟蹊径、开拓的新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即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左”的错误观点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总概括,也即“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指导思想,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密不可分。当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之前,于1976年2月毛泽东决定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于1976年4月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的集中表现的天安门事件遭镇压中,“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粉碎“四人帮”当日晚上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这一任职的历程表明,他的权力的合法性,在粉碎“四人帮”之前,主要来自于毛泽东,因为当时政治局不可能不通过毛泽东的提议;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基础依然来自于毛泽东,再加上参与领导粉碎了“四人帮”。
由毛泽东临终前指定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华国锋,本可以因势利导,妥善地另辟蹊径、开拓新路,但他的思想境界、政治胸襟、领导智慧、执政能力以及现实利益,决定了他无法站在当时中国社会所要求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时代潮头来引领人民前行。华国锋的思维和行事逻辑是,毛泽东给了他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合法性,他就必须维护、坚持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要维护、坚持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必须维护、坚持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必须维护、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这种逻辑的实质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就否定了毛泽东,也就否定了华国锋自己。这种逻辑在当时的实际社会生活中具体表现为:在政治思想理论方面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在实际行动方面阻挠、拖延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要求中央宣传口“凡是毛主席讲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指示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对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为了阻止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华国锋将“两个凡是”提到了领导全党和全国工作的纲和总指导方针的高度。1977年1月,他让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观点写进了他1月21日的一个讲话稿和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是年3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中,华国锋指示为他起草报告的人,中心就是按照“两个凡是”的原则来对待邓小平的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禁止把陈云和王震关于要求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意见载入会议简报。但正义的力量是禁止不住的。在党内外的压力之下,华国锋不得不表示:“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华国锋让邓小平复出是有条件的,他派人同邓小平谈话,明确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种大失风度的“交换”,遭到了邓小平的严词拒绝。
青山遮不住。1977年7月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虽然邓小平复出了,但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仍是障碍重重。天安门事件得不到平反,邓小平的复出就笼罩在一层阴影之下。华国锋在全会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仍然坚持“两个凡是”。
十届三中全会是为中共十一大召开作准备的。是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一大召开。这次大会,不但“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1](P820)。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高度赞美“文化大革命”:“毫不疑问,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烂光辉”;极力鼓吹当时抓纲治国这一战略决策与“文化大革命”的血肉联系:是“巩固与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不管华国锋如何维护、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实践,邓小平的复出终于将这道防线打开了缺口。因为邓小平的复出从两个方面为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条件,其一是,告诉人们“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错误的,“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是错误的,也就是告诉人们“两个凡是”是站不住脚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什么“伟大创举”;其二是,确定了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领军人物——邓小平,也可以说为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准备了舆论条件和组织条件。
(二)
邓小平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其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即1975年的全面整顿为第一阶段,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7年7月复出为第二阶段,复出之后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为第三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79年11月开始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前为第四阶段,开始主持起草决议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一致通过决议为第五阶段。前三个阶段和后两个阶段各为一个大的阶段。
1975年初的中国局势,可以使用“混乱”两个字来概括。为变“乱”为“治”,毛泽东确定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与“文化大革命”之前相比,邓小平的职务更多、地位更高了。这足以表明毛泽东对邓小平寄予厚望。此时毛泽东的心态是,允许邓小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某些极左做法,使局势安定下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不能动摇“文化大革命”的总的路线和政策,因为他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一生所作的两件大事之一,决不容许否定。而以江青为代表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势力,正极力维护已取得的党政军重要权力,并打着“文化大革命”的旗帜,疯狂作乱,以取得更大权力。已71岁高龄的、久经磨炼的邓小平,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要根本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尽力挽回“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并真诚地希望毛泽东能够有所悔悟,容忍自己的行动。如此的态势,注定了邓小平的结果是悲剧性的。
1975年,邓小平由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到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他以毛泽东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为旗帜,在全国展开全面整顿。整顿是从军队开始的。因为中共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自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军队被搞得相当混乱,所以毛泽东提出要整顿。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要对混乱的国民经济进行整顿。邓小平把整顿的切入口选择在国民经济的大动脉——铁路上。之后,是钢铁、军工、企业,是教育、科技、文化。全面整顿,得到了“思治”的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因而立见成效,单就国民经济来说,混乱、停滞的局面迅速改观,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11.9%,达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最高水平。
整顿进行到一定程度时,邓小平决定起草文件,以将整顿中建立的制度、取得的成果固定下来,更重要的是阐明正确的思想理论观点。这主要是后来被“四人帮”诬蔑为三棵大毒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三个文件直指“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应该说这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公开的全面的文字较量。特别是《总纲》将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作为纲,实际上是改变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惟一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是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否定。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把“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作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其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的看法,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2](P641)。但他又明白对“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所以,他希望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按照他的基调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是,邓小平明确地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园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以委婉的语言坚定地回绝了毛泽东的要求,实际上是同毛泽东在政治上的决裂。邓小平这八个字,不过是托词。其在之后的“检讨”中直白地说,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如果说,在整顿之中邓小平采用的方法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3](P81),用实际行动否定“文化大革命”,那么至此,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就走上“台面”了。此为第一阶段。
在第一阶段的1975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邓小平两次提出了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如何理解、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关系到当时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他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片面化,指出:现在实际上没有解决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在当时,邓小平提出的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但确实是破解中国困局的关键问题。在第二阶段,邓小平虽然尚未复出,但他在致中央的信中,循着上述思想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4](P157)。并先后四次表明:“两个凡是”不行,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在复出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郑重地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又鲜明地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4](P162-163)不久,中共十一大召开,华国锋在作政治报告时,不但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邓小平在如此的氛围下,针对“文化大革命”对党的作风造成大破坏的情形,致闭幕词时连续强调了五个“我们一定要”,即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艰苦奋斗、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邓小平的上述讲话和闭幕词,字里行间,针对着“文化大革命”,针对着“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他复出的宣言。
邓小平一复出,就自告奋勇主管科技和教育,当然还管军队。在邓小平看来,科技和教育,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而又是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他于1977年8月4日至8日亲自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后,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国务院正式批转了根据邓小平的批示精神制定的关于恢复高考的文件。这一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没有任何文化考试的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的举措,使更多的青年通过公平竞争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邓小平同时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肯定了中国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一系列举措,使“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鄙视知识、摧残人才的风气开始转变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尚。
邓小平在反对“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提倡恢复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党的优良作风中,实际上已经涉及真理标准问题,即判断是非的标准,是领袖的决策、指示,还是实践。当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公开发表而引起争论后,邓小平是中央领导人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这一正确观点的,之后,又给予了及时而有力的支持。邓小平支持“实践”派、反对“凡是”派的根本意义是,打破了“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个人崇拜的禁锢,为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也就为进行改革开放拆除了思想藩篱。
于此同时,邓小平又支持经济理论界突破了把按劳分配视为“资产阶级法权”的禁区,通过深入讨论,明确肯定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毛泽东对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加上“四人帮”的恶意鼓噪,在实践和理论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导致在经济方面推行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政策,在政治方面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根据。澄清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认识,是从实践和理论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邓小平讲过,他在1977年复出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在广州、成都、东北三省点了三把火。这三把火都是针对“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点燃的,其核心内容:一是提出要清理、调整农村、城市政策,中央和地方都要清理、调整,要统一考虑,地方不要等中央。他尖锐地批评了广东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怪现象。二是提出要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鲜明地指出:当今最打紧的是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如果思想意识还这样禁锢,“两个凡是”没有得到彻底清算,那么政治路线、立国方针就无法端正,组织路线问题、培养合格的接班人问题就成了水上的浮萍,落不到实处。三是提出要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他不无愧疚地说:我们要想一想,解放这么多年,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他又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在当时的中国,只有邓小平才能讲出这样切中时弊的话。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针对深圳的“偷渡逃港”高潮,不同意“左”的观点和作法,即不同意其原因是“政治性的”,处理方法采用政治性和军事性手段,而明确指出:“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可以解决逃港问题”[4](P23)。邓小平又针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高潮,指出“真正解决下乡知识青年问题,归根结底是城市工业发展”[4](P261)。后来的实际情况就是循着这个思路解决的。
特别富有意义的是,邓小平提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表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肯定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要解放思想,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就为后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准备了思想基础。
(三)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折而载入史册。在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迫于会内会外的巨大压力,终于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而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讲话,回答了在历史转折关头党面临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纠正“文化大革命”时期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开辟新时期,探索新道路,创建新理论的宣言书,实际上成为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全会公报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质上是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至此,华国锋在思想理论上维护的“两个凡是”,在实际行动上阻挠、拖延的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都被突破了。但全会没有从整体上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自此,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全党开展了全面的拨乱反正。
全面拨乱反正,在思想理论领域,主要表现为否定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邓小平指出,实践已经证明这个理论是错误的;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通过解决比例失调问题,重新端正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在政治领域,主要表现为大规模地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之前的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邓小平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是根据国内外、党内外的形势变化而决定的。在中央工作会议进行中的12月1日,他指出,“对‘文化大革命’问题,现在也要回避”,“清华大学几个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恩来)民必反,反毛(泽东)国必乱’,这个话水平很高”[4](P445)。转过年来的3月16日,他又指出,“像评价‘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问题,可以暂时放下”[4](P493)。不久,邓小平认为国际国内的人们“都在等”,“应该拿出一个东西来”,澄清人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
1979年是新中国成立30周年,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庆祝大会上作重要讲话。显然,这个讲话必须对建国30年的历史作出总结,这就必然要涉及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评价。邓小平对这个讲话要求很高,在起草过程中曾三次谈了意见。作为中央文件,这个讲话是第一次从整体上明确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叶剑英在讲话中宣布了党准备对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问题作出一个正式的结论。
1979年11月,在邓小平、胡耀邦的指导下,中央开始进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到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审议通过。这个《决议》,倾注了邓小平大量心血,据有的专家统计,仅指导起草的讲话就多达28次。《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定义其性质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1](P811)。这一个“是”和一个“不是”,表明了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科学的、彻底的、根本的否定。《决议》的一个杰作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1](P809)这足以体现了邓小平等高度的政治智慧。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决议》,用了近五年的时间,中共中央终于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这其中,邓小平功居之首。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个否定过程不可能如此顺利,这个否定时间不可能如此短暂,这个否定结论不可能如此科学。
(四)
邓小平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沉迷于难以抹掉的个人恩怨之中,而是为了从民族惨痛的创伤之中分清是非、汲取教训,更好地带领人民前行。往后看,是为了向前走。结束过去,是为了开辟未来。邓小平讲得好,“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3](P272)。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制定了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政策,邓小平将这些政策概括为改革开放。自此,中国人民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就是针对着在“文化大革命”中日益强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进行的。
在中国广大农村,从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体制到1978年,全国尚有2.5亿多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由此可知农村贫困落后之状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随着思想禁锢的松动,安徽出现了包产、包干到户,四川和云南出现了包产到组,广东搞起了“五定一奖”。但是,农民的这些改革举措无不受到来自“左”的方面的压力。1979年当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向邓小平反映时,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不要争论,你就这样干下去。”[4](P531)1980年4月2日,邓小平明确地表示:“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4](P616)不久后的5月31日,邓小平强有力地肯定了安徽的包产、包干到户。邓小平的坚决支持,使农村改革似春潮般地涌动起来。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1号文件称包产、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从而使这一体制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包产、包干到户后来被概括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人民公社体制的对立物。尽管中央文件没有公开否定人民公社,但是人民公社还是日趋解体,到1985年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是自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尝蟹者是四川,之后陆续扩大到其它地区。一些扩权试点企业在实践中尝试实行生产责任制,以解决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之间的责、权、利关系。而在这个过程中,不少企业采用了承包制。这一系列改革措施,有效地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但也暴露出一些需要深化改革才能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流通体制改革开始了,金融体系的改革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也开始了。
创办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个大手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广东省委酝酿在深圳、珠海、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他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4](P510)经过一系列的论证、筹备,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在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设置,不仅打开了中国吸引外资的局面,而且也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外向型经济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在城市经济体制初始改革中,单一公有制的格局发生变化是一件引人关注的大事情。促使这一变化的动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对外开放方针、经济特区的建立,使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的企业陆续落脚。二是为了安置“文化大革命”后大量返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府扶持兴办自筹资金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个体经济。于是,单一公有制经济形式变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更为引人关注的是,这些非公有制经济实体主要是依靠市场生存和发展。这样一来,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变动了,市场经济也来了。
邓小平在启动经济体制改革之时,就在思索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什么?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不是资本主义?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不能说是资本主义。”[4](P580-581)邓小平这个讲话,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最早突破传统观念、将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的论述。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观念在较长时间内没能在决策层达成共识。
政治体制改革,一开始就是针对着在“文化大革命”中日益强化的党和国家人治体制的弊端进行的。
在中国,作为长期执政的中共,党的体制和国家的体制的改革具有同样的意义。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鉴于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一再强调保障民主、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1980年8月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这个重要讲话实际上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在此前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这主要是:中共中央设立书记处,以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确立党内法规;修改党章,增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规定;从国家领导机构着手,以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须知道,政治体制改革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启动的。
邓小平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是,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艰难困苦;目的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邓小平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是,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削弱;目的是,实行民主,加强法制。在启动经济体制改革中,邓小平得出的结论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在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中,邓小平得出的结论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涉及一个重大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此时邓小平眼中的社会主义起码应具备这样几个特征,即生产力水平较高,人们生活共同富裕,人民享有民主,社会实行法制。紧接着就涉及另一个重大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此时邓小平脑中思索的是摆脱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他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迭,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4](P376-378)。他的结论是,“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2](P265)。
于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上庄严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指导思想的提出,就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树立起一面鲜明的旗帜。自此,中国人民在这一旗帜的指引下奋力前行。
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一历史进程表明:中国走出“文革”困局、汇入人类文明大道,是历史的必然;而由邓小平担当起并完成了这一重任,则是历史的偶然。思考这一历史进程中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对于执政者把握历史主动性大有裨益。
[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毛泽东年谱(第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3]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邓小平年谱(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泰山学院学报的其它文章
- 泰山神庙剧场概述
- 清代山东、日本港口贸易及泰山诗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