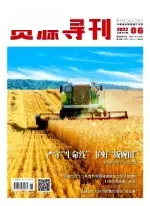难忘家乡玉米花
□崔世俊
家乡的玉米花,既没有超市里那样华丽的外表,也不如爆花机里加工出来的大小一致。但这种玉米花令我难舍难忘、情有独钟。
我的家乡在栾川县三川镇。由于这里由三条沟川组成而取名为三川。三川镇海拔1240 米,因为昼夜温差大,主要农作物只有玉米、土豆,还有少量大豆,且一年一熟,所以,用这里的玉米加工后的玉米糁不仅远近闻名,而且,爆炒出来的玉米花更是堪称一绝。
过去的三川,因为人多地少,每年出产的玉米仅供人们食用六七个月,所以在那个年代想饱餐一顿玉米花也是一种奢侈。但是,对于家庭比较富裕的人家来说,十天半月的炒一次玉米花还是不足为奇的。我的父亲是个木匠,因为怕割资本主义尾巴,他常常夜里点起煤油灯,搞“地下”加工,做几样小家具,赚几个小钱,即便是全家人吃不饱饭,但我家在几个村子里也算得上是上等户。从我记事起,奶奶、母亲就经常为我炒玉米花。特别是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十几年读书生涯中,几乎每个星期都能吃上玉米花。可是,我家偶尔也有揭不开锅的时候。有一年的夏天,家里仅有一升的玉米,可天公偏不作美,没完没了地下雨,大人们无法到外面的石磨上加工仅有的玉米。奶奶看到我饿得大哭大叫,便专门为我炒了一口袋玉米花。那些年,人们为了节省粮食,每到寒冬时就把一日三餐改成了一日两餐。一日两餐不知道节省了多少粮食?但我只知道过了中午时分,村里的大人们个个是饥肠辘辘,他们的那种饥饿之苦难以言表。一部分家长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挨饿,宁愿自己勒紧裤腰带,也要炒些玉米花让孩子们充当午饭。“可怜天下父母心”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到了高中后,学校经常搞勤工俭学,我所带的干粮还是玉米花。到了假期,我无论是下井下挑石煤还是上山采中药,口袋里的干粮都是玉米花。
三川人炒玉米花用的是平时做饭用的铁锅,这锅中炒时还必须放入沙子。这沙子并非从河滩而获,而是从当地的山上采下来的。也许是大自然的垂青与眷顾,附近的山坡上有白、灰两种石块,只要把采下来的石块用锤子轻轻一击,它立刻散成一堆砂子,两种砂子的颗粒均匀度如砂糖那般。灰色的砂子银光闪闪,白色的砂子雪里透亮。每次炒玉米时,先将适量沙子入锅,待沙子达到一定温度时,再把金黄色的玉米放入锅内,用玉米芯顺时针翻搅。几分钟过后,那些玉米会在热锅里争先恐后地“呯、叭”作响,香气迎面而来。有时也会在玉米有七八成熟时,放入一些大豆,待大豆完全开裂后,将锅内的玉米花、大豆和砂子一起倒入事先准备好的竹篮内,这时,只要轻轻提晃几下竹篮,那些砂子便从篮缝中哗啦啦地溜下,剩下的就是玉米花和香喷喷的大豆,即使在三五米外也能闻到它们的香味。慢慢嚼上一粒玉米花,那味道香脆可口,美味极了!
说来也怪,也不知是哪辈老祖宗定下的规距,人们把每年的农历十一月三十日称为炒豆节。如果这个月没有三十,他们就把二十九作为炒豆节。说是炒豆节,其实还是炒玉米花,只不过在炒玉米花中添加了一部分大豆而已。
炒豆节那天下午,大人们从玉米棒上剥下成筐金黄色的玉米粒,孩子们则几天前就三五成群地从山上采来了沙子。傍晚时分,家家户户不约而同地起大铁锅,又不谋而合地围在锅台旁,在欢声笑语中炒着玉米花。顿时村子里灯火辉煌,空气中弥漫着玉米花特有的香气,呯呯叭叭的响声不亚于除夕夜,这里的每一个村落都沸腾了。那热闹、喜庆的气氛让在饥饿中的人们真正地饱餐了一顿玉米花,或多或少带走他们终年的惆怅,期望来年的五谷丰登。
有了炒豆节,自然有了“三十炒,初一咬”的顺口溜。炒豆节后的第二天,大人会把一些玉米花送给远方的亲戚、朋友。孩子们就把口袋装得鼓鼓的,或与小伙伴交换,或送给老师们品尝,用玉米花传递着亲情和友情。有些家里干脆把玉米花磨成炒面,然后将炒面和软柿子一起搅拌,其味道更是甜中带香、香中有甜,令人不厌其食,回味无穷。
玉米花虽然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在那个年代,它不知帮多少农家子弟完成了学业,支撑着生命,让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传宗接代。记得我20 岁参加工作时,每月只有29 斤供应粮,正值年轻力壮的我实在是填不饱肚子,正是那一袋袋玉米花帮我度过了最坚苦的日子。因此,母亲一有机会,就会从乡下给我捎一大袋玉米花。
党的三中全会后,三川人虽然生活如芝麻开花,但炒玉米花一直是当地的一道美味食品,炒豆节在这里一代代传承、延续。尤其是三川柳树坑村的几十名农民,他们把炒玉米花做成了产业,无论春夏秋冬,他们总是提着一个个大竹篮穿梭在山城里的每一个巷道,让三川的玉米花不仅成为栾川人的一道美味食品,同时,也让这里的玉米花走向了四面八方。
直到现在,每次到大街上看到玉米花时我就会买上一大袋,放到车内,有时忙得来不及吃饭时,就拿它来充饥。
玉米花,它滋养着我的生命,帮我完成学业,给我了信心和勇气、坚强和力量,伴我走过了人生的大半个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