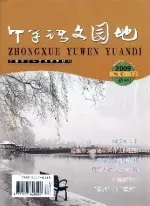“窃书不能算偷”的逻辑学问
陈 江
孔乙己到咸享酒店喝酒被人嘲笑偷了人家的书,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其实孔乙己的这句话里是有学问的,短衣帮没读过书,不懂,引来一阵哄笑。“窃书不为偷”与战国时赵国人公孙龙《公孙龙子》中“白马非马”具有相似点。
据说,公孙龙有一次骑马过关,关吏说:“马不准过。”他回答说:“我骑的是白马,白马非马。”说着就连马一起过去了。
公孙龙的“白马”有没有过关,我们不得而知。从常人的观点来看,守关的兵士八成认为公孙龙是在诡辩。这也是一个逻辑上的“莫能与辩”,现实中不能成立的例子。
哲学家冯友兰从“共相学”角度,对《公孙龙子》里的《白马论》中的“白马非马”进行了三点论证:
一是强调“马”、“白”、“白马”的内涵不同。“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白”的内涵是一种颜色,“白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加一种颜色。三者内涵各不相同,所以白马非马。
二是强调“马”、“白马”的外延的不同。“马”的外延包括一切马,不管其颜色的区别;“白马”的外延只包括白马,有颜色区别。外延不同,所以白马非马。
三是强调“马”这个共相与“白马”这个共相的不同。马的共相,是一切马的本质属性,它不包含颜色,仅只是“马作为马”。共性不同,“马作为马”与“白马作为白马”不同。所以白马非马。①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白马非马”割断了个别和一般的关系。白马属于个别,特指白颜色的马;马属于一般,具有各种颜色马的共性。公孙龙区分了它们之间的差别,但是又绝对化了这种差别。白马尽管颜色上不同于其他的马,如公孙龙提到的黄马、黑马,但仍然是马。作为共性的“马”寓于作为个性的“白马”之中。“马”作为一般的范畴,包括各种颜色的马,公孙龙的白马自然也不例外。
墨辩中有句“杀盗非杀人也”的话,这个命题与“白马非马”极其相似,尽管论证的方法和目的不同。
孔乙己“窃书不能算偷”的观点,可以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解释:
如果“读书人”私下拿书,那么称“窃”书不叫“偷”。我是“读书人”,私下拿了书,所以“窃书不能算偷”。
再简单点:读书人私下拿书叫“窃”书不叫“偷”。我是“读书人”,所以“窃书不能算偷”。
孔乙己这句话隐含着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学”思维,短衣帮没读过书,肯定是听不懂的,当然要笑他迂腐了。
为什么古代读书人私下拿书应叫“窃”书不叫“偷”呢?夏宝祥在《也谈“窃书不能算偷”》一文中已经谈过了,此处不赘述。
今天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读书人”“窃”书与“小偷”“偷”书,在行为性质上是一样的。“窃”、“偷”只是称呼不同;在听觉上一个文雅,一个难听;在主体上一个针对文人说的,一个是针对寻常百姓说的;近代在词义上,都是偷盗的意思。
中国古代这种名辩逻辑,在先秦时期被其他派别称为诡辩,在今天的哲学上称为悖论。庄子说:“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荀子》也认为:“虽辩,君子不听。”
诡辩就是胡言乱语吗?黑格尔在《小逻辑》里说:“一说到诡辩我们总以为这只是一种歪曲正义和真理,从一种谬妄的观点去表述事物的思想方式。但这并不是诡辩的直接的倾向。诡辩派原来的观点不是别的,只是一种‘合理化论辩’的观点。”②看出黑格尔对其中隐含的学问是加以肯定的。
而后来的辩证法就是在对付诡辩论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注释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黑格尔:《小逻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