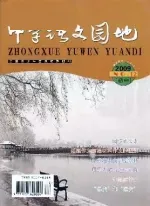披情入山林,且行且吟话凄凉——《始得西山宴游记》主旨之我见
柳 青
[作者通联:江苏常熟市中学]
江苏教育出版社《语文必修一·教学参考书》中,对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一文的主旨分析为“作者感到超脱而旷达,忘却了自我,也忘却了烦忧,获得了精神的慰藉”。对此,我深有疑问。本文想从柳宗元的人生理想以及他被贬永州之后的生活经历为切入点,谈《始得西山宴游记》的另一种解读思路。
柳氏家族,当年在河东,可谓显赫至极。只是到柳宗元曾祖父之辈,已经衰落,已无一人在朝为官。
永州之地,是幸福的,因为柳宗元而千古闻名。而永州对于柳宗元,却是他生命中无法拔除的一个尖刺。贬谪于永州,仅仅半年,让他备尝亡母之痛,倍感人生凄苦。居此十年,柳宗元失去了他重登政治舞台的际遇。永州,是柳宗元心中无法回避的伤痛之地。
一、宴游之中含落寞
司马,是一个如此尴尬的职位。由朝中大员贬为地方司马,当地官员既不敢得罪,怕有朝一日会重新召回任职;又不敢亲近,怕因此得罪朝廷某位要员而影响自己的仕途。被贬司马之人,是孤独的,也是落寞的。被贬司马,是柳宗元心中十年难消的块垒。
柳宗元,20岁中进士,31岁入朝为官,47岁病逝异乡,潦倒终身。其间14年流放生涯。背负着振兴家族的使命,却最终令老母因他而过早仙逝,令亲友因他而颠沛流离,令自己一腔抱负无以施展。永州,是柳宗元的伤心地,十年辛酸十年凄凉十年沦落,化为他诗词歌赋的深重内涵,造就了他文章的宽度与厚度,也造就了一代文章大家。他的那些流传后世的文章,几乎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由永州到柳州,再也没有踏上回乡之路,更不必说回归朝廷回归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再也没有机会为自己的政治革新讨一个说法,再也没有机会为自己14年的辛酸做一个交代。我想,先生离开人世时,一定是带着深沉的遗憾与满腹的愁怨吧,一定是带着满心的不甘与难言的委屈吧,一定是带着无尽的对家乡的思念对亲友的愧疚吧。
所以,我读《始得西山宴游记》,看不出先生宴游山水的快意,看不出先生悠游山林的惬意,也看不出始得西山之游的惊喜。那个清醒的革新家,无法选择自己的生存空间。母亲的病逝,家人的举步维艰,自己政治生命的无望,随便哪一点,都足以令他忧心如焚,忧惧难安。
二、始知西山为相知
这个孤寂的文人,自己的生活状态都无法选择,重振朝纲经天纬地的理想只能是空谈。苦寒之地,遭贬之人,有谁理会他的思想、在乎他的处境、在意他的心境。永州六个月,每一天都是那么漫长,每一天他都转辗反
三、纵情山水话凄凉
“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真的从此寄情山水了吗?真的从此视西山为心灵的皈依了吗?真的可以忘怀吗?西山之山水与永州别处之山水真的差别巨大吗?西山之山水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化外之境了吗?
看似闲暇的生活,其中滋味何人能解?看似悠游的寻访山水,其中的郁闷何人能体味?或许只有在登高山之中,才可消解满腹的愁怨。或许只有在穷深林之时,才可忘却凄凉的处境。或许只有在溪水之畔,才可洗涤尘世的烦恼。或许只有在怪石丛中,才可得片刻的安宁。或许只有借助醉酒,才可一晌无忧。或许只有借助梦境,才可达成愿望。
此时,柳宗元还只是初到永州,心中的那份期待依旧在,心中的那份牵挂依旧在。所以,似乎可以做到暂时的忘忧,似乎也可以故作轻松地说一些自我宽慰之语。只是,在说宴游之时,是那么的勉强,在说始得之时,是那么的伤怀。在纵情山水之时,是那么的不自在。在寄情诗酒之时,是那么的凄凉。游西山之前,不愿归去,是怕面对妻小,怕面对亲友。游西山之后,依旧不愿归,是怕好梦惊醒,是怕幻想破灭,是怕好不容易的沉醉过早清醒吧?
寄情西山,以为找到了消解自己愁苦的通道,其实,此处山水与别处山水有何异?只是先生希望有差别,是先生心内所想心内所愿而已。所谓始得,所谓宴游,所谓西山胜景异于别处,只是一时宽慰之词一时心情之语一时忘情之言而已吧?
所以,《始得西山宴游记》,是无处话凄凉的伤痛之作,是柳宗元与山林的一次心灵对话。许多人从“始得”之中读出偶遇西山的惊喜,从“游于是乎始”中聊以忘忧的安慰,从“与万化冥合”中读出物我相融的惬意。其实,这只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一种误读。只有真正做到知人论文才能做出恰当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