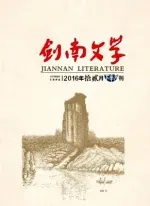柳三喜的女人(小说)
海子湾村柳家岘上组的人在与时代的同步中,争先恐后地走上了致富之路,前不久那条横穿上组村庄而过的大路的开通,彻底让“上组”的人把攒下的一沓沓钞票应用在了实际需求中,买三轮车、打麦机、割麦机、铡草机……家里面的“机”比实际的人还多。如今烙馍馍、蒸馒头这些事,女人们也不再爬到锅灶上去料理了。如今有了带电的自动烙馍馍的机——电饼铛。只要通上电,一会儿功夫就能烙一大堆热喷喷的馍馍出来。
农村女人是一个会“忘恩负义”的群体,终是禁不住改革开放这浪潮带来的巨大诱惑,硬是千方百计从“掌柜的”那儿“骗”来了血汗钱,像城里人一样也买了一台洗衣机,只要一通电,所有过程都是全自动的。真真方便得不得了!有了洗衣机,女人们的腰杆就直了起来。看到谁家的女人在水窖旁揉搓着衣服,还不忘发发慈悲说:
“你犯得这是什么毛病?脏衣服攒多了你就抱下来放到洗衣机里面,两下子就给你洗干净了,你在这儿搓来搓去的以为自己劲儿多得很!”
这也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客套话而已。买了洗衣机的女人们常常精打细算,生怕一通上电那自家的电表就像狼来了一样转个飞快,洗一次衣服,总得比别人多交好几度电费钱。洗衣服的时候觉得很是方便,可等到了交电费的时候总是忸怩在电工面前,唠叨个没完:
“咋就那么多了,这个月也没怎么用电嘛!你是不是多抄了几度?”
有的农村女人更是与国际化接上了轨,家里面不但有了各样的“机”,如今连自己的身上也要“改革开放”了。柳家岘上下两个组中最先从自身开始改革开放的女人就要算“上组”开班车的柳三喜的女人了。
柳三喜是海子湾村第一个响当当的富人,凭借其老爸是原供销社退休干部、老妈是原海子湾小学退休教师这两个便利的条件,柳三喜硬是把日子过到人前头去了。先是买了一辆摩托车,接着买了一辆务农的三轮车,没过多久,那小子揣着他老爸老妈的退休工资买了一辆25个座位的“少林”牌客车。接车那天,据说光鞭炮就放了几百块钱的,乖乖的,这架势哪个庄稼人敢比?再者柳三喜这人门道多,硬是把海子湾村通往县城的这段路给“垄断”了。说白点,就是只有柳三喜的“少林”才配跑县城,其他人要是想偷偷拉几个人,挣点小钱什么的,简直没门。据说只要柳三喜一个电话,县城里那些戴大檐帽的人就专门在半路上等着了,只要你的车一出现,管保跟“黑”沾上边了,几个罚单下来……哼哼,不把你整死在县城他柳三喜就他妈不叫柳三喜了。
柳三喜的女人家里面忙碌的时候,就留在家里干些家务,营务一下地里的庄稼,这庄稼不是胡麻就是油菜籽,不是油菜籽就是胡麻,因为每年腊月柳三喜都要拉上几桶油去孝敬城里面戴大檐帽的人。据说只要这些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柳三喜25个座位的“少林”总要多拉几倍的人,要是遇上那些戴大檐帽的人在半路上执勤,总会提前给柳三喜报个信,柳三喜会把多拉的五六十人卸在半路上,再一车一车在交警眼皮子底下转运……柳三喜的女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屁颠屁颠跟在班车上“卖票”。柳三喜车上喊卖票也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已。哪有票给你卖?说是卖票也不过是叫你从口袋里掏钱。
话说柳三喜的女人在班车上卖票,毕竟这班车是开往县城的,那就意味着这车是从一个世界开往另一个世界的。三喜女人跟班车进城没几次,脚上也蹬上了半高不高的高跟鞋。穿这种鞋在城里的水泥路上走“咯噔咯噔”的有几分女人的韵味,可在农村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行走,不但“咯噔”不起来,而且连女人走路的姿势都变了,变得像只鸵鸟一样,屁股高高的翘着,腰杆勾搭下去,哪还有一点女人的味道?因此三喜女人穿的这高跟鞋没有被其他女人所接受,倒是她脖子上系着的那根花格子丝巾很快流行在了农村世界里。
在脖项里系一根丝巾显然不是保暖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女人的脖项系上这玩意倒还别致,值得看两眼。据在外面厮混过的人说,县城的各大管钱的地方,每个女服务员的脖项里也系着这玩意——这倒让没混上对象的光棍们,没什么事就往管钱的地方跑,往那软绵绵的皮椅上一坐,呆呆地看着漂亮的女服务员,然后理直气壮地“咨询”一些信息。还有人说,飞机上的女服务员统统叫什么“空姐”的脖项里也系着这玩意儿。丝巾的结头斜在肩膀处,回转过头来,给你一个甜甜的微笑……妈的,简直让人的心都碎了,咋鸡巴就那么顺看呢?不得了,城里的女人怎么看都顺眼。
三喜女人除了蹬高跟鞋,系丝巾外,还穿城里人的那种紧身衣服,往腿上一裹,腰带也不需系,把个屁股裹得滚圆滚圆的,大腿小腿,什么都若隐若现。走起路来一拧三扭,再配上高跟鞋,韵味到家了;除此以外,三喜女人还穿低领的短衫。衫子胸前缀着一些在太阳底下能放出射目的光的红的绿的东西。衫子薄而轻柔,像小蜻蜓的翅一样,只需轻轻一扫,女人身上的几根物件就一览无余,比扒光了衣服看还有几分情趣。倒是这般隐隐约约的瞅上几眼,更让人浮想联翩,睡觉的时候都仿佛有这么一个女人在眼前一晃一晃的,双手一抓,鸡巴,连个蚊子都没抓着……
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就比如像雷锋一样,他的精神整整影响了一代人,到如今海子湾小学上早操的时候还在唱 《学习雷锋好榜样》了。同样,三喜女人的这个“榜样”,其作用也是无穷大的,大到足以让一个农村的女人精打细算,锱铢必较,攒上一点私房钱来,在集市上就大大方方的消费掉了,买紧身衣、蝉翼短衫、花格子丝巾、牛仔裤……只要是三喜女人身上有的,其他女人也不甘落后,哪怕一年不上集市,上一次集市总要买一件能和三喜女人身上的相抗衡的时尚东西来。当然三喜女人不但穿着时尚,还讲究牌子,农村女人就不管这么多了,管你妈叫什么名儿了,老娘能穿上身就行了,你再拧扭的美,咱们的样式一个样的……
最近,三喜女人的身上又注入了新时尚的营养元素,先前,三喜女人把头发染了,比以前更亮丽了。不知道怎么弄的,头发比以前直了,披散在肩上,再也不用头绳扎了——据她说城里人都是这个样子。农村的女人也有效仿的,可一效仿才发现,一点都不美气,吃饭的时候头发“呼啦”一下就掉在碗里了,干活的时候不时把眼睛遮住了……妈的!城里人也太没事找事了,把头发扎起来多好,偏偏披在肩上,像个披头散发的妖怪一样,一点都不雅观。
可是没几天,三喜女人的发型又变了,头发还披在肩上,但比以前黄了些,发尖上整体都成了淡黄色,而且有点微微卷曲,像根被拉到最大限度的弹簧。据三喜女人本人发言,这叫烫,先前的叫染,两者不一样,就比如同样是建筑队的人,有的是木工,有的是瓦工,有的是抹灰工……这个比方足以让农村女人们理解这染和烫的区别,有的女人当场就说:
“这个我知道,我男人就是木工嘛,在建筑队上专门支楼梯哩。”
三喜女人还说了,这烫还分若干种,她的这还算是比较平常的一种,叫离子烫,总花下来才两百四十块钱。三喜女人话还没说完,有女人当场就尖叫了一声:
“我的妈呀!把个死驴的毬咋就这么高哩?两百多你也舍得去烫。”
“哎呀!现在什么东西都贵嘛,在城里面,去理发店只搞个洗、剪、吹下来就好几十,更何况这是烫嘛!还得用药水哩!”三喜女人见怪不怪地给其他女人解释着。她尽量着心平气和,不但要让别人知道她是见多识广,而且还要表现出自己对这种消费已经司空见惯了……
三喜女人的话打击了很多女人的积极性,好些人不敢再提这染和烫了,有的女人索性自我安慰说:
“把个死驴的毬烫成黄色的以为好看得很!我要有两百多块钱去买吃的了,还去烫他妈的这个皮。”
骂归骂,羡慕归羡慕。三喜女人的着装打扮一点也不丢司机柳三喜的人。反过来,柳三喜女人还给三喜长了精神,给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精神动力。在班车上卖票的时候,鸡巴乘客们都喜好与三喜女人说笑话,只要三喜的女人往后车厢挤过来,娇声娇气地喊一声:
“大家买票啦!”有人就立马取笑说:
“娃他三嫂子,给当叔的少两个嘛!你看当叔的身上都没带钱。”
“看你说的,当叔的不给当媳妇的多掏几个,你还好意思发言。”
“哈哈哈。”一车人都大笑起来。
“赶紧的,取笑了媳妇还不掏一张红公鸡出来,你能说得过去吗你?”
三喜女人比大男人们会说得多,用手把额前的烫发往后肩一扬,硬是把个大男人说的哑口无言,乖乖的给娃他三嫂子把“票”买……
久而久之,人们习惯了三喜女人一天比一天娇羞的身材,也习惯了柳三喜家一天比一天富有。对于庄稼人来说,“人的命,天注定”,各人有各人的命,这是上辈子老天爷就注定好了的,谁让人家柳三喜家有两个吃皇粮的人呢?据说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叫“轮回”,谁人也走不出来,而庄稼人最大的习惯就是从来都不会去思考怎么样走出这个“轮回”,他们只会在歆羡与知足中“轮回”着……
(西南科技大学东四A-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