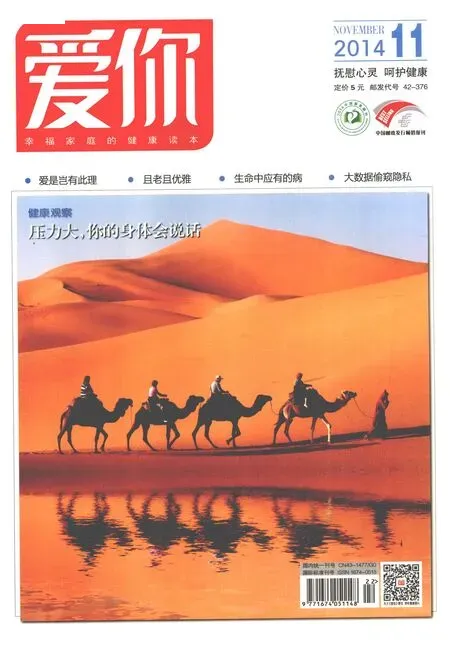红脸小姑
◎ 肖复兴
红脸小姑
◎ 肖复兴

那时候,我们都管她叫红脸小姑。
20 世纪 50 年代,在前门外的粤东会馆大院里,红脸小姑带着她的儿子搬进来的时候,我有些害怕她,因为有一大块“像有人把葡萄汁或颜料甩上去的”紫红色的痣,占据了她左侧大半的脸。
那时候,我很小,那张脸真的很吓人。背地里,我们小孩子都管她叫红脸小姑。之所以管她叫小姑,是因为她是从太原老家来北京,主要是为儿子能在北京上学。
她的嫂子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里当老师,帮助孩子找所学校方便些。她的哥嫂有一个女儿,比我小三岁,管她叫小姑,我们也就跟着叫了起来。
她的儿子比我大两岁,常和我们疯玩在一起,却和他的表妹不怎么玩得来。那时候,我们年龄还太小,不明白其实这是红脸小姑和她嫂子故意为之。她们两人都不愿意两个孩子走得太近,红脸小姑甚至不愿意她的儿子总到嫂子家去串门,虽然她们两家住的很近,只有一房之隔。
那时候,红脸小姑的母亲还在,住在她和嫂子中间的那间房子里。
后来,我常常到红脸小姑家里找她的儿子玩,和她熟了之后,发现她并不可怕。细细端详,除了脸上那块红痣外,她其实挺好看的,个子很高,身材也很好。她爱穿旗袍,特别凸显秀气的身条,特别是坐在她屋前的走廊里喝茶,侧影,逆光,只看到她右侧的脸,背景有窗台上花草扶疏影子的映衬,真的很美,比她的嫂子要漂亮多了。
她不怎么爱说话,每天上班去,下班回,除了到她母亲的屋里吃饭,哪儿也不去,和哥哥嫂子也很少交流。
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只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她的丈夫哪儿去了。曾经有好事的街坊四处打听,也不着边际,问到她母亲,她母亲只说一句离婚了,便难再撬开一点儿缝。
也有好心的街坊给她介绍对象,她只是笑笑。街坊一再劝说别担心那块痣,她就连连摆手。
下班或星期天休息,她不是督促儿子学习,就是坐在走廊前喝茶。她家廊前是一个挺幽静的小院,种有三棵前清时的老枣树。黄昏的时候,晚霞洒满庭院,映得枣树一片火红,也映得她的脸膛火红火红的。没有痣的那一侧,也和有痣一样燃烧了起来。
那是我们大院里的一幅画,定格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颇有点前朝美人的意味。
她的儿子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上了一所中专技校。三年之后毕业,她带着儿子离开北京,回太原去了,因为她在太原钢厂为儿子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和她儿子告别的时候,我们大院的孩子都有些恋恋不舍。青春期的友情常常容易膨胀,浓烈如酒,远胜过红脸小姑和她哥哥嫂子一家的告别。
两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大人们的很多秘密被无情揭开。
大院池浅王八多,庙小神灵大,我们才知道红脸小姑的哥哥其实并不是她的哥哥,她的嫂子才是她的亲姐姐。姐姐未婚先孕,产下这个男孩子,就跑到了北京。为了保护姐姐,成全姐姐以后的婚姻,她把姐姐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亲儿子养大成人,牺牲了自己的青春。
文革中,红脸小姑的姐姐被抄家,她的学生成为那个时代的红卫兵,毫不留情地批斗了她,那时,“私生子事件”足以要她的命。最终,她的学生在她的脸上还是刻印下了红字。当时,我暗想,幸亏她儿子早两年离开了北京,如果目睹这一切,该怎么面对?
(摘自《黑龙江日报》 图/亓寂)
——以柏林Kreuzberg 地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