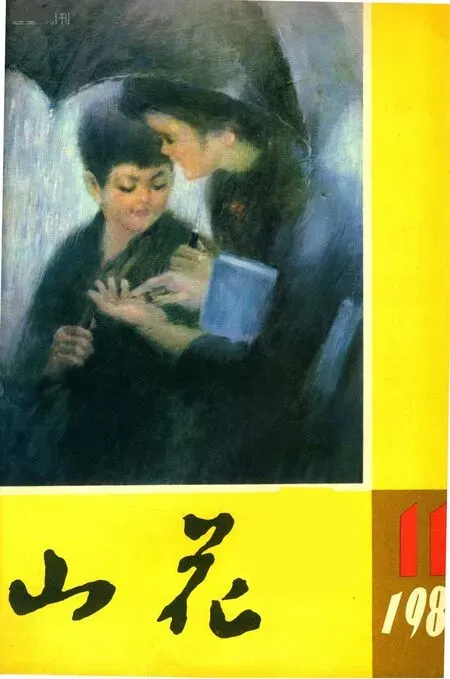海棠之夜
孙频
一
月亮有些残了,挂在一截喑哑的海棠树枝上。
李心藤慢慢在公园里的海棠林中穿行。海棠花香很淡,不到跟前是闻不到的,所以背上肩上一旦被粉簇簇的海棠花拂到了,总有猝不及防的感觉,好像冷不防有只手放在了自己身上。回头一看却空无一人,只是身上沾了一缕阴柔的冷香,花魂似的。
海棠林芯子里飘着一缕音乐,音符在黑暗中像坚硬的金属一样往下沉,愈发衬得那些海棠花云彩似地往上浮。沉浮之间却总能感觉到这夜晚的骨头正阴凉地卡在每一个角落里,就是那无处不在的月光。越往林子深处走音乐便愈发清晰了,像一个模糊的梦渐渐长出了手脚,渐渐能看到它的脸了。林子深处是一片用木板铺起来的圆形空地,有一男一女正在那里跳舞。一台黑色的老式音箱沉郁地蹲在地上,音乐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有十来个看不清脸的男男女女正或坐或站地在旁边围观。李心藤在一张花丛隐掩的长椅上坐了下来,看着那正在起舞的一男一女。
空地边上站着一盏孤零零的路灯,瘦长的灯光透过稀稀朗朗的海棠叶筛落在两个人身上。一曲刚罢,女人站在原地做中场休息。她已经不年轻了,昂着头,高高拎着两只胸器不肯放下,身上搭起的还是刚才舞蹈的架子,明晃晃的,全身上下连道缝都没有松懈。她正用眼角的余光清点所剩的观众。李心藤知道,只要还有一个观众她便能像陀螺一样跳下去。她的男舞伴穿着黑紧身裤白衬衫,谢顶的头发用发蜡塑起来一根根地铺在脑袋上。音乐又响起来了,是肖斯塔科维奇的《抒情圆舞曲》,女人的紫色丝绒大长裙一摆,端起手来搭在了男人的肩上,两人跳起了华尔兹。微风过处,一棵高大的海棠树花瓣簌簌,雪一样落在了这对男女身上。李心藤远远看着他们忽然觉得他们就像他小时候见过的装在一只玻璃球里的一对小瓷人。他只能捧在手里看他们。
旋转的舞步越来越快,像珠子一样缀成了一串,流光溢彩。然而夜色已晚,观众们开始陆陆续续撤退回家,最后只剩了一个胖胖的老女人还在原地看着他们。舞步孤独地进入高潮,女人旋转的长裙嚣张华丽地把这对男女裹了进去,他们简直要渐渐隐匿了消失了,在音乐中飞舞的只剩了这条紫色的孤独的长裙。李心藤不忍心往下看了,他垂下了头,看着自己的手指。他无数次想去学跳舞,最后却只是躲在一边窥视着跳舞的人们。看着男人把手放在女人腰上的时候他会浑身哆嗦,似乎那只手是他自己的。等他再抬起头的时候,连那个老女人也不见了,而两个跳舞的人已经几乎要飞起来了,他们似乎要像嫦娥一样向着月亮飞过去。这时,音乐戛然而止。两个人猝然停住,影子散落了一地。他不敢看他们的脸,他只看着他们落在地上的影子,孤单,狰狞,虚弱,却随时准备要再次飞起来。
又一阵风吹过,海棠花落在女人的头发上裙子上。跳舞的男人抱着音箱先走了,只剩下了女人,女人站在那里拖着裙摆偷偷地观察着四周,确定周围没有人了,她才脱下了脚上的高跟鞋,从旁边的袋子里取出一双布鞋,穿在脚上,再把皮鞋小心翼翼地放进去。然后,她走到一棵高大的海棠树后取出一辆藏在那里的破旧自行车,她再次警惕地扫视了周围一圈,然后背着高跟鞋骑上自行车走了。李心藤目送着她,他看到她骑出去一两米的时候忽然又从自行车上跳了下来,裙摆太长被绞进车轮里了。
此时圆形空地上没有一个人了,只剩下落花微独立,薄薄的月光胭脂一样晕染着它们。李心藤依旧坐在树下的长椅上,他周身沐浴在黑暗中,感觉有一点点解脱,还有一点点悲怆。估计整个公园里也没什么人了,是该回去的时候了,就在他刚刚站起来的时候,忽然发现几米之外的长椅上还坐着一个人。那人也站了起来,就着月光他看清楚了,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女,上身穿着校服,身上还背着书包。这么晚的夜里,在这海棠林深处忽然出现了一个女孩,他一阵眩晕,一时竟有些恐惧,怀疑这女孩是不是花妖所幻。女孩向他走来,但没有停步,她朝林子里走去。这时他的胳膊分明碰到她的衣服了,他浑身一震,竟有些窒息,女孩扭头对他一笑,这笑容让他又是一震。等到再回过神来,女孩已经不见了。整个月影幢幢的海棠林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于是李心藤踩着月光慢慢向自己家踱去。他家就住在公园边上,所以这公园就像是他自家的后花园,他就是在这公园里过夜也没人管他。李心藤一直没有结过婚,他总对人说不着急急什么,结果在他还没来得及结婚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退休一年了。退休之后时间多得简直让他防不胜防,怎么到处是时间,简直是无孔不入,连掐都掐不死。他每天为怎么用掉这些时间而发愁,屋子里空荡荡的像个玻璃瓶,掉根针掉下去都能听见回声。为了能摸到些人气他只好像个流浪汉一样不分白天晚上地在公园里晃荡,公园里不缺的就是人,只要是人都让他觉得亲切。
在屋里的时候,无论手里正做着什么他的耳朵都系在那部电话上,好像他唯一在做的事情就是专门等着电话响起。但电话一直很矜持,一旦真的响起来的时候他立刻扔下一切活,跳起来敏捷地向电话扑过去,因为担心接电话太快被对方笑话他便又摁住电话默默地数了一二三,才接起电话假装用不耐烦的惺忪的声音对着电话一声,喂?
电话里若是有老朋友约他吃饭,他脸上便立刻露出愚蠢的笑容,虽然他明知自己近日里的时间一览无余,没有任何安排,可以像荒地一样随意被开垦被占用,但他隔着电话还是很矜持很犹豫地说,明天晚上啊,让我看看我的时间安排……哦,明晚大约还是有时间的。他一定要用命去捍卫大约二字。
但电话毕竟不多,所以他经常得用几个星期的时间来期盼一件事情的发生,比如一个电话。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活着的全部价值就剩下等待这件事了,简直像个数着日子等圣诞节的儿童。当然,极偶然的,还有性价比更高的电话,那就是有人要给他介绍女朋友,当然他知道,介绍的也都是些满脸皱纹阴道松弛的老女朋友了。
说到相亲,他从大学毕业开始一直相到六十岁,相了整整四十年,对这件事的熟悉程度绝不亚于对自己身体上哪有个痦子的熟悉。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把一次相亲的程序摸索下来。四十年里因为对这件事情太熟悉了,反而从没有真正去正视过它,大约心里只觉得这是自己一个铁打不散的亲人,就是走丢了也能再认回来——左不过来来去去的都是些女人。可是等他年龄渐渐变老的时候,他发现就连这件事都面目狰狞起来,主要是那些芯子里的女人面目狰狞起来了——各色各样的老女人。离异的,孩子都已经结婚的,偶尔有那么两个从未结过婚的老女人他又觉得她们一定深藏着可怕的怪癖,是老处女可怕不是老处女也可怕,似乎她们随时都能拔出什么怪癖来置人于死地。
而他,他不能不珍惜自己,虽然已经退休了,他还从没有真正谈过一次恋爱。从这一点来讲,他觉得自己在本质上与少年无异,所以他总觉得把自己拱手交给一个离异的老女人是暴敛天物。
回到静静的家里还没来得及打开灯就听到电话响了,他一阵狂喜,向电话扑过去,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居然有电话打来。是老友打来电话说明天要给他介绍个女朋友。他简直大喜过望,因为从退休后便极少有人给他介绍了,好像他已经被划归到废弃物里面了,而他的时间正浩如烟海,简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相亲这样的事也算是绝好的消遣了。然而他仍然不忘拿捏片刻,片刻之后方才装作不情愿地应承下来,似乎权当是送老友一个面子了。
电话里约好了第二天中午一起吃饭,第二天早晨李心藤六点便爬了起来,起来第一件事是给珍珠熊先喂点吃的,那是他退休后养的宠物,一只黑白相间的老鼠。他虽然给它冠以一个魁梧的名字——熊熊,但它无论怎么吃也长不过一巴掌,没有变成什么骇人的巨鼠。喂完老鼠他便照例到公园里走了一圈,因为对这公园太熟了,他走在其中的时候不由得比别人要多出些底气,就像一个员外在巡视着自家的花园,而别人不过是沾他的光。巡视完毕又回到家中,一看表才八点,离十二点还遥遥无期。
尽管他一再郑重告诫自己至少要过了十一点再准备,可是他还是实在按捺不住,就像小孩子忍不住要偷吃糖一样他悄悄取出了一只鞋盒子。这双鞋是前不久刚买的,至今还没有适合的场合穿过它,每次看到它被束之高阁他都觉得义愤填膺,好在今天总算有了用武之地。他把新鞋穿在脚上对着镜子走过来走过去,看镜子里的自己是否风度翩翩,是否看起来年轻了十岁。最后为了验证这双鞋所得不虚,他又对着镜子使劲跳了几跳。至于今天赴约的衣服他昨晚就连夜准备好了,衬衣裤子已经熨好挂起来了。这套衣服不到隆重场合他是轻易不穿的,是约会专用服,平日里都是拿塑料袋套起来放在幽暗的衣柜里拿香薰着。现在他决定先试穿一下效果,看看和这双鞋配在一起是否养眼。不错,领子和裤缝都很笔挺,锋利得可以当水果刀使了。因为多年没有女人,李心藤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了雌雄同体,比如做针线活熨衣服,他都很拿手,年轻的时候他还会给自己织毛衣。
他双手插兜在镜子前走了几个回合之后基本觉得可以见人了,便款款脱下衣服再次挂起以免弄皱。最后他只穿着一双黑色的袜子看着镜子里赤身裸体的自己,镜子里站着一个皮肤松弛的老人,他不信,扑过去仔细看,全身的皮肤都已经松弛下来了,那只肚子倒是一枝独秀,简直称得上是长势葳蕤,像在身体里镶嵌了一只西瓜。他又看着自己的侧面,不仅肚子凸起,臀部也开始下垂,像两只沉甸甸的口袋。这时候他又发现自己的胳膊上腿上已经长出了很多褐色的斑点,老年斑。真是老丑。他一阵害怕,惊恐地看着那些斑点,就像第一次在动物园看到了长颈鹿身上的花纹。
他已经这么老了吗?晚上躺在黑暗中把时空抽去的时候他经常觉得自己只有二十岁,十几岁,觉得自己分明还是个少年。觉得自己还是那个大学里的英俊男生,当年暗恋他的女生也不少吧。他年轻时若急着结婚的话有什么结不了的?别人只是急着匆匆赶日子,急着结婚急着生孩子急着让孩子长大急着变老急着死掉,可他不想。那种一路奔过去找死的人生有什么意义,人生如果没有意义,按部就班结个婚生个孩子就能让人生生出意义吗?他一心想把那点年轻无限拉长无限放大,好够他一辈子用,就算它已经很稀释很稀释了也毕竟是年轻时候留下来的血液,他喝着它便感觉自己还是个没有断奶的婴儿。可是现在,这具皮囊根本不管他葱郁的内在,兀自朝着那个方向老去,一路老去。他连这具皮囊都追不上。他悲从中来,突然便大声抽泣起来。珍珠熊爬到他赤裸的身体上窜来窜去,像企图要安慰他。
等到哭声渐小,抬头一看已经快十一点了。他赶紧去洗了把脸,把头发梳整齐,他得给自己留下充裕的出门时间。洗脸梳头之际他又发现两鬓长出了几根白头发,于是赶紧戴上手套动手染头发。等到染发剂洗掉之后又发现鬓角留下了一片黑渍,怎么洗也洗不掉,胎记似的。时间不多了,他只好懊恼地留着它,简直像留着一个罪证,好像他多重视这约会似的。接着他换上了熨好的新衣,穿上新鞋,然后站在镜子前做最后的彩排。这最后一次彩排中他又发现问题了,他看着镜子里的男人,条纹衬衣,黑裤子,黑皮鞋,浑身上下新得无懈可击,可是他就是觉得哪里不对劲。他后退几步,眯着眼睛看了又看,明白了,问题就是太新太隆重了,镜子里的男人看上去更像个正在出席会议的乡镇干部,随时准备着做工作汇报。他一赌气,索性把笔挺的新裤子脱掉,换上了另一条半旧的裤子。把珍珠熊安顿到篮子里之后他便放心出门了。对饭店的距离进行估算之后他做出了一个规划,先乘坐公交车到比较近的地方了再下车打车打个起步价过去,既省钱又体面。
到了饭店门口他看了看表,离约好的时间还差五分钟,现在就坐到里面等的话,显得他就像一桶推销不出去的过期食品在搞促销。不行,他要把这五分钟精确地打发走了再进去,由于怕在门口碰到熟人他便躲进卫生间里,又反反复复照了五分钟的镜子这才踩着整整齐齐的点前去赴约。
他进去一看,老朋友已经和两位女士在里面坐好了。两位女士肯定有一位是主角一位是配角。他想,这四五十岁的老女人了,来相个亲还要闺蜜护驾,好像唯恐被大灰狼拖走一样。真是每个女人都有返老还童的绝技。他用余光一扫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妖媚更鲜艳一点,明显身上的首饰也多出几件,看一眼都觉得琳琅满目,像个刚装修过的橱窗。老友和李心藤打着招呼,老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张女士,这位是她的好朋友王女士……我们这都多久没见了,是吧?我就觉得有阵子没见你了……你还不知道吧,我都做外公了,哈哈,抱了一个胖外孙……老友和他同岁,外公这样老态龙钟的词听起来让他如坐针毡。不就是做个外公吗,有那么值得高兴吗?大约这世上有一个新鲜的人带着自己的几分之一的血液替自己往下活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罢。
两位女士默不作声,他顿觉尴尬,两个同龄的男人,一个已经做外公了,一个至今没有娶亲,还放到一起,终究是有些别扭。老友开始介绍张女士的工作情况,……很不错的工作,有一个儿子都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这时候李心藤咧嘴一笑,露出了一口墓碑似的牙齿,其中还有一个阴森森的豁口。那是他年轻时有一次喝醉了,脸朝下趴在了地上,把一颗牙齿撞飞了。他崇尚原生态所以也懒于修补,从此以后那个地方就一直豁然敞着,终日走风漏气的。他看了一眼对面的女人,张女士正意味深长地看着她的军师王女士,王女士则像鉴赏文物一样看他两眼再看两眼。然后两个女人一起看着老友。
李心藤心中顿时明白,今天这新衣服白穿了,白头发也白染了。他心中先一凉继而又凛冽一笑,打断了老友的话题,突然带着一脸的兴奋对那三个人说,你们养过老鼠吗?我就养了一只,好可爱的耶,身上像奶牛一样黑一块白一块,它还有个名字叫珍珠熊,这名字听起来是不是很庞大,哈哈,其实它还没有我的手掌大,我就叫它熊熊。
他一边说一边甩开腮帮子大口吃菜,因为少了一颗大磨牙的缘故,他把嘴里的菜都挪到门牙上咀嚼,奈何门牙的容量有限,于是满嘴的菜都堆到了嘴唇上,眼看就要溢出来了。然而满嘴的菜还是没有影响到他同时说话,他继续说他的爱鼠,熊熊什么都吃,苹果,梨,所有的水果都爱吃,还吃面包还喝牛奶,简直像个小婴儿。你们肯定在想我为什么要养它呢,哦,最初是因为我发现我家里有老鼠,还不止一只,我就亲眼见过一只大老鼠大摇大摆地从我面前走了过去。所以我后来就养了熊熊,我想着它能不能把它的其他同类都召唤出来,然后我一举消灭它们。这都养了三年了,也没见它召唤出一只同类,我常想,哈哈,难道因为熊熊身上有奶牛的花纹,其他老鼠就不认它,把它逐出鼠类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其他三个人默无声息地看着他,连张女士身上的珠光宝气都黯然失色了,好像瞬间都悄悄藏起来了,大约也是觉得派不上用场了。他笑完了继续假笑,甚至为自己讲的笑话笑出了眼泪,好驱散这尴尬的沉默。
二
张女士站起来,李心藤这才发现她今天还特意裹了一条披肩,如今这个年龄的女人人手都给自己弄了一条披肩披着,就连卖菜的也披着一条旖旎的披肩,队服似的。大约披在身上便生出了不少底气,自觉知性优雅,气质一路往上飙升。张女士脸上不自在地假笑着,裹了裹披肩,一副不胜寒的模样。她说有事得先走一步了。她的女伴显然还没有吃饱,略带着恼怒却也站了起来,搀着张女士的胳膊,像丫鬟服侍着自家的小姐,两个女人逃走了。李心藤起身,像个门童似地把两位女士送到了门口,并绅士式地微微鞠躬致意。
只剩下两个男人了,老友问,觉得怎么样?李心藤又是咧嘴一笑,露出了那只黑森森的豁牙,里面还塞有一片绿色的菜叶。这么宽敞的豁口,吃饭的时候估计塞进几根蒜薹都不成问题。此刻他觉得老友简直是两个女人的同伙,他决定自卫,他斜睨着老友说,我觉得……太老了吧,你看她皮糙肉厚的,该松的地方都松了还要在那扭捏作态。老友看着一桌子菜一圈空座位说话了,老李啊,不是我说你,你这样下去就只能打光棍了,你就只能一个人老死在屋里很多天都变臭了也没有人发现你。你就情愿一个人老死都不愿娶个媳妇啊?有个女人有什么不好,有人给你做饭给你洗衣,你还想要什么,难不成你六十岁的老头子了还想生几个儿子?你要是压根就没有相亲的诚意你可以不来嘛,又没人要把你押过来相亲是不是。你看你还穿得人模狗样地过来相亲,衬衣领子都熨得这么挺,就是开会也没见你这样,怎么来都来了就是嘴里不说人话,尽说你什么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