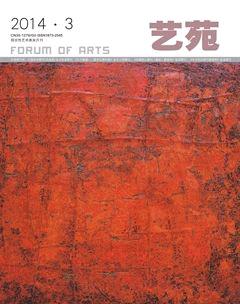《终局》:语言的断裂与超越
【摘要】 贝克特的剧作《终局》因其文本的开放性从问世以来就吸引了众多读者的注意。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和对贝克特写作经历的梳理,我们发现哈姆和克劳夫复杂的关系,与贝克特本人的创作经历有某种程度的契合。克劳夫的出走象征着贝克特摆脱旧形式、实现自我超越的艺术尝试。
【关键词】 《终局》;语言转向;无能;匮乏
[中图分类号]J83 [文献标识码]A
1948年秋,贝克特刚刚完成了《马龙之死》。为了使自己走出小说实验带来的糟糕状态,贝克特写了一部旨在放松的“游戏”之作,这就是后来使他声名鹊起的《等待戈多》。(1)出乎贝克特意料的是,随手写成的剧本使他终于跻身文学大师的行列,《等待戈多》也成为20世纪知名度最高、最受研究者关注的现代戏剧。而他的另一部戏《终局》(Endgame,1957),相较于具有消遣性质的《等待戈多》,则可以说是反复斟酌之后的成熟之作。贝克特为这部剧倾注了大量精力,他反复修改剧本力求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贝克特对《终局》抱有很大的期望:“我迫切想看到它上演,进而知道自己是否上道,能否继续踉跄前行,还是仍在沼泽当中。”[1]296实际上,《终局》成为了贝克特自视最满意也是最难懂的作品。他承认,《终局》要比《等待戈多》更残忍、更绝望、更加趋近终结。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为之,《终局》中哈姆的母亲耐尔(Nell)是贝克特戏剧里唯一死在舞台上的角色。布鲁姆给予贝克特和《终局》非常高的评价:“在我们这混乱时代的优秀剧作家,如布莱希特、皮兰德娄、尤内斯库、洛尔卡和萧伯纳等人之中,难以找到与贝克特并驾齐驱者,他们没写过《终局》……我无法想象任何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像《终局》一样,创作于1957年,却丝毫不减其原创性,迄今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挑战这种原创性。”[2]398布鲁姆同时强调《终局》比《等待戈多》更极端:“对于《终局》的演出,即使再好我也只能强迫自己去看,后者(《终局》)是更杰出但也更狂野的作品。”[2]395由于贝克特不愿意赋予作品确定的意义,他也从不解释自己的作品,这使得他的戏剧尤其是《终局》有着近乎无穷的阐释空间。权威如阿多诺,也选择以“Trying to Understand Endgame”为题来尝试解释《终局》。对于这样的作品,没有人可以担任法官的角色去裁决谁对谁错,因此,本文仅尝试提供一种新的角度来理解《终局》。
一、哈姆与克劳夫:语言的断裂
曾经有研究者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解读贝克特的作品,认为1933年贝克特接受心理医生拜恩治疗抑郁症的经历对他的创作有非常大的影响。据安兹耶(Anzieu)分析,小说《怎么回事》实际上是贝克特和拜恩同性恋关系的隐喻。(2)阿贝尔则认为,《等待戈多》与《终局》实际上是贝克特与乔伊斯师徒关系的隐喻。[3]54虽然这些看法有过度解读的嫌疑,不过它们提醒读者贝克特的作品并非完全脱离现实的创造,我们仍有可能从作品里找到现实的蛛丝马迹。
《终局》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哈姆(Hamm)和克劳夫(Clov)之间的关系。贝克特曾经看过一篇关于长期的囚禁会使人脸色变红的报道,于是他最初创作剧本的时候,把克劳夫与哈姆的脸都描绘成红色[4]97,暗示角色被禁锢在屋子里无法离开。在最初的设定中,四个角色没有名字,直接以ABCD来代替。而在正式的剧本里,角色的名字变成了克劳夫(Clov)、哈姆(Hamm)、纳格(Nagg)、耐尔(Nell)。正因为贝克特对角色名字作了有意修改,很多研究者试图从分析名字入手来解读《终局》。哈姆(hamm)是英文“hammer”的变体,而Clov、Nagg、Nell分别与钉子的法文(clou)、德文(nagel)、英文(nail)单词相近。这些设定都预示着人物之间的激烈冲突。哈姆是个双目失明、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他的生活完全依靠克劳夫,而克劳夫则需要哈姆储藏的食物来维持生命。他们这种若即若离又彼此依赖的关系,如同被橡皮筋束缚的两个人,一旦彼此远离,就会被巨大的力量拉回来。在剧本开头,双方的对话就显示了这种尴尬的生存状况:
哈姆:为什么你要和我呆在一起?
克劳夫:为什么你留着我?
哈姆:因为没别的人可留。
克劳夫:因为没别的地方可呆。[5]10
两者残缺的身体特征也暗示着哈姆和克劳夫的关系。哈姆无法站立,眼睛是瞎的;克劳夫虽然可以行动,但是背驼的厉害,而且无法坐下。考虑到贝克特对笛卡尔非常熟悉,他的第一部单行本作品就是关于笛卡尔的长诗(whoroscope),我们很容易发现克劳夫与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相似之处。无法坐下、终日忙碌的克劳夫象征着机械式的身体,而没有行动能力却发号施令的哈姆则是驱使身体行动的神秘灵魂。按照笛卡尔“我思”的本体论证明,只有思维着的“我”才是不可能被推翻的实存,精神和肉体是相互独立的,而且精神可以通过改变生命精气的运动方向来控制肉体。[6]86这样一来,尽管克劳夫具备行动的能力,但是他仍然要服从精神(哈姆)的命令,他根本不可能离开哈姆。换句话说,快死掉的哈姆是戏中唯一的支配性力量。他不但没有极力阻止克劳夫出走,甚至连出走的想法也是哈姆灌输给克劳夫的。在剧本快结束的时候,哈姆似乎放弃了对克劳夫的控制,他对克劳夫说:“结束了,克劳夫,我们已经结束了。我不需要你了。”接着,哈姆和克劳夫一反常态地伤感了一把,他们如同在车站永别的恋人一样温情脉脉地相互道别(3):
哈姆:克劳夫!(克劳夫停下,未回头。略停)
没什么。(克劳夫又往前走)
克劳夫!(克劳夫停下,未转身)
克劳夫:这就是我们说的抵达出口。
哈姆:谢谢你,克劳夫。
克劳夫:(转过身,激动地)啊,对不起,是我该向你道谢。
哈姆:是我们,该互相道谢。[5]74
随后克劳夫离开舞台,没有回应哈姆的呼唤,贝克特也没有明确告诉读者克劳夫是否出走。剧本结束的场景与剧本开始时完全一致,哈姆“用手帕盖住脸,让两条胳膊耷拉在扶手上,不再动了”。[5]76
如果进一步分析哈姆和克劳夫的台词,我们会发现两种不同的语言模式。在荒诞派戏剧中,剧作家往往通过人物语言的长度、有效性(表达意义的能力)以及语言的情绪变化来表现剧作主题。比如尤内斯库的《椅子》,通过不断到场的没有台词的客人们隐喻物对主体的碾压,演说家发出的无法辨认的声音则象征着真理和秩序的失落;品特的《房间》、《轻微的疼痛》等剧用不同角色语言冗余和沉默的对比来表现权力关系的不对等;贝克特在《等待戈多》里则有意让身为奴隶的幸运儿背诵大段没有停顿的台词来增加荒诞感,这些难以理解的台词里恰恰包含了“时间”、“上帝”、“空间”、“存在”、“劳动”这些高级词汇。而在《终局》中,哈姆和克劳夫的台词不像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那样平等,哈姆的台词比克劳夫的多很多,既有对克劳夫的命令,也有对生活的抱怨,还有几段很长的独白。而克劳夫的台词则少得多,而且除了登场和离场的几段台词,几乎都是对哈姆命令和询问的回答。哈姆的语言经常表现各种不同情绪,比如愤怒、恐慌、吃惊、沮丧,甚至他在讲述故事的时候还显得相当兴奋。他的语言大部分时间是刻薄无礼的,但是有时候又流露出一丝温情,尤其是他回忆过去的时候。而克劳夫的语言完全不同,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以“目光呆滞、语调平直”的疲惫状态说话,几乎没有语气变化。克劳夫如他自己所说,对生活“一直都厌倦”,几乎维持不动的客体状态。简言之,哈姆的语言主动富于变化,居于支配地位;克劳夫的语言则被动单调,居于被支配的地位。在剧本里,哈姆和克劳夫都说过“克劳夫”这个名字,但是“哈姆”却从来没有从克劳夫的口中说出来过。在剧本的最后,克劳夫发表了自己的“出走”宣言:“我在心里想……克劳夫,有时,你必须更好的承受这样的痛苦,如果你希望别人厌倦对你的这种折磨的话……有朝一日。我对自己说……克劳夫,有时你必须更好地呆在这儿,如果你希望他放你走的话……”[5]73这种称谓的缺失显示他心里仍有对哈姆的敬畏,所以克劳夫只能同自己对话,他始终无法成为与哈姆平等对话的另一个主体。在两人的关系中,克劳夫永远处于下风。
哈姆强烈的表演欲望使《终局》变成了一出戏中戏。台下的观众与台上的演员构成了第一层观演关系,而舞台上的哈姆与其他角色(克劳夫、纳格、耐尔)则构成了第二层关系。哈姆反复要求克劳夫把自己推到屋子的中央,仿佛主演在寻找最佳的表演位置。他还十分在意克劳夫和纳格对自己讲述的故事的反映,如同一名演员热切地期待观众们的称许。哈姆进入表演的狂热状态、成为台上真正的演员,其余的角色则是迷惑的观众。生命力开始从他衰败的身体里涌出,他又能暂时恢复世界的秩序。表演,或者说掌控语言的能力是哈姆支配性力量的源泉。与克劳夫相比,哈姆拥有唯一永恒的资源就是他的语言。哈姆讲述的故事,他教给克劳夫的词语,才是克劳夫想要抗拒但又无法离开的。有评论家指出,贝克特的创作一直面临着悖论:“在撕下语言的面纱并揭示语言背后隐藏的空无之前,他自己必须先要编织语言的面纱。”[6]50对《终局》来说,克劳夫也面临同样的语言困境。哈姆是克劳夫意义的最后来源,克劳夫只能用哈姆的语言来摆脱哈姆。克劳夫疑惑为什么哈姆能够控制自己,当他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感到他已经厌倦了哈姆的故事,他希望出走。可是他的语言完全继承自哈姆,克劳夫没法用自己的方式思考问题。克劳夫抱怨自己使用的话都是哈姆从前教过的,如果哈姆仍然要控制自己的话,那么他就得教克劳夫新的语言或者不让克劳夫开口。在下场前,克劳夫这样反思他与哈姆的关系:
克劳夫:(目不转睛地看着,声音含糊)你对我说过,爱,就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相信我吧,你看见了吧……
哈姆:说清楚些!
克劳夫:(依然声音含糊)……这很简单。
你对我说过,友谊,就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向你保证,你不需要到远处去找。你对我说,就是这儿,别走,抬起头,看这种荣耀。这是个命令!你对我说过,来吧,你不是一个笨蛋,想想这些事,你将发现一切都变得那样清晰,而且简单!(4)[5]72
克劳夫关于世界的概念以及逐渐失效的语言都来自于哈姆,所以哈姆期待的“可以在心里回忆回忆”的真心话克劳夫是说不出来的。不但如此,克劳夫和哈姆都已经意识到,在匮乏的语言影响下,克劳夫不可能寻找到自我,他只能是一个沉默的客体、一个完全听命哈姆的仆人,或者成为缺失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另一个哈姆。哈姆曾预言式地告诉克劳夫:“在我这所房子里,有那么一天,你将变成瞎子。像我一样。你将坐在某个地方,孤零零的感到空虚,永远地陷于黑暗之中,就像我一样。有那么一天你会对自己说,我累了,我要坐下,你就去坐下了……是的,有那么一天你将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你将像我一样,除了你什么人也没有,因为你将不会同情任何人,也不会有任何人来同情你。”[5]35而克劳夫则说:“可是我觉得自己太老了,已经无能为力了,去养成新的习惯。算了,这永远都结束不了……我求他说说别的话……睡觉,醒来,晚上,早晨,除了这就无话可说。”[5]73话语的力量不但塑造了克劳夫的现在和未来,而且控制着克劳夫的过去。哈姆每天都在重复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内容是有一个父亲为他饥饿的儿子向哈姆讨面包,并且希望哈姆能够收留那个孩子。而每当哈姆讲到孩子的时候,无论克劳夫怎样要求,他都拒绝继续讲下去。看起来克劳夫很有可能就是故事里的孩子,哈姆则是克劳夫的养父。除了讲故事,哈姆还经常问克劳夫是否记得他是怎么来到哈姆家的:
哈姆:你还记得你是怎么来这儿的吗?
克劳夫:记不得了。太小了。你对我说过。
哈姆:你记得你的父亲吗?
克劳夫:(疲惫地)又来了。(略停)你这些问题都问过成千上万次了。
哈姆:我喜欢这些老问题。(激动地)啊,老问题,老回答,只能这样!是我当了你的父亲。
克劳夫:是的。(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是你为我尽了父亲的责任。
哈姆:我的房子成了你的家。
克劳夫:是的。(慢慢地看着四周)成了我的家。
哈姆:(骄傲地)没有我(指自己),就没有父亲。没有哈姆(指四周),就没有家。[5]37
语言型塑主体,并改写主体生成的历史。克劳夫没有能力质疑哈姆的叙述,哈姆则通过反复的讲述和询问构建克劳夫的身世记忆。语言赋予了哈姆裁决历史的权力,他可以通过一个一个的故事重新书写历史(哈姆就认为那些故事是自己创作的小说)。只要他有足够的精力和想象力,哈姆可以让自己的故事永远持续下去没有终结,而可怜的克劳夫只能恳求哈姆“再讲一个”。语言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权力关系,他的思维、语言、历史都是哈姆创造的,即使克劳夫离开了哈姆,他又如何摆脱哈姆对他的影响呢?
二、出走与超越:黑色以外的《终局》
除了语言外,剧本中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弑父。弑父是非常古老的母题,《俄狄浦斯王》就是有关弑父最著名的作品。《终局》与《俄狄浦斯王》也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哈姆是一个双目失明戴着墨镜的瞎子,俄狄浦斯也是瞎子。按照列维·施特劳斯的分析,俄狄浦斯、拉伊俄斯(俄狄浦斯的父亲)、拉布达科斯(俄狄浦斯的祖父)这些名字都与无法行走或者行走困难有关[7]50,而哈姆正好双腿瘫痪无法行走。剧本里哈姆曾挑逗克劳夫:“你就从来没有过这种好奇,在我睡着时,取下我的墨镜来看我的眼睛?”暗示哈姆的瞎眼有不寻常的地方。俄狄浦斯的眼睛恰恰不是自然失明,而是他用母亲衣服上的别针刺瞎的。哈姆不仅与弑父的俄狄浦斯有不少隐秘的相似之处,而且在剧本里,克劳夫与哈姆都直接提到了弑父。哈姆问克劳夫:“你为什么不杀了我?”克劳夫则回答:“我没有搞这种阴谋的勇气。”哈姆还建议克劳夫干掉他,而且他会把餐柜的密码告诉克劳夫,克劳夫则拒绝了这个建议。不过,克劳夫并不是完全排斥这个念头,他也说过:“要是我能杀了他,我会高兴死的。”我们甚至也可以把克劳夫的出走视作弑父,因为他的离开意味着哈姆的死亡。
弑父并不一定如弗洛伊德的理论代表着占有母亲的无意识冲动。这种现象在远古社会非常普遍,一个部族最强壮的男人拥有唯一的繁衍后代的权力,这个部族的下一代都是首领的儿女。当后代中出现了足以挑战首领的男人,弑父便发生了。在文明社会,弑父不再以流血的方式发生,但是这种“取父亲而代之”的心理结构则一代一代慢慢积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克劳夫、哈姆乃至贝克特自己都是尝试摆脱父亲、超越父亲的“弑父者”。那些雄心勃勃意图突破传统的先锋艺术家,都是现代的俄狄浦斯。
对贝克特来说,乔伊斯或许就是那个需要摆脱的“父亲”。年轻的一代意识到自己从旧的偶像那里学到了足够的知识和技能,为了避免成为偶像的翻版,选择出走自立门户,就像《终局》里的克劳夫竭力走出哈姆的阴影。1928年贝克特结识乔伊斯之后,立刻成为了乔伊斯最好的朋友和最忠实的学生。艾尔曼这样描述贝克特对乔伊斯细致的模仿:“像乔伊斯一样,他翘着腿坐,一条腿的脚跟放在下面一条腿的脚面上。他眼睛贴在书本上阅读,嘴里含着香烟。他甚至买了一双漆皮夹跟鞋,号码和乔伊斯的一模一样,尽管穿起来脚发肿并且长鸡眼,但他也坚持穿着。”[8]58当时乔伊斯的视力开始恶化,无法独立完成写作。贝克特担任了他的助手,记录他口述的新小说《进行中的作品》(即后来的《芬尼根的守灵夜》)。两者的关系如克劳夫与哈姆的翻版,贝克特此时成为了乔伊斯身体的替代品,帮助乔伊斯完成他伟大的文学探索。不仅如此,当《进行中的作品》遭到评论界的批评时,乔伊斯召集了12个他的崇拜者为《进行中的作品》辩护,并且将这12篇论文结集出版,排在首位的就是贝克特的论文《但丁……布鲁诺·维柯……乔伊斯》。后来这12个人就被戏称为乔伊斯的12个门徒。[1]83贝克特在乔伊斯诞辰100周年时曾感慨:“在离去之前,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在他的伟大作品和伟大的存在面前,深深鞠躬。”[8]84贝克特早期的创作,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都能看到乔伊斯的影子,这是大多数研究者公认的。这些旁征博引、词语华丽、充满怪异想象的作品甚至可以看作是贝克特对乔伊斯的致敬与模仿,对贝克特来说,乔伊斯是当之无愧的文学教父。但是,这些乔伊斯风格的作品没有获得成功。抱着手稿穿梭于各个出版社,恐怕是20世纪30年代贝克特经常要面对的尴尬。当然,贝克特的不成功并不意味着乔伊斯不够好,恰恰相反,乔伊斯实在太完美,他的创造力、想象力和运用语言的能力无一不是满分,他几乎凭一己之力就穷尽了由他开创的语言实验的可能性,对于任何后来人这都是难以企及的高度。克劳夫告诉哈姆:“我对我们的故事厌倦了,非常厌倦。”[5]67同克劳夫一样,贝克特已经看到了乔伊斯达到的极限,沿着乔伊斯的路走下去已经行不通了,他迫切需要树立自己的文学风格。
在贝克特与乔伊斯的友谊中,也存在着一些插曲。乔伊斯非常重视自己的家人,即使他与贝克特是最好的朋友,他仍然直截了当的告诉贝克特:“除了我的家人外,我不爱任何人。” [3]18(这种说话的口气还真有点像哈姆)不幸的是,乔伊斯的小女儿露西娅爱上了经常出入他们家的贝克特,可是贝克特没有接受露西娅的爱,他犹豫再三还是告诉露西娅他感兴趣的是她父亲而不是他。[8]115由于露西娅已经患上了难以医治的青春期精神分裂症,贝克特的拒绝加重了露西娅的病情,乔伊斯的健康状况也因为这件事迅速恶化。贝克特一直对此事心存愧疚,认为自己亏欠了露西娅和乔伊斯。我们无法估计这件事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乔伊斯和贝克特的关系,贝克特也没有想到自己会给偶像带来灾难,但这种痛苦也许有助于贝克特从崇拜乔伊斯的狂热中清醒过来。
如果说现实中贝克特和乔伊斯没有根本的分歧,那么在文学艺术方面,贝克特似乎要面对乔伊斯带来的更多压力。乔伊斯既是贝克特文学生涯的领路人,也是一座贝克特无法逾越的大山,这两种形象叠加在一起,构成了《终局》里的哈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终局》看作克劳夫摆脱哈姆影响、寻找自我的成长过程。克劳夫和哈姆的对峙实际上是两种风格,或者两种语言——乔伊斯的语言和贝克特语言——的较量。旧的语言已经达到顶峰,甚至开始失效,克劳夫告诉哈姆:“我用的是你以前教我的话。如果这些话不再能表达什么,你就教我别的。或者就别让我开口。”贝克特后来解释过他与乔伊斯的差别:“我意识到乔伊斯的所作所为表现了一个人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可能到达的极限,他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素材。他在不断地增加素材。你只要看看他自己提供的证据,就会明白这一点。我觉得我自己的写作方式则会使素材越来越贫乏,知识越来越少,不断在施予,所以我的素材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9]39从小说《瓦特》开始,贝克特就尝试使用一种新的语言来创作,而他的戏剧作品则充分展示了这种语言的特色。他的作品放弃了名人名言和典故,放弃了故弄玄虚,放弃了复杂华丽的语言,总之他用减法取代了乔伊斯的加法。他不像乔伊斯那样庆贺语言的存在:“我们不能马上消除语言,但是我们可以尽我们所能,让语言渐渐声名狼藉。我们必须让语言千疮百孔,这样,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某种东西,或者根本就没有东西的东西,就会显露出来;我想这可能就是当代作家最崇高的理想了吧。”[10]49贝克特还告诉朋友诺尔森,他的写作重心将集中于失败、贫穷、流放和失落,因为在他看来,世界混乱不堪,人类的理性不值得信任,那些企图增加知识来了解世界本质并控制语言的行为都是徒劳。他在给品特的信中写道:“如果你坚持(从我的剧中)寻找形式,我会为你做一番论述。我曾经住过院,另一个病房里有一位先生,因患喉癌已经奄奄待毙。寂静中我能听见他持续的尖叫声。这就是我作品所具有的形式。”[10]486空无,才是语言的本质。按照贝克特喜欢的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说法,没有什么比“没有什么”更真实,这才是语言不可质疑的根基。斯盖纳有次对贝克特说,他的作品与他认为语言不能传达意义的信条之间有矛盾,贝克特则回答:“先生,我该怎么办呢?这是些字眼,除此之外别无它物。”[3]70贝克特的作品来自思想的最深处,始终与语言的精神本身进行一场不断的斗争和痛苦的角力。此时贝克特与乔伊斯渐行渐远,他逐渐确立了自己的诗学。“语言的本质是隐喻,人与人之间几乎无法有效沟通,并且人根本不可能超越语言来认识事物,这些都使贝克特寻找一种途径去精确表现语言的不可能性。这样做的结果是贝克特语言的赤裸与贫瘠同乔伊斯式的充裕形成了尖锐的对比。”[6]60贝克特在1956年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作为一个艺术家,乔伊斯追求的是全知全能;而我在创作中只关心无能和无知。我不认为在我之前,‘无能曾被严肃地探讨过……在今天,我认为任何人只要稍微关注一下自己的存在就会发现那种无知者和无能者的经验。其他形式的艺术家——日神——与我的精神气质绝不相通。”[11]160贝克特的成熟作品,尤其是戏剧,特别重视表现这种生存体验。《终局》里的哈姆与克劳夫、《等待戈多》里的波卓与幸运、《最后一盘录音带》里的克拉普,都是“无能”和“无知”的代表。这些作品多是抽象表现人类生存的痛苦,这种痛苦并非由具体的原因造成,所以也无法摆脱,痛苦就是生存的本质。贝克特将其归结为“出生的原罪”:“悲剧与人的正义无关。悲剧是某种赎罪的证词,但不是那种可悲的赎罪——是一种由一帮无赖为一帮白痴准备的,与实地情况相违背的杜撰性语言。这个悲剧形象体现了对于原罪的赎罪,对于人及其他的厄运之伴的最初及永恒之罪的赎罪,对与生俱来之罪的赎罪。人之最大之过是其被出生。”[12]9在贝克特看来,只有使用全新的形式,才能表现“无知”和“无能”的内容并揭示最本质的痛苦。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放弃旧有的语言观念,而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正好赋予了贝克特新的武器。
贝克特对于语言的否定性看法深受奥地利哲学家毛特纳的影响。贝克特是从乔伊斯那里得知毛特纳的,但是与乔伊斯接受毛特纳的方式不同,贝克特非常重视乔伊斯所忽视的抽象哲学,而不是仅仅关心毛特纳举出的实例。在贝克特的笔记中,常常整页抄写毛特纳的《语言批判》,并且在他的《无线电速写》里,直接提到了毛特纳,这是他最后一次在作品里提到哲学家的名字。[13]95考虑到贝克特曾在采访中表示从不阅读当代哲学家的作品,因为他搞不懂他们究竟在说什么,那么他的语言哲学认识应该大部分来自于毛特纳。[11]239毛特纳认为思考和言说是同一的,即语言不是思考的工具而是思考本身。我们必须通过语言才能思考世界,我们也不可能以上帝般的角度来观察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如毛特纳所说:“我们只能思考在语言中我们能够表达的,我们只能表达那些我们思考过的。”[13]99贝克特同样认为,“谈论和思考理性或语言问题是超出我们智力范围之事”。结果,语言被上升到世界本原的地位。但是语言并不如看起来的那么可靠,语言并不是对世界的真实反映。正相反,我们通常认为的真实是由语言型塑的,语言不能描绘真实,它所做的是构建抽象的概念和思想。毛特纳强调,语言的本质是隐喻,它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并非一一对应:“我们到处散发词汇如同散发钞票,却忘记自问在国库中是否有物质实体式的资金给这些钞票的面值作担保。” [13]104贝克特在与考恩的通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的语言在我看来越来越像一个面纱,只有把面纱扯开,才能看见背后的东西,或者看见背后其实什么东西也没有。”[9]39语言不能说出真实,也无法承担意义,它之所以还有效就是因为人们对词语抱有古老的迷信,习惯已经形成。贝克特在一条笔记里写到:“人的话语绝不会帮助他了解世界。无论谁在说话都只是在记忆自己的感觉;任何听话者都绝不会体验到比他所知道的更多的东西,不会体验超越他的词汇中已经包括的东西。”[1]67《终局》巧妙地表现了这种语言观:克劳夫面临同样的窘境,语言的匮乏使得他只能做一个“听话者”,他根本不能从语言中增加对世界的理解,也永远无法反驳哈姆对自己身世的叙述。在毛特纳看来,语言不但不值得信任,而且任何批判的语言的“语言”都要陷入自我指涉的圈套,最终会导致“思想的自杀”,这种“自杀”意味着完全抛弃旧的自我封闭的语言系统。
对贝克特来说,由于他已经意识到语言存在致命的缺陷,他迫切需要新的形式(戏剧就形式而言,是更纯粹的语言游戏)来继续他的文学创作,毛特纳的语言批判正好为他指明了方向。
为了实现“思想的自杀”,贝克特不但完全改变了写作风格,并且选择用法语写作。英语对他来说已经变得困难甚至无意义了:“语法与形式!它们在我看来像维多利亚时代的浴衣和绅士风度一样落后。”使用法语让贝克特写起来更顺手和不受风格影响,也让他摆脱了母语带来的陈规和惯性,这正是毛特纳批判的语言意义的虚假来源。贝克特需要对语言做减法,从而揭示语言的本真,法语显然比英语更合适。另外,贝克特使用英语写作难免不会受到乔伊斯的影响,他需要外语的帮助来走出乔伊斯无所不在的影子。从用法语写作《瓦特》开始,贝克特的作品专注于展示语言的空洞无力,这与他早年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语言的转变或者说断裂,贯穿了贝克特成熟时期的作品。
三、结论
不管《终局》看上去多么古怪,剧中核心的要素就是语言。语言首先决定了克劳夫和哈姆的权力关系,哈姆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而这种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又是青年贝克特与乔伊斯关系的翻版。即使我们不能把乔伊斯和哈姆简单地等同起来,起码可以认为哈姆象征着旧语言的巅峰,而这种无所不能的语言正好是贝克特竭力摆脱的。克劳夫的出走可以看作是贝克特摆脱乔伊斯影响、探索自己文学之路的尝试。无论剧中克劳夫的命运如何,在现实中贝克特还是成功地完成了“弑父”,即对乔伊斯的超越。贝克特没有变成第二个乔伊斯,相反他发现了语言的另一种可能性,并且因为他的出色创作我们在文学史上就有幸看到了乔伊斯与贝克特两位风格各异的大师。
《终局》蕴涵着丰富的可能性,这是它吸引读者的原因。贝克特说:“我戏剧的关键词就是‘可能。”妄图为《终局》确立唯一的解释,无异于焚琴煮鹤。通常,我们习惯了黑色的贝克特,但不要忘记,现实中的贝克特与捷克著名的异见作家哈维尔是好朋友,并且他创作了剧本《大灾变》(Catastrophe)声援当时被捕入狱的哈维尔,这是他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那么,《终局》是否也隐藏着光明的一面呢?或许那个残酷阴暗的世界背后,同时存在着贝克特自我超越的伟大尝试。
注释:
(1)如果视1931年的长篇论文《普鲁斯特》为贝克特踏入文坛的开端,那么在20年的时间内他都算不上特别成功的作家。他的作品因为过于先锋而得不到世人的认可,1936年完成的《莫菲》曾被四十多家出版社拒绝,两年后才得以问世。
(2)参考《不断延伸的思想图像:萨缪尔·贝克特的美学思想与创作实践》一书第二章第八节:“贝克特与现代心理学和二十世纪哲学思潮。”
(3)此处与之前克劳夫的自白是全剧感情最集中的体现,以荒诞派剧作的标准来看,可以算的上罕见的温情了。
(4)《终局》英文译文中克劳夫说的是“They said to me, Thats love”。考虑到克劳夫的语言只可能学习自哈姆、纳格、耐尔三人,“他们”也可能指的是哈姆。
参考文献:
[1]王雅华.不断延伸的思想图像:萨缪尔·贝克特的美学思想与创作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3](英)马丁·艾斯林.荒诞派戏剧[M].刘国彬,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
[4] Fletcher, Beryl S and Fletcher, John, A Students Guide to the Plays of Samuel Beckett[M].London: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78.
[5] 贝克特.贝克特精选集:是如何[M].赵家鹤,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
[6] Jaurretche, Colleen. ed. Beckett, Joyce and the Art of the Negative[M]. Amsterdam: Rodopi, 2005.
[7](法)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陆晓禾,黄锡光,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8](美)罗伊丝·戈登.萨缪尔·贝克特和他的世界[M].唐盛,等,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0.
[9](英)詹姆斯·诺尔森.贝克特肖像[M].王绍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0](英)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M].朱近东,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11]L. Graver & R. Federman. ed. Samuel Beckett: The Critical Heritage[M]. N.Y.:Routledge, 1979.
[12](爱尔兰)塞缪尔·贝克特.普鲁斯特论[M].沈睿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13]雷强.“言无言”论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中的语言哲学思想[J].外国文学评论,2010(1).
作者简介:曲爽杰,厦门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