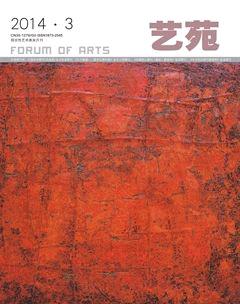“成功真的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导语:2013年10月4日,携带一本《基耶斯洛夫斯基谈基耶斯洛夫斯基》,笔者从阳光寂静的小岛厦门飞向晚秋尚未冻结的华沙平原。基耶斯洛夫斯基是笔者此行最重要的目的。作为一名华沙大学的交换生,笔者每天穿越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片场——科学文化宫的地下通道、克拉科夫大街的圣十字教堂以及耸立哥白尼雕像的波兰科学院。推开华大古老教学楼厚重的大铁门,听从来不微笑的Miroslaw Jelonkiewicz 教授郑重地用汉语“你好”与我们寒暄之后,一节“基耶斯洛夫斯基和他的电影”的英文课程便开始了。幸运的是,笔者到来的这个落叶绝美的时节,也正是第20届华沙电影节在波兰最高建筑物文化科学宫举办之时。在“波兰经典电影”这一环节的电影放映活动中,笔者有幸见到了诸多曾与基耶斯洛夫斯基朝夕相伴的重要人物,这其中有《爱情短片》的女主角扮演者Grazyna Szapolowska,《摄影迷》中的男主演Jerzy Stuhr,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御用摄影师Slawomir Idziak,以及曾凭借《寂静太阳年》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在国际影坛与瓦伊达、波兰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齐名,目前仍活跃于电影界的波兰著名导演克里斯多夫·扎努西(Krzysztof Zanussi)。
克里斯多夫·扎努西,1939年生于华沙,1960年进入罗兹电影学院学习电影,后成为波兰八大电影创作集团之一的托尔电影集团的主导人物,是波兰70、80年代“道德焦虑”电影的先锋,被誉为波兰最杰出的导演之一。他长期担任波兰电影协会主席和副主席,1973年获波兰文艺部国家奖,1984年凭借《寂静太阳年》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2000年以《生命宛如致命恶疾》获第22届莫斯科电影节最佳影片。他不仅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生前的挚友,而且也是基耶斯洛夫斯基1975年以后大部分剧情片的制片人。
在扎努西担任董事长的托尔电影集团(“TOR” Film Production)会客厅,笔者获得了一次与他对话的机会。
笔者:第20届华沙电影节期间,在“波兰经典影片”放映环节,我有幸观看了您在1969年拍摄的影片《钻石的结构》,这是您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此后70年代后期您又率先开辟了“道德焦虑电影”(Cinema of Moral Anxiety)这一波兰电影史上至关重要的电影流派。因为国内可以查到的资料非常的少,可以请您为我解释一下什么是“道德焦虑电影”吗?
扎努西:“道德焦虑电影”实际上是评论家们的创造。他们认为这一流派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约一直延续到80年代。当时的波兰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波兰的文化政策主要指向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部分电影反映的现实都在迎合这一理念,但真正的社会现实和这套理念是完全相悖的,道德焦虑电影就是要反对虚伪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尝试以隐蔽的方式躲避电影审查,呈现现实原来的模样,这是一个非常态的不辨是非的世界,道德价值和理想相继丧失,不仅充斥着权力的滥用、自由的缺失和腐败的猖獗,人际关系也处在冷漠和堕落的边缘。评论家们认为我的《家庭生活》(Family Life) 和《合约》(The Contract)都属于这一流派,当然,他们也把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这期间拍摄的《职员》(Personnel)、《摄影迷》(Camera Buff)《机遇之歌》(Blind Chance)、《无休无止》(No End)归于此类。除此之外,阿格涅丝卡·霍兰和瓦伊达也曾创作过此类作品。
笔者:1989年之前的波兰电影和中国一样,都要面对电影审查,那么,这些违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片是如何通过审查的,在没有政治审查的今天,波兰电影面临的新的挑战是什么?
扎努西:关于政治审查,有很多的文献都大量讲述过,你如果感兴趣,可以找来看看。波兰的政治审查是对已经制作好的电影的审查,他们会剪掉除片中他们认为政治不正确的内容,如果导演不同意,这部影片就无法上映。还有一个选择是,导演同意剪掉那些部分,然后删掉自己的名字,再放映这部影片。政治审查刚开始的时候很严肃,后来越来越轻松而且腐败,也许通过贿赂审查人员,审查就会放松。最初审查人员自己相信审查制度是有必要的,后来他们本人也意识到这是多么的荒谬。
我认为波兰电影最伟大的时刻就是现在。你有注意到我们目前正在院线上映的影片吗?瓦伊达导演的《瓦文萨》讲述了苏联解体后波兰第一任总统的生活,瓦文萨目前还在世。还有保罗·帕夫利克夫斯基的作品Ida,它已经斩获了包括多伦多电影节、伦敦电影节在内的多项国际大奖。而最近我们也有一部涉及酗酒问题的电影Pod Mocnym Aniolem正在上映,由斯玛佐斯基导演。另外,我们目前还有同性恋题材的影片《漂浮的摩天楼》!
笔者:我知道您在1955至1959年期间在华沙大学就读于物理系,在学习物理的同时又在波兰科学院艺术协会(Institute of Art of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学习电影,业余拍摄了一系列的短片,获得了一些奖项,后来曾进入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学习哲学,在1960年之后才考入在波兰乃至全世界都十分卓越的罗兹电影学院正式学习电影,1966年从这所学校毕业。我想问的是,您的求学经历十分丰富,并不是一开始就钻研电影,为什么会经由物理、哲学到达电影?对您影响最大的电影导演是谁?
扎努西:我进入大学时正逢斯大林主义在波兰的余威仍旧凶猛的时期,那时候很多学科都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非常深重,包括建筑。我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学习建筑的,我本来也要学习建筑,但是实在不喜欢苏联时期的建筑风格。而在当时,唯一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学科是像物理、数学、化学这样的学科。于是我选择了学习物理。物理其实挺有意思的,但我喜欢物理,物理却没有喜欢上我。在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波兰在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领导下,社会意识形态处于松动状态,于是我就开始在业余拍摄电影,当时有一个业余电影节,设十个奖项,我获得了其中七项。那时我还是个年轻人,受到这样的夸奖,觉得非常高兴,备受鼓舞,因此就决定正式转移到学习电影。
我最喜欢的导演是伯格曼。电影和其他艺术一样,总是有许多类型和规则,可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伯格曼就不受任何类型和规则的束缚。真正的艺术是没有类型的,伯格曼把这当做他的原则,这对我影响很大。此外,他的作品透露出的异常冷静的风格和理性哲思也启发了我的创作。
笔者:您在罗兹电影学院学习期间,曾经被学校开除,我很好奇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扎努西:我刚开始在罗兹电影学院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很多教授都对我赞赏有加,但是三年后我去了法国,在那里接触到了法国新浪潮以及诸多新锐导演。回国后我试图使用新浪潮的方法来拍实验电影,例如使用手持机器、演员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像业余电影一样。但我的老师们很不理解,他们认为,你入学的时候就是一个业余摄影者,现在你又要用业余摄影的方法来拍电影。之后我就被开除了。当时我非常难过,现在我理解了,他们反对是因为当时他们完全没有了解过新浪潮。
笔者: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摄影迷》(Camera Buff)中您友情出演了您自己,足见您与导演的深厚友谊。而在片尾男主角毁弃自己的电影作品,转而将摄影机镜头对准自己,这是否暗示了导演思想的转变,也就是说,他的镜头逐渐从关注外部社会与政治对人的压迫和束缚转向了自我、内心和人性?
扎努西:在《摄影迷》中我出演了我自己,其中一部分在审查时被剪掉了。我在电影里面说过一句话,“好人成功的机会很小,基本上没有这个机会。”“基本上没有这个机会”就被剪了。艺术家最终都要将摄像机对准自己,了解自己。
笔者:众所周知,您和基耶斯洛夫斯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您眼中,基耶斯洛夫斯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外界对他的普遍性评价是,他是一个忧郁、沉默的人,您认同这个看法吗?
扎努西:在罗兹电影学院期间,我比基耶斯洛夫斯基高一个年级,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们的审美、对世界的看法都很相似。我支持过他很多电影。他和我的妻子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我妻子是一个画家,同时也做剧场艺术,她喜欢园艺,而基耶斯洛夫斯基也特别爱种植玫瑰。
忧郁和沉默是他的外表,这只是习惯的不同。就像我一直穿西装打领带而他习惯穿毛衣是一个道理。基耶斯洛夫斯基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幽默或者不微笑,他是对生活非常的严肃。他觉得生活不是游戏。
他去世大概十年后,有一个瑞士人碰到了我,给我讲了一个他从未向他人提及的故事。这应该算是关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一个独家故事。原来当时柏林举办过年轻电影专家的周末讲座,给有志于电影的年轻人提供帮助和培训。基耶斯洛夫斯基也曾是主讲人之一。特别离奇的是,在培训期间,基耶斯洛夫斯基打了他一耳光。这个瑞士人当时特别气愤,转头就去了当地警察局投诉。然而排队等候时他突然后悔了,他想我应该怎么才能用自己可笑的瑞士德语给德国警察说明我花了300马克来培训,还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波兰人打了一顿,这些警察又会如何看待我。他想起了基耶斯洛夫斯基举起手掌时对他说的话,“你就是个骗子,从早到晚骗自己,永远不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你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你需要救自己,你需要面对本真的自己,了解本真的世界!”想到这儿他从警察局缩了回来,放弃了投诉。这个瑞士人对我说,活到现在,连他父亲没有打过他,而一个素昧平生的波兰人居然一边骂他在过着虚伪的生活一边狠狠给了他的人生一记耳光。这件事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所以基耶斯洛夫斯基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他觉得瑞士人是误入了生活的歧途,所以就一定要挽救他。这是他独特的美德。
笔者:那么,您觉得基耶斯洛夫斯基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扎努西:他不是悲观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他的问题在于,他的成功来得太晚了。成功有一个最好的时间,不能太早也不能太迟。对他来说,他的成功来得太迟了。后来他认为,成功真的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他获得国际声誉后反响巨大,但是那时候他却说,我不想再拍电影了。我力劝他,不,你必须得继续拍电影,现在大家都十分喜欢你的电影。但是他坚持要在事业的顶峰期隐退。其实真的很遗憾,因为后面他的生活状态并不理想。
为什么他认为成功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呢?法国的戛纳电影节,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有四次想要参赛,但是都被拒绝了。戛纳的评委对我说,请你不要再送他的电影来,他只适合在波兰本土拍电影,但是走出波兰,没有人会喜欢他的作品。1988年,第41届戛纳电影节,那期间基耶斯洛夫斯基正好拍完了《杀人短片》,戛纳再次拒绝了他。巧合的是,有一部本应提名的影片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参赛,出于同情,电影节提名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新作。但谁也没想到的是,就是这部先前被评审团拒绝的影片,赢得了评审团大奖。这让他觉得成功其实是个瞎子,它很盲目,来得偶然而非理性。他不能相信他的成功,甚至他持续地认为,他并不是一个优秀的电影制作者:如果他是,那么为什么在更早的时候人们没有发现他的才华呢?他认为,所有环绕着他个人的这些所谓的成功的“噪音”都是毫无意义的,成功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痛苦地看到,世界是如此的愚蠢。
所以,他不相信梦与幻想,他知道现实是什么样子的。但他爱人类,他对人类充满希望。他也是很暴躁的人,学生都怕他。如果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他就一定会责备他们,但这是出于关心,他不能接受人们浪费自己的生命。就如看到别人溺水他一定会呐喊不要放弃。
笔者: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中经常会出现一个神秘人,他们默默注视着人类发生的一切,似乎是冷漠的,又似乎是警惕的忧虑的。我很想知道,您如何看待这些神秘人?
扎努西:我觉得他是一个象征和隐喻(metaphor),而不是讽喻(allegory)。它没有一个确切的意义,也不能理解为命运、死亡、上帝派来的人、天使等。他只是一个超自然的人物,能让我们想起生活的超自然方面,但你无法说出他具体是什么。基耶斯洛夫斯基虽然不喜欢提到玄学(metaphysics),但很坚持这个人物的存在。
笔者:1996年,基耶斯洛夫斯基因心脏病英年早逝,他的离开对您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扎努西: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我还和他见面。他的心脏非常不好,因为他每天抽太多的烟。我一直建议他做心脏移植,但是他说他不愿意,想想他必须要在电视机旁等着一个人死去,在这个人死后使用他的心脏,他就会觉得这是一件令他鄙视自己的事情。他想做一个更为容易的手术,但是医生们觉得这个手术实在是没有必要,因为他的心脏已经太差,做这个手术风险非常大。但最后因为他的坚持,这个万万不该做的手术还是做了。他说,如果生活仍然需要我,那么我就会活下来;如果不需要,我就会死去。这让我印象十分深刻。
作者简介:任众,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2012级戏剧与影视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