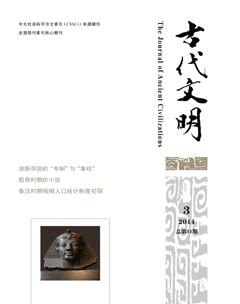明清时代南海疍民的分层流动与社会身份重构
张朔人
明清时代南海疍民的分层流动与社会身份重构
张朔人
明清交替之际,南海疍民为摆脱自身的“贱民”命运,进行身份重构,琼州海峡北部水域疍民多采取武力方式,而其南部地区疍民多以诉讼方式进行。因所采取的方式不尽相同,在国家政策、地方习俗和疍民之间长时段的互动过程中,该群体产生明显的分层,海北的疍民身份日益固化,海南疍民则向“编户齐民”方向发展。
疍民;身份重构;分层流动
自明太祖“设立蛋户、渔户、教坊等名色,禁锢敌国大臣之子孙妻女,不与齐民齿”的规定之后,1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凤阳人乞食之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涵芬楼秘笈第2集第5种,第4页。按:疍是一个以舟为室,视水为陆,浮生江海的人群,主要活动范围从福建至东南亚沿海一带。史料指称这一人群的称呼有多种:蛋、蜑、疍、龙户、獭家、科题(曲题或裸题)、卢亭、卢余等。本文引文使用原文献所用称呼,论述则统一使用“疍”字。疍民群体随之进入了社会最底层。因历史的惯性,即便在王朝鼎革之际,其贱民身份也难以摆脱。然而,从地缘的视角入手,疍民因地域不同,其身份也产生明显差异:以琼州海峡来划分,该族群在处理自身权益问题时,海峡以北,多以武力方式体现;而海南的疍民,多选择诉讼手段解决。疍民族群以不同的方式与王朝政治进行互动,从而使得其身份体现出明显的分层流动:海峡以北地区,贱民身份日益固化,而海南水域则开始向齐民化方向转变。明代海上不靖,倭寇、海盗日益猖獗,疍民的海上生活遭到强烈冲击而生计日蹙。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这一群体开始裂变,其中有部分人助纣为虐,成为官府的对立面。最早发现这一问题的是明初广东都指挥同知花茂:“广东南边大海,奸宄出没,东莞、笋冈诸县逋逃蜑户,附居海岛,遇官军则诡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寇盗。飘忽不常,难于讯诘。不若籍以为兵,庶便约束。”2张廷玉等:《明史》卷134,《花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908—3909页。这一提议,为朱元璋所认同。花茂的言论是对整个广东地区疍民而言的,其目的是把良莠不齐的南海疍民纳入朝廷水师体系之中。明代中期以前,疍民构乱、危害地方的记载,并不多见。以河泊所之下的“编户立长”为日常管理手段,“供鱼课”成为疍民的常态化生活;而“籍以为兵”作为对其管理的重要补充。如此,疍民基层社会由军、民两个系统构成,它们之间相辅相成,运行相对平稳。而晚明时期,海南海北地区则出现另一幅景象。
一、晚明海北疍民改变身份的武力诉求
(一)珠池之禁与苏观升、周才雄之乱
明代粤西雷、廉二府附近海域共有珠池八处:“廉州之池七,曰青莺、曰杨梅、曰乌坭、曰白沙、曰平江、曰断望、曰海渚沙;雷州之池一,曰乐民”。因过度采珠,珠产日益减少。为了“取之有节、用之有礼、禁之有法”,弘治时期规定“十年一采”。1戴璟:《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30,《珠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8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505页。然而,嘉靖时期在采珠周期上发生了较大的突破。嘉靖八年(1529年),提督两广侍郎林富就此上疏称:
……自天顺年间采后,至弘治十二年方采,珠已成老,故得之颇多;至正德九年又采,珠亦半老,故得之稍多;至嘉靖五年又采,珠尚嫩小,故得之甚少;今去前采仅二年,珠尚未生,恐少亦不可得矣。(嘉靖)五年之役,病死、溺死者五十余人,而得珠仅八千八十余两,说者谓“以人命易珠”。今兹之役,恐虽易以人命,珠亦不可得矣。今岭之东、西,所在饥民告急,申诉纷纷,盗贼乘间窃发,乃复以采珠坐派府县,恐民愈穷、敛愈急,将至无所措其手足,而意外之变生矣。2《明世宗实录》卷104,嘉靖八年八月乙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嘉靖帝对此置若罔闻,命“如前旨,采办进用,无得迟误。”3《明世宗实录》卷104,嘉靖八年八月乙丑。资料记载,嘉靖五年(1526年)、九年(1530年)、十二年(1533年),皆入池采珠。4戴璟:《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30,《珠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89册,第506页。朝廷在无度采珠的同时,以重兵把守,防止疍户侵犯“禁池”。这些举措,严重地影响了采珠疍民的生产和生活,私自采珠无望,同来此地购买珍珠的“番商”交易也随之中止。
更为重要的是,“诸蛋户廪廪于子钱日益增,恐嗣岁必无所得于豪贾”。也就是说,疍民无法及时归还从富商处所借的高利贷。因为生计日蹙,一些疍民铤而走险,“聚党数千人,数出劫雷、廉之间,萧然苦兵矣”。5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3,《蛋贼苏观升周才雄粱本豪传》,《续修四库全书》第43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8—240页。
《万历武功录》详细记载了疍户苏观升、周才雄活动于珠池周边海域,据乌兔埠,建立军事基地,以对抗官兵的情况。乌兔埠,“北枕高山,南濒大海”,为疍民聚集之地,属明高州府石城县管辖。6曹志遇:(万历)《高州府志》卷7,《纪事》,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11—112页。该志曰:“(石城)县原于附海地方设乌兔、多浪、厐村三埠,蛋民口居之,采鱼办课”。万历七年(1579年),苏、周指使木工伐木于此处建屋,“令部曲相保,为堑垒,木樵校联不绝,开东西二大门。其一门面大海,往来幸得通,它门皆重封”,“聚党千余人,治舳舻三十余艘”,势力盛极一时。他们以夜间巡逻、厚赏鼓动人心等方式,与政府军队对抗。经过二年的集聚,万历九年,侵犯永安所附近的断州,雷、廉、高三州官兵合力围剿,先后生擒苏观升、周才雄等400余人。7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3,《蛋贼苏观升周才雄粱本豪传》,《续修四库全书》第436册,第238—240页。此役后,乌兔埠疍民军事堡垒不复存在,疍民在珠池为乱,渐趋平息。
(二)梁本豪勾结倭寇危害东粤
海寇曾一本,“横行闽、广间”,8张廷玉等:《明史》卷212, 《李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622页。称雄海上。隆庆三年(1569年)六月,穆宗命刘焘兼兵部右侍郎,“往督三省师,又调大猷率兵会闽广夹剿”。9《明穆宗实录》卷36,隆庆三年八月癸丑。曾氏力量被摧毁之后,其余党梁本豪等“奉头鼠窜入于海”,纠结梁本明、马国隆、马本高等14支疍人的水上力量,人数达千余人。“专往来波罗、香山、三水东西海,日夜习水战”,“飘忽无常所”。梁氏为了达到其“尽灭官兵”的计划而勾结倭寇,10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3,《蛋贼苏观升周才雄粱本豪传》,《续修四库全书》第436册,第240页。万历十年(1582年),倭寇犯广东,便是“为蛋贼粱本豪勾引”,其势猖獗。11张廷玉等:《明史》卷322,《日本传》,第8356—8357页。
由于政府征税太苛,“海上无以为资”,大量造船之人放弃旧业,而“往从倭与蛋”,12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3,《蛋贼苏观升周才雄粱本豪传》,《续修四库全书》第436册,第241页。梁氏水上势力甚众。鉴于“蛋贼梁本豪复聚众挟倭焚剽郡邑,流毒已久”,万历十年六月,总督尚书陈瑞率兵全面征剿,“斩本豪,后先擒斩倭贼一千六百有奇,犁沉倭船、蛋艇二百余只,歼余孽殆尽”。13《明神宗实录》卷130,万历十年十一月丁巳。经历此次大征,梁氏势力消失殆尽。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没有海北疍民为乱的记载。
二、海南疍民的生存状况及其身份转型
明清时期,海南称作琼州府,隶属于广东。所以,中央层面政策设计中的“广东”一词,是包括琼州府的。与海北疍民通过武力来改变身份做法不同,海南疍民多以诉讼的方式来处理该人群与官、民及其内部的纷争。
(一)偶发状态中的武力诉求
明清时期岛内府州县志所呈现的结果,本岛疍民亦有助纣为虐抑或是武装起事之举。总体来看,其个案特征明显,规模不大,且多发生在清代中后期。
明隆庆元年(1567年)十二月晦(三十日——引者注),儋州疍民是否为害乡村,方志记载多有抵牾。1曾邦泰:(万历)《儋州志》地集《海寇》曰:“隆庆元年十二月晦,番寇劫乡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18页;而与此差不多同时的欧阳璨(万历)《琼州府志》卷8《海寇》未见对此事的记载。入清之后,该条记录被改为“隆庆元年十二月晦,蛋寇掠乡村”,见韩祐重:(康熙)《儋州志》卷2,《海寇》,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197页。韩氏的修改为张岳崧的(道光)《琼州府志》卷19《海黎志》及王国宪(民国)《儋县志》卷八《海寇》所转引,从而成为该地疍民危害乡村的主要证据。从明代儋州地方志来看,清代疍民为寇的结论难以成立。
清嘉庆三年(1798年)五月,“蜑户方世建、方维富等奉檄招安”。2张岳崧:(道光)《琼州府志》卷19,《海黎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433页。道光三十年(1850年)三月二十七夜,“贼劫海口钱铺数处,官兵知之不追,贼遁去”。海贼上岸劫钱之事,时议“蜑家水手引海匪为之”。3王国宪:(民国)《琼山县志》卷11,《海防志》,上海:上海书店、成都:巴蜀书社、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03页。
显然,“奉檄招安”的方世建、方维富等疍民,有着明显的反政府倾向。其规模和持续时间无法判定,可以肯定的是无法与海北相匹敌,这一推论从方志中隐约可见。至于海口钱铺被劫一事,官府并未采信当时议论,自然也就没有追究疍民之责任,据此可知,其危害程度在可控范围内。
(二)诉讼成为其维权的常态手段
政治生态的急剧恶化,环海而居的族群生存难以为继,交纳渔课之定额并没有因之而豁免,诉讼成为海南疍民处理其与官府、州民之间的重要手段。
1,儋州疍民诉讼案例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儋州政府“岁派四差”在落实过程中,就“渔船”、“木排”、“硐口”三项杂税银60两6钱的征收问题上,疍民许柳甫赴院道,认为:此三项杂税“告压通州”;而通州士民则“告推蛋户”,双方之间展开诉讼。后经过知州曾邦泰“减银十两,以商船税抽补”的裁断,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实行,为期六年的“缠讼”才告一段落。
无独有偶,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儋州疍民生员不认可州政府“凡蛋籍人丁有充员役,止优免在州粮,不优免在州丁”之规定。疍籍生员钟元声、周翊运等赴提学道副使姚履素告免所中丁课,为姚氏所准批。知州曾邦泰,对此作出如下调整:
本州知州曾(邦泰)审将蛋籍生员除免州中米二石,又再免所课米二石,折作二丁。如民籍充员役免丁之数。免去课银,以通所课米,通融均派,充额随据。各蛋唯唯、佥同,以励蛋家将来子弟。申祥批允,就四十四年为始。4曾邦泰:(万历)《儋州志》天集,《食货志》,第53—54页。
上述二则史料表明,该地疍民通过法律的途径,与“通州士民”和州政府间分别展开诉讼,最终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
2,崖州疍民间的海面纷争
“缘州属沿海东至赤岭与陵水交界,西至黄流莺歌与感恩接壤”,清代早期,崖州(即今三亚市)疍户主要集中在所三亚里、保平里、望楼里等地。根据规定,本州疍户需要交纳鱼课银162两余,上述三里分别承担:61两余、50两余、42两余;鱼课米584石余,保平、望楼二里,“载米二百五十石”,黄流、莺歌二湾,“分载米二十石余”,按户征输。“自深沟至黄流海面仅一百四十里,三亚里载米一百六十石,内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间,抽米饷于赤岭、琊琅等处,仅米一十石余,亦按户征输”;自红岭至与陵水交界的赤岭海面,“共一百七十里,其番坊绝米,已有燕菜足供输纳”。若以东西海面米石相较,显然西面“米多海少”,所以居于州西保平里等疍户对此颇有微词,并试图通过扩大其海域来加以改变。乾隆十八年(1753年),保平里籍的疍民徐翰珪等,与所三亚里蒲儒嵩(以捕鱼为业的回民)等互控海面一案。《正堂禁碑》道出了其中原委:
其海面虽无界址,而各里蛋户向来按照各埠采捕输纳,或有异邑小艇,呈请给照在其处海面采捕,即帮照其处课粮该管,现该完纳,相沿已久。兹保平里徐翰珪住居藤桥,欲将藤桥海面归贴保平,因以海面宽窄悬殊,具控前来。1引文取自崖州州府乾隆十八年《正堂禁碑》,该碑现存三亚市凤凰镇回辉村清真寺院内。
以徐翰珪为代表的保平里之疍民,以占领藤桥海面之名,来行“归贴保平”之实,同时对所三亚里疍户的水上作业区形成东西夹击之势,从而为蒲儒嵩等所反对,此乃双方诉讼的主要原因。州官以“相沿已久”为辞,拒绝了保平方面的要求,作出相应的裁决,并“勒石”以示谕各方:
嗣后务宜照各在本埠附近海面采捕,朝出暮归,不得多带米粮违禁远出。或有异籍蛋户到境采捕,该埠长俱须查明,呈请给照帮课,亦不得私行越界强占网步滋事。如敢抗违,许该埠长指名扭禀,按事究治。2引文取自崖州州府乾隆十八年《正堂禁碑》。
上则史料表明,以捕鱼为生的行业间因海面扩张一事,因双方采取较为理性的问题处理方式——听从州官裁决,而避免了武装械斗。
3,琼山县疍民内部纷争及其解决
博茂图沙上村与下东营村分别位于濒临琼州海峡的沙上港和下东营港(现为海口市灵山镇辖地),因渔汛多寡,自光绪三年(1877年)至光绪五年(1879年),二处疍民为如何分摊纳额税银3两6钱之事,展开了为期3年的诉讼。
沙上村的陈奇昌等6位联名呈文曰:近年以来,屡被下东营村林香圃等所“索诈”,并坚持本港疍民延续已久的上纳税银之数。下东营港的林香圃等认为:
伊下东营埠近年渔汛淡薄,仅存桴船二十八号,而沙上村渔汛近年甚旺,添有拖风船二十余对之多,是以断令:沙上村每年封贴四十千文与下东营,以为添纳税饷之需。3引文取自琼山县衙光绪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告示》,该告示碑现存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大王庙内。
沙上村认为,林氏所报告的下东营渔船数量及生产情况严重不实,经县衙差人调查,“下东营各港共有桴船九十余号,连牛船、小网等船,共计百十余号。统计每年所收二百千有奇,尽数完纳”。据此,琼山县对沙上村作出如下判决:“沙上村每年仍照前交钱一十六千文与下东营,以符三两六钱之税,以后永以为例,不得加增。”对于造成此次诉讼的肇事方——下东营村,“合行给示晓谕”:
下东营埠蛋户人等知悉,即便遵照堂断,嗣后博茂图沙上港埠各船只,每年仍照前交钱一十六千文,与下东营收纳,以符三两六钱之税,永为定章,不得逞强加索,滋事到斡重咎,各宜凛遵毋违。4引文取自琼山县衙光绪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告示》。
三、海北、海南疍民身份的分层流动
晚明海北疍民构乱给周边地区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明朝的两次军事征剿,给疍民的教训也十分惨痛。随着朝代的鼎革和时间的推移,其影响从两个方面逐步显现:一是,被武力镇压的疍民,不得不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而重操旧业,缴税纳课;二是,岸上居民对其有所戒备,这在番禺人屈大均在康熙年间所著《广东新语》中有所体现。5参看屈大均:《广东新语》卷7,《人语·蛋家贼》,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0页。
(一)清初海北疍民“贱民”身份的确定
清代雍正、乾隆两朝是海北疍民社会身份发生较大变化的时期。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雍正帝发布上谕:
闻粤东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种名为蜑户。即猺蛮之类。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通省河路俱有蜑船,生齿繁多,不可数计。粤民视蜑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蜑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局蹐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深可悯恻。蜑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且彼输纳鱼课,与齐民一体,安得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而使之飘荡靡宁乎。6《清世宗实录》卷81,雍正七年五月壬申,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从雍正诏旨中可见,明太祖朱元璋将疍民规定为“贱”民的划定,在入清近百年之际,依然严重影响者疍民的社会处境与生存实况。雍正帝则考虑改变此种状况,为此责令广东督抚,并转饬有司,通行晓谕:
凡无力之蜑户,听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栖身者,准其在于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以便稽查。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陵驱逐。并令有司劝谕蜑户,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以副朕一视同仁之至意。1《清世宗实录》卷81,雍正七年五月壬申。
这应是疍民社会身份改变的一个重要节点。
其后,在乾隆时期又有乾隆帝的“报捐应试”诏。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礼部会同户部议准陕西学政刘墫“山陕等省乐户丐户请定禁例”之奏折,指出:已经“改业为良之乐户、丐户”,“不便阻其向上之路,应请以报官改业之人为始,下逮四世本族亲支,皆系清白自守,方准报捐应试”。朝廷对于山陕等省“贱民”进入科考相关规定,推及“广东之蜑户、浙江之九姓渔户及各省”,指出:
凡有似此者,悉令该地方照此办理。但此等甫经改业之户,惟不准遽行报捐应试。至于耕读工商,业已为良,应悉从其便。如有世豪土棍,籍端欺压讹诈者,该地方官应乃严行查禁惩治,以儆刁风、以安良善。2《钦定皇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18—419页。
就其内容而言,广东疍民“报捐应试”的前提条件是:自其上辈“改业为良”始,至以下四代“清白自守”。按照代际传承20年为一周期计算,五代为100年,如果从雍正七年“开豁为良”算起,至少到1829年,疍民才有“报捐应试”之可能,也就是说其实际效力是在乾隆、嘉庆之后的道光时期了。显然,这一政策设计对于疍民身份改变,无法产生太大影响。
处在博弈双方风尖浪口的疍民,晚明“武装起事”式的冲动性格已消失殆尽。虽然清代早期国家层面的政策设计,对于海北地区疍民多有顾及,但是地方习俗的强烈抵抗和政策的不可操作性,使得疍民彻底沦为“贱民”身份,并且逐步固化。这一情况,到20世纪20年代才有所改变。对此,陈序经先生《疍民的研究》的相关章节,有着具体的阐述。3陈序经:《疍民的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92—145页。
(二)海南疍民的身份转变
1,疍民向上流动趋势
至迟在明正德年间,沿海地方以“乡都里图”来管束疍民的制度开始运行,行政关系上则隶属于河泊所,疍户需向所在地的河泊所交纳渔课。如:崖州,正德时期,疍民聚集在保平、望楼、番坊、大蛋四里;万历后期,保平、望楼、番坊以及取代“大蛋里”的“所三亚里”成为疍民的聚集地,其行政关系仍旧;4唐胄:(正德)《琼台志》卷12,《乡都》,《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60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欧阳璨:(万历)《琼州府志》卷3,《地理志·乡都》,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67页。北部澄迈,景泰间设疍图,采鱼办课。这种将疍民纳入国家编户的努力,在清初的澄迈开始出现新变化:“近因图下买有司田多,始告立民疍籍,米照当差,丁仍免科,民户有不均之叹。”5丁斗柄:(康熙)《澄迈县志》卷1,《舆图志·乡都》,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26页。民疍籍的设置,缘于疍户购买有司之田,此乃海南疍民纳入编户的最早记录。尽管在全岛仅属个案,但事件本身表明,政府对疍民置产置业的态度产生了极大的转变,即:从此前默许转变为制度层面的确认。不仅如此,对待新入的民疍籍,地方政府继续沿袭前朝“米照当差,丁仍免科”的政策,比起民户有着明显的优惠,致使一般民众有“不均之叹”。当然,这与是时海北疍民之处境,有着霄壤之别。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儋州“蛋籍生员”钟元声、周翊运等,赴提学道副使姚履素告免所中丁课一事,前文有所述及。知州曾邦泰“将蛋籍生员除免州中米二石,又再免所课米二石,折作二丁”的判文表明,有一定数量的“蛋籍生员”存在,这就是说,儒家教育开始向疍民群体推广。入清之后,“亦有读书列庠士者”,6樊庶:(康熙)《临高县志》卷2,《疆域志·民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48页。清代的“庠士”,实乃“秀才”之别称。毫无疑问,与儋州毗邻临高县疍民教育有着进一步的发展。
2,社会习俗与疍民间的关系
明初,琼山北部滨海一带(即今海口市海甸溪两岸)疍民女性,参加一种叫做“纺场”的晚间户外活动。唐胄对此做过记载:“时郡俗,村落盐、蛋、小民家女妇,多于月明中聚纺织,与男子歌答为戏。凡龙岐、二水、大英、白沙、海田诸处,俱有之,号曰纺场”。正统间吏部尚书王直年轻时曾游遍纺场各地,并为之撰《纺场赋》。这表明当时琼山疍民女性为主体的“纺场”,得到普遍的社会认可。正统时期,知府陈莹对之加以整饬,“余韵犹存。至成化中,始无矣”。1唐胄:(正德)《琼台志》卷42,《杂事》,《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61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清代早期的澄迈县志记载了民、疍共同赛龙舟之事。“海边蛋户与近河民,俗以木刻龙首尾祀庙中,俱于是日(农历四月八日——引者注)赴庙绘饰,以俟端阳赛会”。这种迹象表明,疍民为本地的社会习俗所认同,排斥、歧视的案例鲜有发生。
3,疍民的贫富分化
大约在明代晚期,在澄迈疍民群体中出现了“渔人者”和“渔于人者”,二者间的雇佣关系开始显现:
明时蛋户以海为肆,以渔为业。鱼之为利溥,课之宜矣。然有渔人者,有渔于人者。巨舰小艇,募穷户为之役,扬帆海澳之中,计岁所获可当中人十家产,此渔人者也。彼渔于人者,赁一叶之舟,衣不蔽肤,沿岸而网,得鱼不易一饱,而课额已难取盈。2丁斗柄:(康熙)《澄迈县志》卷2,《食货志·渔课》,第92页。
在海南岛东北部的文昌,疍民受雇佣大约发生在明后期。晚明文昌海域的海产品“琼枝菜”,因其“岁利亚于槟榔”,利益所在,引起垄断,万历府志对此作如下按语:“琼利榔椰之外,琼芝(即琼枝菜)次之。然巨姓营穴,利不及民。且封山界海,兼并易生,讼无宁日。”3欧阳璨:(万历)《琼州府志》卷3,《地理志·土产上·菜属》,第73页。巨姓通过“封山界海”,通过雇佣疍民采集琼枝菜,以达到其追求财富之目的。因王朝兴替,这一关系出现断层,至康熙海上开禁之后,又再次兴起。《康熙文昌县志》道出了其中的蹊跷:海禁使得鱼课“课米无征”,地方官只好用“摊入通县苗米融赔”的方式完纳。开禁之后:
渔蛋迁移,船只稀少,一时不能照额领课,于是沿海居民认管海面,报领课米,私收渔船租利,是为海主。康熙五十六年,奉督部院杨禁革名色,恐有绅衿、地棍包揽、勒索,饬令沿海州县额征课米,各按属内渔船征收。4马日炳:(康熙)《文昌县志》卷3,《赋役志·鱼课》,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85—86页。
清代文昌“海主”,存在有30多年时间。当然,这种“沿海居民”多为地方势力组成,他们分割海面,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私收渔船”、通过雇佣关系来进行水上作业。世代从事业渔、又无船只的疍民,生活日益窘迫。
即便是在海禁时期,疍户所交纳的渔课“仍无失额”,5焦映汉:(康熙)《琼州府志》卷3,《赋役志·鱼课》,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252页。禁海使得疍民生活窘迫。“矧今禁海,界内小河所得有限,而课尤不改额,毋论渔于人者不能竭手足之力以输供,即渔人者亦无由资采取之利以完正,蛋其重困也夫。”6丁斗柄:(康熙)《澄迈县志》卷2,《食货志·渔课》,第92页无论“渔人者”抑或“渔于人者”,皆陷于生活困境。澄迈如此,临高亦然:“康熙元年,申严海禁,滨海蛋户资生无术,日就死亡,全额俱无可问。今弛禁,流离渐复。自康熙三十五年改征全额,然二三孑子遗,亦艰苦甚矣。”7樊庶:(康熙)《临高县志》卷4,《户役志·鱼盐》,第84页。由此可知聚集在本岛周边海域生活的疍民,其群体经济状况整体下滑。
4,地方政府的干预
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广东巡抚朱弘祚的奏疏,道出了地方经济之残破:“高州府属吴川县,琼州府属临高、澄迈二县,自康熙十八年起至二十八年止,未完地丁银一十二万八千六百两有奇,实系户口稀少、田亩荒芜所致,应请尽行豁免。”8《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三十年四月辛巳。以摊入通州、县“苗米融赔”来完成渔课米,在本岛已有先例,但这是非常时期的临时举措。疍民的集体沉沦,无法保证渔课米的按时、足额交纳,再行摊派将不利于地方经济恢复和发展,更不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有兹于此,各地政府纷纷采取措施,来改变疍民的生产生活。
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人口统计,儋州疍民共有2063丁,占该州成丁人口10151的20%,为岛内疍民人口数字最多之地。该州疍民集中在新英都一二三图,旧有“船只印牌及木牌册结”等“陋规银”120两,连续征收,疍民病之。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韩祐为本州知州,着手裁革,“永为定例”。韩氏因之而赢得“蛋民颂德”。1韩祐:(康熙)《儋州志》卷1,《食货志·田赋》,第77、89页。
清初海禁与开海,使得琼州海峡周边的疍户一片萧条,其对本岛南部崖州影响似乎并不太大,该片海域相对宁静。于是,一定数量的“异籍蛋户”开始移入本地作业,这可能是临高村人(位于今三亚市保平港镇)落籍崖州较为合理的解释。崖州,随之成为疍民重要的聚集地。在前文所述的《正堂禁碑》中可知,“异籍蛋户到境采捕,该埠长俱须查明,呈请给照帮课”。反映出地方政府对于“异籍蛋户”通过“给照”、“帮课”的方式,予以合法身份和生计出路,以避免“异籍”与本土之间的海上纠纷。
四、余论
南海疍民为了摆脱明太祖朱元璋所规定的“不与齐民齿”的“贱民”命运,自明中叶至清代康乾时期,进行了长达近两个多世纪的身份重构。其结果是,海北地区上岸流动的通道被切断,水居成为固定的生活方式,其“贱民”身份随之日益固化;而海南地区,“民蛋籍”、“庠士”等全新现象不时涌现,其向上流动的通道较为通畅,并逐步向“编户齐民”方向发展。究竟何种原因导致了南北的差异?
在海北地区,因为疍民的武力重构身份之举,对地方危害难以磨灭,是故地方习俗对疍民颇不认同。
广中之盗,患在散而不在聚,患在无巢穴者,而不在有巢穴者。有巢穴者之盗少,而无巢穴者之盗多,则蛋家其一类也。蛋家本鲸鲵之族,其性嗜杀。彼其大艟小出没波涛,江海之水道多歧,而罟朋之分合不测,又与水陆诸凶渠相为连结。2屈大均:《广东新语》卷7,《人语·蛋家贼》,第250页。
屈大均,这位致力于反清活动的前朝遗老,其文字足以代表是时文人士大夫对于疍民的基本认知。屈氏的文章中,也曾描述疍民身份的变化,如在征渔课时,“亦皆以民视之”,此外“诸蛋亦渐知书”、“有居陆成村者,广城西周墩、林墩是也”。但是,因“其性凶善盗,多为水乡祸害”之故,“良家不与通婚”。3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8,《舟语·蛋家艇》,第485—486页。
此外,也有以诉讼作为手段来解决问题者。乾隆八年(1743年),西江疍民就地方豪衿地棍霸占鱼埠一事,将对方诉讼至高要县。经知县裁决鱼埠归疍民经营,并立《鱼埠归蛋民资生告示碑》,碑文记录了诉讼经过、处置措施。4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水电局编:《端州文史资料》(水利专辑),肇庆: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厂,1990年,第89—94页。
屈氏笔下疍民身份的变化及高要县疍民诉讼案件,毫无疑问,是疍民向上流动的重要表现。然而,海北地方疍民分布广泛,且人口众多。对于其整体来说,这些现象仅具有个案色彩,且并不具有联系性。在地方习俗的强烈抵制下,其“贱民”身份日益固化。
与之截然相反,明清时期,海南疍民以诉讼作为维权的主要手段,来解决族群内部、与地方习俗及官府之间的矛盾。获得胜诉的疍民群体,与其教育水平的提高有着一定的关系。海南疍民在宋代“北粮南运”、元代“疍民军籍”以及承担本岛与内地联系5张朔人:《海南疍民问题研究》,《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等重大历史事件上,一直积极参与。明清时期,该群内出现的诸多向上流动的现象,以及社会习俗对其广泛认同等,表明其贱民身份已荡然无存,他们通过自身努力取得与编户齐民同等地位,“蛋民”仅是其职业的代称而已。这也表明,在海南这一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中,社会阶层的划定,同内地的刚性结构相比,显现出较大的弹性。
[作者张朔人(1966年—),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海南,海口,570228]
(责任编辑:刘波)
2014年1月20日]
* 本文为海南省教育厅课题“‘王化’与‘梗化’——海南历史研究”(项目批号:Hjsk2011-1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