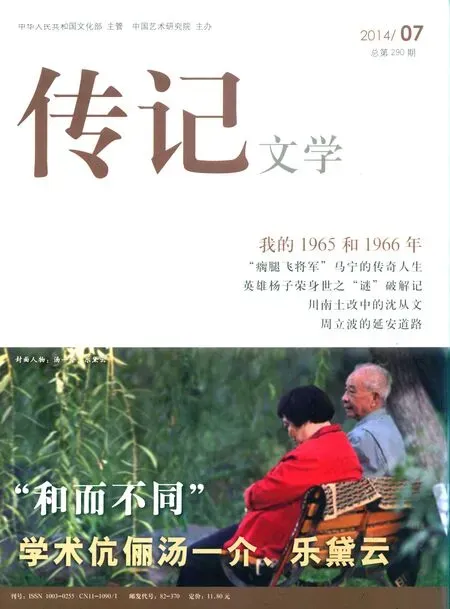我的1965和1966年(上)
田润民
我的1965和1966年(上)
田润民
美好而短暂的一年
1965年7月中旬的一天,大队书记姚占魁笑吟吟地走进我家,看着母亲正在院子里缝被子,他问道:“三姨,你知道了?”母亲一头雾水,不知他此话何意。姚书记接着说:“大热天,你缝被子,看来是为润民做准备的。”母亲说:“是啊,润民准备到穆家岭去包山(指种地),我给他做准备哩!”“是到北京去包山哩!” “润民考上大学了!”姚书记绕了半天弯子,这才把一个好消息说了出来。原来,高考的结果出来以后,我所在的旬邑县中学首先打电话通知考生所在的生产大队,姚书记是获知这一好消息的第一人。当我拿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入学录取通知书以后,把它看了又看,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这个厚厚的大信封将改变我的人生命运。我是当年我们那个偏僻而闭塞的陕西旬邑县考进北京的唯一一个大学生,全县轰动,老师、同学都为我高兴。8月的一天,父亲赶着小毛驴驮着行李把我送到县城,第二天坐汽车赶到西安,接着坐火车前往北京报到。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坐火车,感到既新鲜又好奇。那火车车厢非常整洁,不那么拥挤。和蔼可亲的列车员一会儿用墩布拖地,一会儿又给乘客端茶倒水,其中一位女列车员胸前佩带的是“唐山铁道学院”的校徽,热情,文静而又彬彬有礼。几十年来我乘坐过无数次火车,似乎再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周到热情的服务。
同行的还有一位邻县的同学,几个星期以前,我们同乘一辆汽车到乾县参加高考,现在又同乘一列火车到同一个大学去报到。后来分配工作时又被分到同一个系统(第三机械工业部),世上难得有这么巧的事!现在,只见他头上戴一顶陕西农民夏天常戴的大草帽,背着个铺盖卷,躬着腰上了火车,然后,把铺盖卷往地上一放,坐在上面,就这样在铺盖卷上坐了一路,不时地还用那大草帽扇风。那模样真像一个外出打工的农民(他叫尚三续,入学以后被分配到法语系);我的形象比他强不了多少,当时上身穿一件我母亲亲手缝制的白色粗布对襟衫,下身是一条蓝裤子,脚上穿的是我母亲做的黑布千层底鞋,和那位同学所不同的只是没有戴草帽,也没有坐在铺盖卷上。
火车从西安出发,开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晚上六七点钟的样子,终于到了北京。火车到站那一刹那,我又激动又紧张,激动是终于到了伟大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了,紧张的是我能不能找到要去的学校。当我走出车厢时,一个醒目的大牌子闪入我的眼帘,上面写着“北京外国语学院新生接待站”,我喜出望外,赶紧朝那块牌子走去,并自我介绍道:“我是来报到的新生。”那举牌子的两个校友十分热情地帮我拿行李,领我出站,其中一个叫全振福,陕西洋县人;此时此地,遇到老乡,感到格外亲切。前几年,我在首都机场还遇到过他,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都是快60岁的人了,在茫茫人海中,彼此相见,一眼还能认出来。可见当初新生接待站给人留下的印象之深。

本文作者大学入学照
一辆敞篷解放牌大卡车把我们刚到的几个新生送到位于北京西郊魏公村的外语学院。虽然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却毫无倦意,站在这敞篷汽车上贪婪地欣赏着沿路北京的夜景。司机也善解人意,特意路过天安门,让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新生一下火车就能看到这座雄伟而充满神秘色彩的建筑物:这就是毛主席经常出现的那个地方,乡下的农民误以为他就住在那里呢。今天我亲眼看见了它,心里禁不住问:“我们那个偏僻小县有几个人到过北京、看见过天安门?”接着是笔直而宽阔的长安街,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我只觉得眼睛不够使。到了学校,英语系负责接待我们,当晚把我们安排在5号楼439室;从此我在这间小屋子里度过了三年五个月的大学生活。
第二天,负责接待我们的英语系二年级张少平等同学带我们到苏州街那个唯一的小商店买了脸盆、毛巾、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具,又到生活科领了饭票,还陪着我们到校园走了走,熟悉周围的环境。外语学院分为东西两院;东院的南面从西往东1、2、3号楼,是部分教师、干部、工人的宿舍楼;北面从西往东数,4号楼是俄语系、东欧语系、亚非语系的学生宿舍楼,5号楼是英语系学生宿舍楼,6号楼是法语系和西班牙语系学生宿舍楼;宿舍楼高达五层,顶部为中式结构大屋檐,排水、隔热效果好,是首都高校中少有的中西结合的建筑,据说它出自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50年代的设计思想。两排宿舍楼中间、靠西朝东矗立着一座六层楼,是学院的主教学楼,是“北外”最高的建筑物,也是大屋顶,很气派。当年盖成以后周恩来总理曾登上顶层,俯瞰周围,发现它竟是北京西郊最高最漂亮的一座大楼,掌管着六亿人口家业的总理在赞叹它的雄伟壮观之余又不免有点心疼,批评道:一个大学盖这样阔气的大楼未免太奢侈了。令总理没有想到的是,十多年以后的“文革”中,以打倒他为目标的“六一六”红卫兵组织的总部就设在这座楼的顶层。
主教学楼前面是一片开阔地,这是学院的大操场,操场的正面有个用水泥砌的主席台,是全院开大会的地方,平时学生们在这里上体育课、锻炼身体。每个周末,大操场挂起银幕,放一次电影。大操场因为大、能容纳的人多,“文革”中成了“北外”最热闹的地方,在这里曾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陈毅副总理在这里讲过话,班禅大师在这里挨过斗,“北外”许多著名教授、学者、学院院长、书记在这里“坐过喷气式”,蒙受人格侮辱和身体摧残。与此同时,“文革”中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以及军宣队、工宣队的头头都曾在这里登台亮相,或辩论,或演讲,出尽了风头。1968年的10月份左右,工宣队进校后不久,在主席台的对面修建了一座绘有“毛主席去安源”画像的石碑;那是“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军宣队”)在“文革”中给“北外”留下的的纪念物,军、工宣传队和他们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曾强迫几乎所有的教授和一部分老干部每天在那里向伟大领袖“请罪”。这个石碑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见证,真应该永久保存。可惜,在那个反复无常、变化莫测的年月里,这类东西如同政治舞台上的角色一样,上得快,下得也快;“工宣队”所留下的这个水泥建筑物也不知什么时候被拿掉了。
大操场朝东的尽头是游泳池。游泳池靠操场这一头栽种着一些树,小树之间是一些用水泥砌成的小石桌和小石凳,还有几张简易乒乓球案。夏季,男女大学生们有的在这里打乒乓球,有的围坐在小石桌边谈天说地,不时地发出一阵快乐的笑声。游泳池里,那些从大城市来的同学在水中自由地穿梭,有几个女同学身穿三点式泳装站在高高的跳台上练习跳水。“游泳池”及其周围的小树林、石桌、石凳是当年许多男女学生经常幽会的地方,因此给许多校友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1968年12月初,北外校园合影(左二是作者,背景即那座绘有《毛主席去安源》画像的石碑)
在3号楼对面,也就是东院的东、南侧,坐落着两个饭厅,即“一饭厅”和“二饭厅”,“一饭厅”是教职员工食堂,“二饭厅”是学生食堂。外语学院的伙食在北京高校中因办得好曾经多次获奖。许多从农村来的大学生感觉在这里吃饭好像天天在过年。当时我们每人每个月伙食标准是15.5元,大部分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我每月助学金是18元,扣除伙食费剩余2.5元。人们形容大学生的生活是三个点:宿舍-教室-食堂,生活中好像没有更多需要花钱的地方,助学金基本够用。每年家里的补贴不超过100元。
这两个饭厅本来是大家吃饭的地方,“文革”中却成为两派斗争的另一个热点,持不同观点的学生曾在这里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那些重要的大字报、大标语往往贴在“二饭厅”前面。在两个饭厅上面是学院的大礼堂,本是学院开大会、表演节目的场所,“文革”中成了仅次于大操场的开批判会、斗争会的地方。
出了学院西大门,穿过马路,是外语学院的西院。西院实际上是两个学院共用,一部分属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一部分属于北京语言学院(后来搬迁到原北京矿业学院即现在的地址,并改名为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院实际上是从“北外”原来的“留学生预备部”(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出国前学习外语)分出去的,后来增加了一个“来华部”(专为外国人教授汉语),两个部合在一起成为北京语言学院。“文革”中一张耸人听闻的大字报揭发说:“北京语言学院是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背着中央搞的‘第三外国语学院’,是为彭真搞政变培养外事人才的,是个没有‘户口’的黑学校。”起因是那位炙手可热的“文革”顾问康生在一次会议上听到“北京语言学院”这个名字时,反问道:“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个大学?”康生一句话把一个大学打成一个“黑学校”和“反党黑店”,这是那个年代为了整人所制造出来的诸多天方夜潭式奇闻中的一个。西院属于外语学院这一块主要有两座楼,一座是靠北的英语系教学楼,另一座是位于院中的学院院部办公大楼。在西北角,有两座当时专供外国留学生学习和住宿的楼,属于“禁区”,一般人很少进入。在西院的西南角,坐落着两座灰色的四层楼,那是学院一部分干部和教师的住宅楼,著名的教授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等就住在那里。从北面的语言学院留学生楼到南面的外语学院家属楼,从东面的院部办公楼一直到西面的围墙尽头,是一大片空地,当时用作操场。语言学院的学生和住在西院的教师、干部以及他们的家属经常在那里锻炼身体、散步、做游戏。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北外”密密匝匝的宿舍楼。
东、西两院原来分属两个不同的学院,东院原来叫“北京俄语学院”,西院叫“北京外国语学校”。北京俄语学院是50年代中苏关系处在“蜜月”时期建立起来的,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紧张,俄语人才需求减少,于是,俄语学院撤消,和西院的外语学校合并。两院合并对于外语人才的培养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没有想到,从此却为两院干部之间埋下了矛盾的火种,成为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干部之间互相争斗的历史根源,到了“文革”期间,这种历史上的纠葛和矛盾和“两条路线”挂在一起,演变成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所有这些,我们这些刚入校的新生当然一无所知。1965年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尤其展现在我们这些新生面前的,到处都是笑脸,老师是那么和蔼可亲,同学之间是那么友善,高年级同学把我们当小弟弟、小妹妹一样看待,生活上给予很多照顾。漫步在校园里,绿荫遮挡着炙热的阳光,鲜花吐着芳香,处处是琅琅读书声。女同学那鲜艳的花裙子和银铃般声音把校园装点得更加妩媚。“北外”女生的衣着打扮和天生丽质在首都高校中颇有名气,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住在6号楼有一位法语系女同学,长得细高个儿,瓜子脸,皮肤白皙,气质高雅,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一股古典美的气息,被称为林黛玉式的美女。尤其她夏天穿一件鲜艳的百褶裙,把她那苗条的身段和漂亮的脸庞衬托得更加美丽。她所住的6号楼对面是北京工业学院(现改为北京理工大学)的宿舍楼,中间只隔着一条马路。时间一久,不知是对面楼里哪位有心男子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突然发现了马路对面这座楼里竟然有这么一位美丽的女子,他隔着窗户看呀看,越看心里越激动,终于忍不住写了一封求爱信,并准确地观察好了“林黛玉”所在楼层和房间,穿过马路,亲自把信从门缝里塞进去。“林黛玉”当然不会答应这位冒失的求爱者,不仅如此,而且从此将窗帘拉了个严严实实。

教育部文件
入学以后,学院首先为我们安排了“新生入学教育”;主管教学的李棣华副院长给我们做报告。他简要地介绍了学院的情况:“北外”在校学生3000人左右,教职员工不到1000人,规模不算大,是一所全国重点文科大学。学校归外交部直属领导,毕业生大部分分配到外交部、外贸部、外经部以及其他外事部门。今年的新生是从参加高考的考生中经过严格的政审和平均分数在80分以上中挑选出来的。学院的教学设备是第一流的,有先进的电化教研室,平均每个班配有一台录音机;师资队伍也是第一流的,集中了全国外语界著名的学者、教授,还聘请有许多外国专家。“北外”还是全国外语院校中的“龙头老大”;其他外语院校都以“北外”的教材为样本,还经常派人来“取经”。不仅仅在全国,就是在亚洲,“北外”也是有名的,当时的蒙古和朝鲜派留学生在我们学院学习英语;这些虽然和我们一样是黄皮肤但衣着打扮、举止行为十分特殊的留学生就住在我们5号楼。外国人在英语非本国语言的国家学习英语,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十分罕见,足以说明“北外”英语教学水平之高。许国璋教授主编的英语教材不仅成为全国外语院校的权威教材,还被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等国翻译过去,成为他们本国的英语教材。
李院长在他的“新生入学教育”报告中还特意对北外设置专科一事做了说明。1964年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14国后,中央预测我国对外关系将有一个大的发展,而当时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人才缺口较大,满足不了需要。同时,毛主席1964年春节就教育问题有个讲话,大意是:教育要改革,学制要缩短。据此精神,外交部决定,1964年、1965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法语系、西班牙语系设立3年制专科。李院长强调说,设置3年制专科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合格的初级外交翻译人才,专科学生在3年内外语上课时间等于甚至超过5年本科生,因为专科学生不参加“四清”运动(本科学生必须到农村参加一年“四清”),课程设置只有3门:外语、政治、体育。李院长还强调说:3年制专科属于试验性质,如果不成功,仍恢复5年本科制。“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北外的专科试验中止,3年后,学生离校毕业,工资按照大专对待。1980年6月,国家教育部发文予以纠正,规定这两届3年制专科试验学生工资按本科大学生定级。
李院长给我们这些新生画了一幅多么美好而又令人向往的人生蓝图,使我们大家沉浸在幸福的憧憬之中!能在这样一个大学学习,我们是多么自豪!
不到一年,李院长本人连同他对我们所作的“入学教育报告”都受到了批判;他被打成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北外”的代表人物,运动一开始,就被院党委抛了出来。好在他在两院干部的矛盾中比较超脱,不久,被视作“死老虎”,虽然偶尔上台挨挨斗,但只是“配角”而已。运动后期,他不幸得了直肠癌,做了手术。有一次,我看见他拄着拐杖,沿着魏公村那条小路向学院东门缓缓地走去;李院长素以谨小慎微出名,胆子特别小;显然这场来势凶猛而疯狂的“文化大革命”给他精神上打击不小,加上疾病的折磨,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入学以后不久,几乎所有的新生都参加了1965年国庆节天安门仪仗队训练,另一部分同学则参加《东方红》大歌舞合唱队。仪仗队的训练十分辛苦,适值8月,正是北京最热的季节,烈日当头,把大地烤得抓一把土都烫手,我们每天顶着酷暑在大操场练习正步走,腿要求抬得一样高,队形要保持整齐划一。虽然辛苦,但一想到能见到毛主席,大家什么苦都能够忍受。10月1日那一天,当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天安门广场走过时,远远望去,看到的是城楼上影影绰绰模糊的人影,只能从位置上判断哪一位是毛主席的身影。如今,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那年北京市的西红柿既好吃又便宜,我们每人花了一角钱买了一大网兜,在天安门等候期间拿它既解馋,又解渴。
国庆节以后,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学习了。我所在的班是英语系一年级专科四班,共有13名同学,分别来自陕西、山西、安徽、辽宁、浙江五省。教我们班的老师是张文君、奚宝芬,1966年初,又增加了石成惠老师。我们这个年级的同学在中学学的是俄语,一点儿英语基础都没有,要从ABC开始。而这一年我们正好赶上学校实行教学改革,采用“听说领先”情景式教学方法,这个方法在上一年级已试行过,效果显著。因此,老师们热情很高,教课时十分投入、卖力。在教语音时,没有课本,老师要求每人买一面小镜子,先听老师的发音,然后模仿,对着镜子矫正口型。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同学,带着各自的地方口音,普通话还讲不好,学起英语来格外吃力,因此老师每堂课要用很多时间来纠正大家的发音。有时碰到某个难发的音,怎么学都学不会,老师怎么纠正都纠正不过来,有的看到其他同学都会了,而自己还卡在那里,心里别提多么难受。有的同学为了某个音发不好,急得掉下了眼泪,有的失去信心,怀疑自己是不是学习英语的料。好在老师并不歧视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一边鼓励,一边不厌其烦地纠正、辅导。“北外”的老师,或者说“北外”的传统,对语音的要求特别严格,要求学生发音一定要规范,绝对不能马虎。我们年级教研室主任夏祖奎老师是语音课专家,教一年级很有经验,他给我们讲大课时特别要求同学们重视语音,并强调说:“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门面,不要怕枯燥,要多练。”还举了他年轻时冬天在树底下练习发音时的情景,曾被人误以为是神经病。在课堂上,老师基本上不讲中文,逼着我们去听,同时逼着我们说一些简单的英语,还要求我们互相之间用英语对话。那情景,就像幼儿园的阿姨教小朋友学说话一样。在上大课(即每四个班或者全年级在一起上课)时,老师千方百计营造一个语言环境,徐静渊老师有一次上课带了个大书包,从里面拿出盒子、书、笔记本、镜子,等等,每拿出一件东西,就用英语问:“这是什么?”同时要求大家用英语回答。杨勋老师平时待人和气,又很幽默,他在课堂上给我们用英语表演坐公共汽车的情景。老师们还用英语排演过戏剧小品《半夜鸡叫》,夏祖奎老师扮演剧中的周扒皮。到了第二学期,我们还欣赏过赵家蟾和马元曦两位老师表演的英语戏剧小品《一百分不算满分》,她们两位都是英语系骨干教师,英语口语流利而纯正,其戏剧表演才能也令人叹服。赵老师后来调到外交部担任高级翻译,改革开放以后定居美国,自己开办了一个律师事务所。随着学习的进展,学习的内容和方式也不断增加和变化,如刚刚配成英文的电影《天山的红花》《女跳水员》等作为教学片首先给我们放映。焦裕禄的事迹被报道以后,马上被改写成为英语,由付丰贵老师给我们讲演。付老师也是“北外”培养出来的一名尖子人才,英语“字正腔圆”,其夫人吴璞是“又红又专”的典型,担任英语系党总支副书记,是院、系两级的后备干部。付老师用英语给我们讲焦裕录的事迹,十分投入,充满感情,讲着讲着,竟然哽咽起来。可惜这样一位人才,“文革”中其夫人含恨自杀,本人受到株连,最后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离开这个使他伤心的地方。英语系有一位英国老太太,名叫Margrate Turner,中文名字叫陈梅洁,当年50出头,讲一口纯正的“皇家英语”,她给我们上过大课。陈梅洁出生在中国,父亲是一位传教士,她本人终生未婚,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英语教学事业。“文革”前,她灌有很多英语教学唱片,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听她的录音。可惜,这位除了教英语以外似乎没有其他需求的善良而慈祥的洋老太太被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吓坏了,跳楼摔断了腿。“文革”后期,当我再看见她的时候,她拄着双拐走路,样子十分可怜。每想起她,我心里禁不住要诅咒“文革”,这场荒唐的“革命”害了多少好人!
“北外”的英语教学真是形式多样。除了课堂教学以外,还让同学们互相结成对子,课后练习对话;还可以随时到电教室去听录音。每个班都有一台当时还很稀罕的录音机,同学们可以随时随地去听。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锻炼听和说的能力。这样一个学期下来,我们就敢和二年级那些大哥哥们用英语对话,常常使他们大吃一惊。
“北外”这短暂的两个学期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经历,它给我打下了比较坚实的英语基础,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中有可能通过实践进一步提高。1970年12月,我正式分配工作,先后在哈尔滨122厂(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石油部科技情报研究所、文化部外联局、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从事翻译。2012年12月,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我“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

荣誉证书
回顾北外宝贵的两个学期,我体会最深的是,做学问也罢,学一门本事也罢,最重要的是打好基础。同时我也体会到,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必须踏踏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现在社会上有许多所谓的英语“速成班”,还有许多五花八门自称能让人“快速”入门的英语教科书,声言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就能学会英语。我本人对这些不相信,也常常劝我周围的朋友不要去信。因为我是学英语专业的,参加工作以后也一直和英语打交道,深知不可能“速成”;我和我的同学们虽然不能算是“尖子”学生,但至少是经过“文革”前严格的高考而筛选出来专门学习外语的大学生,我们这些人学起来都那么不容易,老师教起来还那么费劲,一般人怎么能那么轻而易举地把英语学好呢?再说,如果真的有什么捷径和速成法,国家还花那么多人力物力办专门的外语大学干什么?如此明白而简单的道理,竟然有那么多人于不顾,宁愿相信那些所谓的“速成法”和“捷径”,真让人不可思议。
大字报吓疯了一个老师
1966年的四五月份,北京的政治空气骤然紧张起来,报上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的文章连篇累牍,而且调门越来越高,人们的心情十分压抑。年龄大一点的人预感到,中国大地上又要刮起一场政治风暴了,但是,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这场风暴后来刮得那么猛、持续的时间那么长。从5月底开始,我们除了正常上课以外,还帮助学院图书馆搬家。学院原来的图书馆位于4号楼和5号楼之间,是一个4层平顶楼。这个旧图书馆楼一年以后名扬“北外”,它成了“红旗革命造反团”的总部,其顶层架着数枚高音喇叭,不分昼夜地喊叫,使我们住在5号楼的同学饱受了失眠之苦,其地下室曾关押过一些干部和群众,他们在那里饱受折磨。楼前面那一条不长的水泥马路,在武斗最激烈的日子里,成了两派之间的“三八线”,其对立面——“红旗大队”的干部和群众不敢轻易穿越,否则,就会成为“人质”或“俘虏”。1967年10月17日,两派在这座楼前展开了一场武斗,久居中国的外国专家柯鲁克夫妇出于好奇,在旧图书馆楼前观看,被“造反团”发现,马上扭送公安局,罪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外国特务”,克鲁柯被无辜送进秦城监狱,一关就是5年,他的夫人伊莎白也失去了人身自由,在校内被“监护”。
新建成的图书馆坐落在6号楼前面和游泳池旁边,那些日子,我们下课以后来到旧图书馆楼里,抱起一摞摞图书沿着楼前那条水泥马路一直向新图书馆楼走去。教研室主任夏祖奎老师也在我们中间,只见他抱着图书默默地走着,头上的汗水沿着他那发白的鬓角往下流着。每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都是首当其冲,从夏老师那忧郁的神色和凝重的脸色上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又要倒霉了。
6月1日是天真烂漫的少年儿童的节日。可是,一张大字报亵渎了这个美好日子。一大早,广播里传来北京大学那张被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人们吃惊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中央的电台竟然播放大字报?” 而且大字报公开点了北大校长陆平、党委书记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负责人吴子牧、宋硕等人的名字,这等于宣布了这几个人政治上的死刑。大字报称他们是“反革命黑帮”,“黑帮”一词大概由此而来,并迅速传播开来。大字报的作者是一个名叫聂元梓的女人,开始人们都以为她是个学生,后来也一直被称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实际上她当年已50出头,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行政级别12级,属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和其他几位真正的学生领袖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相比,应该是后者的妈妈一般大的老太太了,“文革”后期,北京大学一派学生组织送了她一个不大好听的外号“老佛爷”。这张大字报被广播标志着“十年浩劫” ——“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这一下,“北外”就有点震动,人心慌乱,不到一个星期,正式停课。
“北外”的“文革”初期几乎是仿效“北大”的样子打“黑帮”。几乎一夜之间,学院四处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集中点了三个人的名字:刘柯、郝金禄、石春来,称他们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反革命黑帮”。“打倒刘、郝、石!”、“粉碎刘、郝、石反党集团!”、“揪出刘、郝、石在外院的黑爪牙!”大字报以各种各样的标题或批判、声讨这三个人,他们的名字成了“北外”“文革”期间大字报、广播、大小批判会上出现最多的名字。大字报归纳他们的主要罪行是:1.秉承彭真的旨意,抗拒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领导。事实之一: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以后,彭真指示刘柯布置外语学院收听美国之音等西方国家电台的评论和反应。彭真越过了外交部和新华社,找外语学院的刘柯,说明刘是他的死党,同时说明他妄图夺外交大权。2.积极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3.打击、排斥工农干部,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除了这三个“黑帮”头子以外,基层还有大大小小他们的爪牙,这些人分别是:英语系党总支副书记关化,法语系总支书记杨淦春,西班牙语系总支书记凌志,俄语系总支书记梁克,东欧语系总支副书记张紫霞(郝金禄夫人)、亚非语系副主任陈振宜、院部办公室王助、图书馆支部书记史明、学生科科长陈某、外语附小校长张沁。除了“黑帮爪牙”以外,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也未能逃脱,被冠以“黑帮亲信”或者“黑帮干将”,如英语系总支副书记吴璞和一年级党总支书记郑刚,法语系的汪家荣和宋宝昌。大字报勒令这些“黑帮爪牙和亲信”们交代问题。
以上大字报所点的这些“黑帮头子”及其“爪牙亲信”几乎清一色是原北京外国语学校即“西院”的干部,普通学生根本不认识他们,更不知道大字报所披露的那些“罪行”,显然这是学院党委精心部署的。
有必要介绍一下刘、郝、石三人的简要情况。
刘柯,辽宁省昌图县人。30年代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大学新闻系,和黄华、龚澎(乔冠华前夫人)是同学,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参加进步组织“民先”(抗日民族先锋队的简称)。1936年,应张学良之邀赴西安办报,担任《西京民报》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军区从事外事工作,做过白求恩大夫短期翻译,陪同过英国友好人士燕京大学教授林迈克夫妇。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担任《东北日报》主编。解放初期,任昆明外事处处长。50年代初,任北京外国语学校副校长兼党总支书记,两院合并以后担任第二书记兼副院长。1963年前后,离职养病,“文革”开始前,正在北京医院住院。
郝金禄,原北京外国语学校副书记,后担任北京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主管后勤工作。“文革”开始前已经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任党组副书记,“文革”开始时正参加亚非作家协会会议。
石春来,秦皇岛市人。解放初期,是“华北革大”的学生,后调入北京外国语学校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两院合并以后,担任英语系党总支书记、学院党委常委。1963年左右,调到外交部任亚洲司副处长。“文革”开始那一年36岁。
显然,运动初期院党委所定的这三个“黑帮头子”要么不在领导岗位、要么已经调离外语学院,而这个“黑帮集团”的其他成员都是当时外语学院的基层领导,最高职位为系党总支书记。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几乎和打“黑帮”同步进行。几乎所有的教授、副教授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名教授更是首当其冲。英语系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被打成“洋三家村”,罪名是散布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毒素,利用外语教学阵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许国璋教授所主编的那套英语教材(即目前社会上所畅销的“许国璋英语”)被批为修正主义大毒草,周珏良教授曾写了一篇介绍英国诗人济慈的“西风颂”的文章,被说成是和毛主席的“东风压倒西风”唱对台戏。教师队伍被重新排了一下队,以英语系为例,王、许、周三位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中的老一辈,接着是年龄比他们稍微小一点的副教授,被称为是“中权威”,这些人包括刘世沐、刘承沛、薄冰、张道真、杨树勋、危东亚、王晋熙、邓炎昌等。接着,是讲师一级的,凡是业务尖子和教学骨干都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如青年教师梅仁毅、吴千之、张仲载、章含之、袁鹤年、马元曦、张载良等,他们既是反动学术权威王、许、周的得意门生,又是“黑帮”分子石春来的“八大金刚”,其罪行之一是曾排演过《奥塞罗》《认真的重要》《造谣学校》等外国戏剧,以此毒害青年学生。这样以来,英语系的师资队伍几乎没有多少好人了,老师们胆战心惊,人人自危。
给这些教授、讲师们贴大字报的主要是高年级学生和一部分青年教师,我们一年级学生对大字报所披露的内容一无所知,对涉及的人对不上号,大多数同学在一旁看热闹。然而,一年级个别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其中一位写的大字报导致一位年轻女老师精神失常。大字报的作者看到高年级学生贴那些教授、讲师的大字报,大概受到了鼓舞,于是把矛头对准了教他的一位老师——王世芬。这王老师来自江南水乡,皮肤白皙,长得端庄秀丽,称得上是一位美女老师。她从北外毕业不久留校任教,“文革”开始前一个月左右给我们上过大课。贴她大字报的这位学生是从农村来的,带有比较重的地方口音,英语发音有点吃力。王老师大概是第一次教农村来的学生,听到那浓重的山西口音觉得有点奇怪,忍不住乐了,这一笑使这位同学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认为这是嘲笑他。“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是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表现之一就是打击迫害工农子弟。于是,这位同学借助“文革”初期所刮起的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风暴,把王世芬老师这一笑上纲为对工农子弟的歧视和侮辱,说她是“歧视工农子弟的资产阶级臭小姐”,甚至骂她是“王世臭”,结尾时威胁道:“不管你是王世芬还是李世芬,我们都要把你揪出来批倒批臭……”
有一天,王世芬老师站在这张大字报前,默默地看着。
不久,传来消息说她疯了。
章含之在她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对王世芬被吓疯一事做了详细记述:“当天晚上,首都体育馆的工地打电话到学院说有一个女疯子是外语学院的,在他们那里,要学校去接。工作组想起我向他们反映过,于是派了一辆车叫我和另外一个人去把王世芬接回来。当我们赶到首都体育馆时见到的王世芬竟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她抓住工地铁丝网正在对一群旁观者声嘶力竭地演讲。她不知什么时候记住了那么多当时时髦的口号,什么打倒旧市委,揪出黑帮;什么去新市委请愿之类。我们走上前去劝她跟我们回去。她向周围的围观者大声呼救,说我们是黑帮,要迫害她。那时的许多人好像都丧失了理性。明明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在讲疯话,却竟然有众多的人响应,要跟着王世芬向‘新市委’进军,并且阻拦我们把她带走。王世芬双手抓着带刺的铁丝网,鲜血直流。回校后,她的宿舍在我的隔壁,一整夜都听见她在叫喊。一个文静优雅的女孩子突然之间变成了失去理智的女疯子,我无论如何难以面对这个现实。”
我和王世芬老师不是很熟,印象中仅有两次接触,除了她给我们上大课那次以外,另一次是1966年初,我们在参加修建京密运河工地劳动时走在一个队列中,有一天正好我和她并列走在一起。那时候我们这些入学不久的一年级学生胆子真大,竟敢用刚刚学会的那几句英语和老师对话。我一边走,一边向她请教,她十分耐心地回答我的提问,看不出她对我这个农村来的学生有任何歧视,相反,态度十分和蔼。实话实说,我当时的陕西口音很重,有一次在课堂上冷不防说了一句陕西话,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自己虽然觉得有点难为情和不好意思,但并没有认为老师和同学是嘲笑自己。实事求是地讲,当年外语学院的领导和老师对我们这届学生尤其是从农村来的学生给予了特别关照,倾注了一片真心和感情,配备了很强的师资力量,10多个人一个班配备2至3名老师,老师们个个都很负责任。要说他们中谁歧视工农子弟,那真是冤枉。王世芬老师面对那张大字报,久久无语,我想,她内心该是多么痛苦!
几十年以后,我经常回想“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事情,这场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是要借助群众的力量来打击他们政治上的对手,而在群众中间,一些人则利用当时的政治口号发泄私愤,借“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报自己的“一箭之仇”,而不考虑后果。那位给王世芬老师贴大字报的人心里可能痛快一时,但却毁了一个年轻老师的一生。
没有想到,这一事件对章含之老师刺激很大,促使她给毛主席写信。章含之的父亲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章士钊是毛主席终生所尊重和信赖的党外朋友,章含之本人“文革”前给毛主席教过英语。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她才敢给毛主席写信表达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她在信中详细描述了“文革”初期所出现的暴力和野蛮行为,重点讲了许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挨斗受批的情况,希望伟大领袖能够出面制止。一个星期后,毛主席叫秘书给章含之打电话说:“主席现在不便见你,但有几句话带给你。一句是要你‘经风雨,见世面’,另一句是要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忧来明日愁’。”毛主席的第一句话那是见诸于报端的革命词语,听起来耳熟能详,第二句话很难想象是出自伟大领袖之口,因为他老人家在“文革”中号召人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章含之不解其意,还是饱经历史沧桑的章士钊老先生悟出了其中的含义,他长叹一声,感慨万分地说:“中国又要大乱。”(参见《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第32页,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