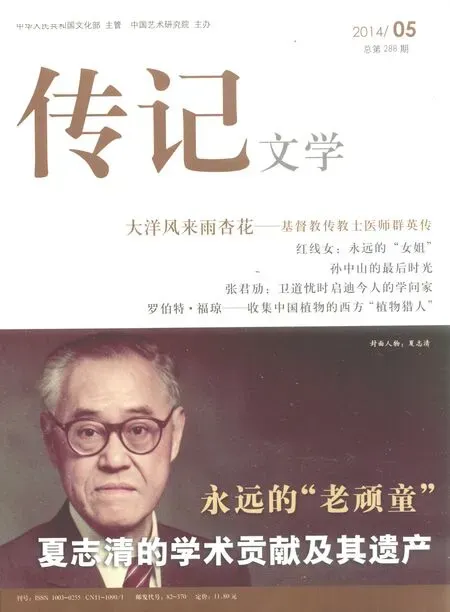用苦难铸成文字
——冯积岐评传(五)
郑金侠
用苦难铸成文字——冯积岐评传(五)
郑金侠

第五章 两块搅团和三斗小麦
1
冯积岐的小说中曾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年轻的农民提着镰刀一大早进山割柴,割了大半天,只有随身带的水解决饥渴问题。到后晌的时候,他饿得几乎虚脱(因为在家,他也是每天都吃不饱肚子),于是他硬着头皮去山里要饭吃。当他走进一家农户的院门口,站在一眼窑洞前,他朝窑里看去,窑顶和窑壁上厚厚的烟灰比瓷器上的黑釉子更加结实更加油光。窑里的亮光很有限,光线也显得有些迟钝。这时,只见窑洞里有一个女人在里面忙碌着,光线实在太暗,他感觉不到那个女人的实际年龄,便怯怯地叫了一声“姨”,他恳求这个“姨”:你能不能给我一块馍馍吃?“姨”只扫了他一眼说,家里没有馍馍。“姨”顺手从案板上拧了一块颜色淡紫发红的高粱面搅团(关中农村用粗粮做的一种吃食)。在接过搅团的一霎那,他抬眼看了看这个“姨”:她可能比他还小一点——十八九岁的样子。本来,搅团这东西是要拌盐、醋、辣子这些调料的。他接过搅团看都没看塞进嘴里就吃了起来。“姨”呆呆地看着他风扫残云般地吞完了一块搅团,顿了顿,就又给了他一块。在饥饿面前,他感觉所谓的尊严已经显得没有丝毫的分量。“君子不吃嗟来之食”,只是某些文人的美好愿望。假如这个年轻女人让他叫“婆”,他也会毫不含糊地开口就叫。这个小说情节不是冯积岐虚构的,是他经历和体验过的真实生活。
多年后,冯积岐没有忘记那个曾给了他两块搅团吃的年轻女人,他不但记住了女人的模样、女人的脸庞、女人的眼神,更记住了女人悲天悯人的那颗善心——他将这个美丽的女人用文字固定在了纸上,呈现在千千万万个读者面前。冯积岐在他的创作谈中不止一次地说过,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是靠不住的。他是怀着一份感激一份尊敬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中无数次地描绘和记录了这个给了他两块搅团的善良的女人。冯积岐记得,在他吞下最后一块搅团时,女人将半碗温开水递在了他的手中。他埋下头喝完水,递还空碗时,对女人很小心地一瞥:女人的眸子很黑,双眼很纯净。女人问了他一句:你是哪达人?他说,山下面,陵头村的。女人没再说什么,进了窑洞。冯积岐看了女人的背影一眼,提着镰刀,走出了院畔。人不能忘恩负义,这个简单的道理不断回旋在他的脑子里,他知道,有一天他会回报这个善良的女人的。

1981年初夏,冯积岐(28岁)摄于陕西岐山县陵头村田地里
那时候,生产队长常常派冯积岐去距离陵头村20里以外的山里去种地——生产队在叫作“桃花顶”的山里有100多亩山地。
冯积岐记忆最深的是,有一年正月里,生产队长派他去“桃花顶”看门。时值正月初三,年味还正浓稠得似化不开的糖水一般。吃完早饭,冯积岐背着薄薄的被子和馒头,踏着厚厚的积雪离开了陵头村向北山里面走去。一场大雪刚刚下过,厚厚的一层覆盖了整个路面,只有一条行人踩出来稀疏而逼仄的小径。上山的路更是白茫茫一片,连个脚印也找不到,只有靠着记忆和路边的荆棘丛认路了。经过半天的跋涉,冯积岐终于赶到了距离陵头村20多里路的“桃花顶”山庄。生产队有一个规定,在没有生产活动的时候,以防窑洞门窗被盗等等此类事件发生,总要安排人轮流看门。当然,这样的差使非冯积岐们这样成分的人莫属,生产队长自有他的考虑。
到了山庄,站在院畔朝下望去,一座座大山在白皑皑的大雪中静默伫立。天气一片阴沉,院子里的雪有一尺多厚,山顶的风狂吼着,冯积岐感到了一阵刺骨的寒凉,从身上冷到了心底。本来,隔壁还住着一家三口,可是春节前都下山去了。他打开了窑门,冷风卷起雪花先他进入门里面,鞭子似地抽打在他单薄的身体上。冯积岐走进了做灶房的拐窑里。一早出发,那时已是半下午了,已是又饥又饿的他急于看看能否做些吃的。他揭开前后锅盖,锅里全是厚厚的冰块。春节前有人离开时在锅里添满了水,本是好意,以备后来者生活之需,不想却冻成厚厚实实的两锅冰。环顾一圈,窑里没有一把柴禾,拿什么点火做饭呢?!走了半天,肚子饿的前胸贴后背,人也累得不能再动,他原想就在冰冷的炕上躺一会儿,先解解乏再说。里间的土炕却是一副坍塌的景象,他似乎站在绝龙岭上,只有仰天长叹的份了!饥饿、寒冷、孤独、甚至巨大的恐惧感一齐向他袭来,冯积岐无力地跌坐在窑口的门槛上,凝视着远处被大雾锁住的山头,泪水潸然而下。他面对的是凄凉、冷酷、缺少人情没有温暖的生活,面对的是自己内心无法言说的痛楚。他很清楚,眼泪解决不了问题。他站起身,擦去泪水。他必须在天黑前找到一些柴禾,这时候,他想到了邻村的山庄,他打算去借一捆柴。于是便来到半里开外的另一个山庄,眼前的景象令他失望至极:没有一个人,草房也被大雪压塌了,那情景就像《水浒传》里看守草场的林冲面对的大雪压顶的惨状。他无言了,折返回去,取了一根绳子,把那草房上的烂草和断了的木椽捆在一起扛了回去,点着了火,烧开了锅里的冰块,把水舀出来倒掉,再把从家里带来的馒头热了热,就当一顿饭了。吃后,他开始填炕,从隔壁的空窑洞里挖了几笼子土垫上,把炕填实了,他的日子总算是安顿了下来。
到了晚上,点上一盏孱弱的煤油灯,昏黄的灯光下,冯积岐铺开了被子,在冰冷如铁的土炕上,薄薄的被子实在无法温暖他同样单薄的身体,他蜷缩着身子。在这深山中,在这寒气逼人的冬夜里,他一个人承受着这一切,没有人能帮到他,他凝视着豆粒大闪烁的灯火,眼泪在默默地流着,这就是他的人生吗?!许多年后,当他读到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所描写的日瓦戈医生和他的情人被困在暴风雪肆虐的小木屋的时候,就想起了自己在雪夜里的孤独,耳畔仿佛回响着凄厉的狼嚎一般。
在山里的那五天,他每天用院子里的积雪烧水做饭,吃的是从家里带来的冷馒头。像一个接受劳改的犯人一样的承受着生活的苦难和内心的煎熬。那五天,让他学会了面对生存的挑战,学会了面对苦难的淡定和坚实的生存之道。
回想起他的少年和青年时期,许多美好的日子都播撒在了这个深山里。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陟峭的坡地里,纵横交错的山沟中,曾经洒下他深浅不一的脚印和苦涩艰辛的汗水。他的生活乃至生命和这个大山密不可分;对山里的生活,他有刻骨的体验。冯积岐的长篇小说《村子》《沉默的季节》《逃离》及中短篇小说《黄芩》《树桩》《成人仪式》《我们在山里活人》等篇章的不少故事都和这一座大山相关联。山,是冯积岐人生舞台上一根不可或缺的立柱,是他充满苦难的农村生活中丰满的一页,是他创作的“背靠点”和源泉。在冯积岐的作品中,人物一旦“进了山”,故事都是那么的丰饶,那么的生动。《黄芩》中黄芩的人物原型就来自他们隔壁住着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小女孩一家二代四口人住在一眼很小的窑洞里,一进窑洞,右边是土炕,左边是锅灶,锅灶后面是案板,案板底下安置着猪和鸡。小女孩和哥哥以及母亲、养父一家人每天晚上就蜷缩在那样逼仄的土炕上睡觉,简直让人无法想象。一天午后,冯积岐去隔壁借农具,窑洞敞开着。他走到窑口,迈开的步子正要落下,猛然看见小女孩的养父和她的母亲倒在灶膛前一块窄小的空地上。冯积岐一愣,突然明白了什么,他赶紧退出窑洞跑了出去。若干年后,冯积岐从山民们粗糙而原始的生活中开掘出了较为深刻的小说题材。
在山里,每天清晨,天还没有亮透,他就要爬起来套犁,犁地。肚子饿了,他顺手从地里拔起一根草根放在嘴里嚼,像牛回草一样不停地嚼着,越嚼,反而感觉越饿了。等到半晌午把两头牛从犁上卸下来的时候,冯积岐已经累得趴倒在湿漉漉的山地里起不来了,他双腿打颤,眼前发黑,他几乎连地里的土都想掬起来吃下去。当他饿得前身贴后身的时候,看见饭食反而产生憎恶的感觉。
饥一顿,饱一顿是常有的事情。生产队长不管你的肚子饥饱,他只把你当作一个劳动力看待。晚上去饲养室记工分的时候,生产队长说,明天去踏胡基(打土坯),两个人踏十磊。踏胡基是力气活儿中的重活,一磊子胡基500个,一个也不能少。冯积岐本来就瘦弱单薄,加之总是饿着肚子,他把那几十斤重的石头锤子提在手里,在胡基模子上轮番捶打着(一块胡基打20锤左右)。到最后,他饿得虚汗不止,肠胃里被掏得什么也没剩下,如果不是手里按着石锤子的把儿,他肯定会一头栽倒在地上的。他从模子上下来,蹲在土窖里长长地喘着粗气,他体验到的饥饿是一种要呕吐的感觉,似乎只要把肠胃能吐出来就不会再饿着了。回到家,端起饭碗,他心里很难过,喉头哽咽,无法动筷子。
在冯积岐的记忆里,最饥饿的岁月是“文化大革命”那十年。造成饥饿的原因不只是天灾还有人祸。生产队里打的粮食除了交公购粮,还要交什么爱国粮、支援世界革命粮。每个社员分到手的口粮每年只能吃八九个月。到了农历二三月青黄不接的时候,上面就给农民发放返销粮。返销粮不是按人头分配的,而是由生产队里评——说是评,其实是生产队的干部和生产大队的干部说了算。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子女是很难吃上返销粮的。每一个贫下中农吃100斤,地主富农只能得到10斤或20斤。在那时候,没有人管你是否会饿死。没有粮吃,每天照样要上地干活。如果缺勤一天,夏秋两季分粮时就要扣二斤粮食。男劳力一个月必须出勤28天,女劳力一个月必须出勤26天,这是硬性规定,无人能改。
地主富农和“狗崽子”们就是吃糠咽菜也难熬过这两三个月的时光。家里能卖的都卖掉换了粮吃。黑市粮有的是,可是,没有钱买。剩下的一条路就只有去借,向亲戚朋友借。在饥饿的岁月里,冯积岐把每个有粮食的亲戚朋友家都跑遍了,看人家眉高眼低也罢,挖苦讥刺给脸色看也罢,冯积岐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他只是含着屈辱去恳求去借粮。尽管嘴很笨拙,好话还是要说。求人时,根本没有自尊和尊严。一颗年轻的心在胸膛里忐忑不安地跳动着,就怕遭人拒绝。如果他借不到粮食,就要去讨饭吃。这些事情,父亲从来不管,父亲就连去隔壁借一件农具的勇气都没有。从十五六岁起,冯积岐作为长子就担起了生活的重担。冯积岐有一个表哥,是别的村的生产队长,他家的麦子用包扎着,足足有七八石(2000多斤),冯积岐去表哥家借粮食,表哥的脸吊得老长,他说,你们前几年借的三斗麦子还没有还,借了你们拿啥还?冯积岐只能苦苦恳求,他知道,粮食借不到,明天就断顿了。表哥很不情愿地借了他三斗麦子。冯积岐拉着架子车里借到的粮食,走出村庄,他的眼泪喷涌而出。他的情感很复杂,既委屈又感激,委屈的是他付出自尊才换得了粮食,感激的是表哥终于借给了他粮食。
有一年初夏,眼看着又要断顿了。家里已是无处可借。当冯积岐初中时的同学杨恒兴用自行车把三斗麦子给冯积岐推进家门的时候,冯积岐的父亲就像家里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似地从房子里急急地跑出来,按住自行车的车头竟然不知说什么好,冯积岐的母亲满含感激的泪水潸然而下。对于饥饿的一家人来说,这三斗麦子就是救命粮。同学杨恒兴,成为冯积岐一生都不能忘记的至交。
已经到了1976年夏收时节,“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了,冯积岐一家仍旧处于饥饿中。搭镰收割的第三天,家里断顿了。那天中午,冯积岐和父亲、妻子、妹妹一起去给生产队里割麦子,割了一晌麦子,已是又饥又渴。特别是父亲,额头汗珠滚滚,脸色发黄,疲惫不堪。收工回到家里的时候,家里静悄悄的,听不见熟悉的风箱声,闻不见柴草烧锅时的味儿,院子里,似乎没有一点点生活的气息。母亲没有在灶房里做饭,锅冰灶凉。往常这个时候,母亲早已经做好了饭在等他们了。冯积岐问祖母:我娘哪搭去了?祖母说,出去要面去了。冯积岐和父亲他们没有饭吃,一家人坐在房檐台阶上,谁也不开口,谁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只有父亲在一声接一声地叹息着。院子里的气氛冰凉、凄楚,冯积岐心里难受得无法形容,他感觉作践一家人的不仅仅是饥饿,更有一种无以言说的艰涩或者无法表述的令人心酸、心痛的情感。他觉得,在苦难面前他可以不低头,但一家人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实在是太煎熬了,简直无法活下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母亲回来了。几十年后,冯积岐怎么也忘不了母亲那天的形象:她的脸色蜡黄,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脚步细碎而急迫,手中提着一个面口袋,从前院匆匆地小步赶进门来。母亲一句话也没有说,她走进了灶房,把要来的面抓了几把搁进和面盆里开始和面。冯积岐知道,母亲身体不好,但她的内心总是那样的坚毅而顽强,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是母亲一手支撑着,她就像在大海中掌控着一叶扁舟,艰难地带领着一家人迎风破浪,把日子一天天地往前拽。收麦子的时候还要讨要,一家人和叫花子有什么两样?!这些无法回首的日子顽强地守望在冯积岐的人生中,他一回想起来,心里就痛疼难忍。等母亲把饭做熟了,上工铃敲响了,一家人匆匆地吃下几口饭,又上地给生产队里割麦子了。下一顿饭母亲又要去哪里要?就是民国时期的佃农和长工,收割时,也能跟着碡碌过个年。一家人捱到收麦时节,还要饿肚子,地主富农和狗崽子还有活路吗?父亲只是一个劲地抱怨着,他拿不出对付艰难日子的办法。
母亲是在哪儿要的面?母亲讨要时是否受了委屈?母亲是否多次讨要过?冯积岐想问问母亲,可是,直到母亲去世,他始终没能张开这个口。他不敢也不能面对母亲伤痕累累的过往人生,他觉得,母亲活得太可怜了。在他的小说《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中,他倾注了自己对母亲和这个版图上生活着的所有母亲全部的心血和感情——那就是对爱、怜惜和同情以及忠诚的讴歌。在《沉默的季节》里,周雨言的母亲出去要饭时被迫吃猪食的情节就来自冯积岐的母亲曾经讨要的现实生活原版。
晚上收工回来,父亲给冯积岐说,你去给队长说说,给咱借一斗麦子。生产队已碾了一场小麦,麦子就堆在打麦场上。冯积岐硬着头皮去找生产队长。生产队长闷声待在房间里抽烟,他的脸像刨子刨过一样板平,冷漠,显得毫无人情。冯积岐把借粮的事一口气说了两遍,生产队长没吭一声,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房间里的气氛很凝重。生产队长一边抽烟,一边将装满“阶级斗争”的眼睛看着门外面。生产队长的母亲看着不落忍,她说,你给人家娃说一声,到底借还是不借,咋塞死不言传?又过了一会儿,生产队长的嘴里嘣出来石头般坚硬的两个字:不借!冯积岐没有再三恳求,他默默地走出了房间。这个没有借给冯积岐一两粮食的生产队长,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冯积岐家里来借粮票(改革开放以前,买粮食或去餐馆吃饭用的票证),冯积岐没有犹豫直接送给了他100斤粮票。那是冯积岐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作家班时,积攒的几百斤学校发下来没有用完的粮票。在他看来,这个生产队长虽然心硬如铁,缺少恻隐之心,但还算不上“坏人”。他的小说中塑造的生产队长的形象就来自这一个具象的人物。
第二天傍晚收了工,父亲给冯积岐说,你到东坡去给你德儿叔说说,给咱借一斗麦。冯积岐挟着口袋出了村,上了东坡生产队。被父亲称为“德儿”的是东坡生产队里的队长刘德太。冯积岐找到他的“德儿叔”,说了家里的窘迫和借粮的事,刘德太把冯积岐领到生产队里的打麦场上,吩咐保管员给他装了一斗麦子。踏着暮色,冯积岐背着那一斗小麦回了家。母亲即刻取来了簸箕将麦子簸了簸,背到生产队里的电磨子上去磨。
同样是生产队长,同样是贫农成分,为什么刘德太就把粮食借给了冯积岐?这不是“亲不亲,阶级分”能概括当时的人际关系的。只要有一颗向善的心,不论在怎样的际遇下,都是会乐善好施,这和出身、地位没有多大的关系。他至死也不会忘记在他们一家断顿的时候借给他们一斗小麦的刘德太。2
013年春天,冯积岐回到陵头村,见到了已经74岁的“德儿叔”, 冯积岐旧话重提,说起了那一斗小麦的事情,刘德太说,你爹是个好人,你们一家都是好人,我清楚着哩。那个时候,你们一家受大罪了。在冯积岐的作品中,像刘德太这样怀有善心的好人随处可见,他让这些好人昂首挺立在文学的圣殿,活在读者的心中;小说《沉默的季节》中的祖母、粮子老汉、宁巧仙;《村子》中的赵烈梅、马志敬、祝义和;《大树底下》中的父亲、祖母等等都是一个个鲜活的好人。2
在我们的许多书籍中,把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饥饿岁月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在那三年里,可以说是全民饥饿,全国饥饿。
在那特殊的三年里,冯积岐印象最深的是村子地窑里的叫花子。村子东边的地里有几眼地窑,从平地上挖一道坡,坡下面开一个天井,天井四周是窑洞。窑洞里铺着麦草,那些从甘肃逃难来的叫花子东倒西歪在麦草铺上,他们脸色蜡黄,精神疲惫,双眼无光,衣衫褴褛。多年后,冯积岐从资料中里了解到:在三年困难时期,甘肃是重灾区之一,那些垂死的农民纷纷逃难到关中寻求活命。冯积岐和他的小伙伴们怀着好奇的心理跑到地窑里去看那些叫花子。其中在地窑里的一个女叫花子给冯积岐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那是一个大约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没有裤子穿,光着屁股。同去的一个男孩子从麦草铺上捡起一根草枝,耍猴一般在小姑娘的光屁股上乱戳,小姑娘羞红了脸,忍无可忍后猛地拧身扑过来,抓住那个男孩子的胳膊就咬,那个男孩子吓得赶紧往坡上跑。后来,村里的一个光棍汉领走了那个中年女人和她的小姑娘。冯积岐这些童年记忆里的片段后来成了他小说中的生活原型。
冯积岐的短篇小说《树上的眼睛》中讲述的饥饿年代的故事是一副真实的图景:饥饿的中年男人打发四五岁的孩子挨家挨户去讨要。孩子将半碗饭或几口馍要回来之后,自己还没有吃,就先回到街道口的大树底下给自己饥饿的父亲,那个父亲拿过孩子手里要回来的饭食狼吞虎咽的几口便吞下去了,没有给孩子留下半口,甚至也没问孩子有没有吃,饿不饿。这是冯积岐亲眼目睹过的场景,在饥饿面前,人性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与挑战,为了自己活着,亲情变得如此之脆弱、可憎。据此,他认识到历朝历代的大饥荒中,“人相食”的记载是真实的。灾难,是对人性的考验,面对灾难,人性的劣根性暴露无遗,灾难就像试金石一般让人没有逃遁的角落。《泰坦尼克号》之所以抓住了全球观众的心,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面对生死的关键时刻,船长的“妇女儿童先上救生艇”的一声断喝。船长的形象一下子树立起来,高洁伟岸的情怀,人性之美在此得到了充分的绽放。人作为生物性的存在,离不开空气、水和食物。作为精神的存在,文学作品需要塑造这样一个完整的人。因为人一旦精神坍塌,将根本无法站立。

1983年,30岁的冯积岐(右)与作家黄建国摄于临潼华清池
在吃公共食堂前,公社里派机关干部去各生产队挨家挨户搜查粮食——不允许农民家里存放一粒粮食。当时,冯积岐的父亲担任陵头村生产队的会计。哪一天搜粮食,父亲会提前得到消息,他给能说到的村民,搜查前都一一通知。有些村民得到消息后开始藏粮食。藏的严实的,躲过了这一劫,没有藏严实的,被全部搜去。有一个村民在瓦罐里藏了几斤红小豆,竟然也被搜了去。他记得,那次灾难性的事件过去了好多年后,村民们仍然念念不忘冯积岐父亲的恩情。他们给冯积岐说,多亏了你父亲让我们提前得到消息,藏了几斗粮食,不然,那样的年馑,非饿死不可。父亲天生脾气暴烈,但是他的心里总是装着和他一样受苦的人,父亲有着金子一般的心。就像《村子》里的祝永达的父亲一样,利他主义是父亲做人的原则。父亲的善良一直影响着冯积岐弟妹的成长与做人。
一开始,食堂里还有馍馍,有面条,到了1961年,生产队里的食堂里一天两顿糜子面糊汤,说是糊汤,其实和下毕面的面汤一样稀,糊汤里有几块煮熟了的萝卜。母亲端一个瓦盆,从公共食堂里打回来糊汤,用勺子给一家老少分,一人一小碗。母亲的每一顿饭,都是她给一家人分完饭后,剩多少,她便吃多少。如若是清汤寡水的饭食没有剩下,她就没有饭吃。冯积岐从小就是在这种母爱下长大的。小小年纪的他目睹着村民去北山里打酸枣,然后在石碾子上碾成酸枣饼和碾毕小米的米糠(小米皮)烙成饼吃;曾目睹有人把榆树砍倒,剥下来榆树皮,然后晒干捣碎吃。这些东西冯积岐也吃过。吃下去,屙不下,憋得肚子疼。
一天,冯积岐半夜里被祖母从被窝里拉出来,他睡眼惺忪地跟着祖母到了后院里。一到后院,祖母就倒扣上了后门。只见楼房的后檐台上用几块土坯支着一个锅,锅里是母亲已经下好的面条儿。母亲给冯积岐盛了一碗面,冯积岐接过去,埋下头就吃,吃了一碗面,反而更饥了。后来,冯积岐才知道,在公社里派人来搜粮食前,父亲将三斗小麦藏在了祖母已经做好了有十年的棺材中。幸亏,搜粮食的人没有打开棺材看。也许,他们潜意识里有恐惧感,不愿意去碰老人的棺材。父亲和母亲半夜里起来在家里的石磨子上把小麦磨成面粉,过几天,饿得实在不行了,就偷着做面条吃。吃自己的粮食还要偷着吃,这叫当代人觉得实在不可思议。因为那时候只准公共食堂里的烟囱冒烟,各家各户的烟囱是不能冒烟的。有些农民家里连锅都没有了。那时候,有一个口号叫作:只有一只碗一双筷子是自己的,其余的东西都是人民公社的。
三斗麦子,也是偷着吃不了多少时日的。不过,有这三斗麦子垫底,毕竟比生产队里的其他农民幸福多了。那时候,冯积岐只知道偷着吃可以填饱肚子,他还感觉不到偷着吃在填饱肚子的同时会给父母亲带来怎样的紧张与不安。对父母亲来说,偷着吃是很害怕的事情。如果被生产队里的干部捉住,非被再次抄家不可。半夜起来“偷着吃”这件事,冯积岐后来写进了他的小说《沉默的季节》及几篇散文中,它深深地刺激着他敏感的神经。
偷吃自己的都惶惑不安,偷吃人家的更是要付出代价的。
饥饿的冯积岐和他的小伙伴们偷过生产队里的西瓜,偷过邻家的桃子、杏子。有一次,为偷杏子吃,从杏树上掉下来,摔伤了腰,被人背回去,在家里躺了十几天。他亲眼看见,他的一个小伙伴因为偷吃生产队里的豌豆,被生产队长捉住,捆在了村子街道的中国槐上。他的短篇小说《树上的眼睛》就是有关饥饿的记忆。在小说《沉默的季节》中,对饥饿的体验,在他的笔下苦若黄连,痛若刀割,读之使人震颤。
上初中的冯积岐每周要步行到50里以外的学校去读书。秋季里的一天,走到学校半路,他饿得实在不行了,拔了人家地里一个白萝卜,一口都还没来得及吃,就被生产队里的人抓住了。那人要把他带到学校里去交给老师处理,冯积岐一再求饶,他知道,这事情如果被老师和校长知道,他就名誉扫地了,也许,他会被开除,无法在学校继续读书。那人说,你如果不去学校,就把这个萝卜连叶子一起吃下去。冯积岐看着带着绿叶沾着泥土的萝卜,无法张口。他怎么能吃下去生叶子和泥土呢?!那人看冯积岐站着不动,转身把一口痰吐在冯积岐的脸上,扬长而去。悲凉的秋风迎面吹来,冯积岐呆呆地站在萝卜地里,体味着萧杀的深秋,眼泪在眼眶里打颤。饥饿不只是对他的肉体的折磨,也是对他的精神的摧残。他常说,自己自尊而敏感的性格是饱受多次屈辱以后形成的。对冯积岐来说,饥饿和苦难未必就是坏事。一个作家经历越丰富,书写也就越透彻。固然,不是说一个作家写小偷就要去做贼,可是,那些无病呻吟或者强说愁的文字堆砌与蕴藏着作者痛彻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思考的作品相比,读者所获得的艺术享受有着天壤之别。冯积岐的诸多小说中阐述了他对生活,对时代,对人性深刻的理解以及对人类深切的悲悯。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