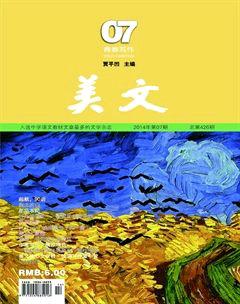橘红糕
金竹
橘红糕,一种老掉牙的糕点。
记得有回贾母问宝钗喜吃何物,宝钗深谙老人家爱甜烂之物,便专挑了贾母喜欢的说了几样。吃食方面,我倒也和老头老太们一样,就拣甜的软的吃,什么糯米糍、驴打滚、麻芯汤圆、奶油泡芙,多少不论,一概全收的。
橘红糕制作历史极久,称得上甜糯糕点之鼻祖。小时候在农村疯野时,总见一太婆蹬着一车的橘红糕沿路吆喝叫卖。一块块橘红糕齐崭崭地码在簸篓里,用干净的麻布遮盖着,有客人来,太婆便取来杆小秤,称上一纸包——碰上小孩买糕,还能多给一块。
我曾目睹太婆做橘红糕,手法传统且繁琐。
一团熟粉,一把白糖,一勺薄荷脑。一双老手娴熟地将原料掺和均匀,然后,揉、捶、打、甩,折腾太久面筋会老,力道不够又嫌嫩,只有熟练者才能游刃有余,使面团弹性劲道恰恰好。之后方能上案擀压,切成指甲盖大小的方块。
整个制作过程中最有韵味的,莫过于“点胭脂”。太婆会割下一茬茬嫩嫩的红苋菜,捣出新鲜汁水来,然后拿小竹签蘸着苋菜汁,在切好的每块糕上描一个红点儿。接着,一簸篓的橘红糕上笼一蒸,冰薄荷沁人心脾的甜香便溢出来,填满屋子里的每个罅隙。
再揭开笼盖,隔着雾气窥见苋菜汁已渗进糕团,细细密密地晕染出一点点灼灼的红。叫人不由联想到古代美人眉心间那一点朱砂痣,盈盈一水间,顿觉风情万种。
橘红糕出笼前还须滚上一层熟米粉,方不至于粘手。太婆慈善,见我已在一旁眼巴巴守候多时,便会拣出几块热腾腾的糕团赏给我。我那时真馋,捧着橘红糕如获至宝,狗一样乐颠颠地蹲墙根去了——吃是舍不得的,只闻一闻,舔一口,再盯着那红点儿发怔。
三块橘红糕往往值得我花半天吃,再用另外半天细细回味。
……
后来,太婆年纪愈大,老到拎不动蒸笼,也踏不起三轮了,终于躺到床上,终于躺进黄土里。自然,橘红糕也就这样,销声匿迹了。
村里人吃了几代的橘红糕,也早该换换口味了。物欲横流的年代,形形色色的事物冲击着人的感官,大家忙着应付层出不穷的新奇食物,一时忽略了老掉牙的橘红糕,也是理所当然的。
可惜我是个极恋旧的家伙。即使长大后搬出了村庄,即使家里条件渐渐宽裕,即使如今奢侈到再金贵的糕饼都只咬一口便搁边上,我还是独独忘不了那块橘红糕,忘不了如玉般的莹白温润以及眉宇低回间,那一点红朱砂。
张爱玲在散文里写她常梦见小时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怅惘。
谁的生命不是如此?故人已逝,往事心酸。回忆若是有气味,必定是橘红糕的冰薄荷香气,甜而稳妥,丝缕游荡在每一个恍惚的瞬间。
人间别久不成悲,相见倒不如不见。
我本以为今生难逢橘红之风情,谁知这么多年了,居然能在一个外贸专柜上瞥见那一抹熟悉的红朱砂。
隔着玻璃橱,它的红太刺眼,显是人工色素在搔首弄姿;而它的白嫩又显得暗淡了,失却了当年太婆手下的莹洁剔透;更可悲的是,精美的标签上写着的竟是“进口点心”,而非我心心念念的“手工橘红糕”——大约已鲜有人记得,这位从中国古典诗词里款款走出的美人,芳名:橘红。
我结了账,找个没人的角落蹲下来,拆开盒子,小心翼翼地拈起一块糕点,像小时候一样,闻一闻,舔一口,最后才心满意足地送入口中。
不出所料,我还没嚼上两口,便觉不对劲。太甜,甜得腻味了,完全品不出薄荷的清冽,香米的甘糯;且口感软趴趴的,毫无嚼头,可憎地黏缠在喉头,像鱼刺,像痰,咽不下去,却又吐不出,涩而怅惘。
这就是我日思夜想的橘红糕?不,不是这样的!仿佛刚从一场光风霁月中仓皇惊醒,刹那间被排山倒海的失落感湮没了。直面现实的滋味不好受,像是眼睁睁看着容姿如玉的美人被赶出本属于她的亭台楼榭,从此流亡红尘,无枝可依。
我想,若是做橘红糕的太婆还在世,必定也不愿看到这番情景吧。
整个时代荒淫繁华,横冲直撞着,然而奢靡的背后,总会有些曾经很美很纯的东西,躲在人们视线的背阴处,挣扎,颓唐,终而萎谢。
我直起身,收拾购物袋,拖起大包小包回家。身边不时掠过一对对红男绿女,朝气蓬勃,容光焕发的样子。临出门还瞅见一个时髦女孩,对着光亮如镜的金属玻璃门,咬开一个亮晶晶的发卡,细致地别进挑染的长发,然后举起手机熟练地摆出造型,自拍。
我怔怔地盯着她良久,随后撮起嘴唇,用极轻的声音,让那三个字在胸腔、喉头、舌尖、齿间,反复流转着,激荡起惊鸿绝响:
“橘——红——糕——”
(浙江省萧山中学1504班)
(荐评人:柯红斌)
【推荐理由】
生命有它最原始最纯粹的一面,如同豆蔻少女,天然一段风韵。可惜总有人自作聪明,殷勤地拿香脂银粉去玷污它的纯美。
行文流畅华美,言辞精准犀利。对童年回忆的记叙烂漫温馨,而对传统橘红糕的消逝又不乏叹惋缠绵。结尾咬开发卡的时髦少女的出现,将作者的凄怨情绪推向极致,寥寥几笔便诉尽苦涩的思念与甜腻的怅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