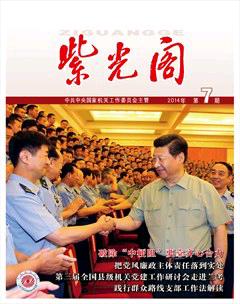“我没有辜负对组织的誓言!”

入党:这是必然的人生选择
我是1949年初入的党。在思想汇报上我引了列宁说的一段话:如果革命需要我一次性把血流光,我就一次性把血流光;如果革命需要我一滴一滴地流光,我就一滴一滴地流光!
当时我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大四。进入交大后我就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叫“山茶社”,这是共产党员领导的社团,主要进行一些革命教育。1948年夏天我就向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局势非常危险,国民党在上海对我们的地下党组织的镇压是非常残酷的,有的同学就牺牲了,没有迎来解放。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实施大逮捕,组织通知我们临时撤出学校。两三天后学校又平静下来,我们就又回去了,准备迎接解放军渡江了。那天夜里学校里响起了机关枪的枪声,我非常激动,是解放军来了!但其实是国民党的士兵进校搜捕学生党员。我就躲在厕所里,有个同学冒险悄悄跟我说,楼梯口的士兵换防了,正好没人,让我赶快上三楼,那里不是搜查重点,比较安全。我就趁着这个机会一口气跑到三楼,躲在别的同学房间里,这才逃过一难。我隔壁的党员同学就是那天牺牲了。
加入共产党对我来说是必然的。我1926年出生在广东海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沿海城乡学校都停课了。那时我近10岁,在家里休息了半年,参加了当地的抗日宣传队。靠近除夕,日本鬼子马上要进城了,我们上台演出话剧,叫《不堪回首望平津》,说的是老百姓逃难的事。我男扮女妆,主演流亡的小姑娘。我们演得特别认真,台下看的人很多,也很动情。演着演着台上台下就越来越激动,抓到汉奸了,台下无数的观众含着泪水一起高喊:“杀!杀!”那时我就想,长大了,我一定得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求学:怀揣报国理想上征程
怀着这个信念,我踏上了求学之路。中学进了聿怀中学,抗战时聿怀迁到了揭阳的五经富,在山沟里。那时我14岁,跟着哥哥去五经富,交通断了,就靠两条腿走了整整四天,脚都磨出了好几个血泡。但是没有哭,我要读书啊!那么危险、那么艰苦的环境,大家都挺着。五经富的学校搭的就是草棚,也不安全,日本飞机时不时来轰炸,我们就跑到更偏僻的山沟里。那时我又参加了抗日宣传队,到乡村里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我还是男扮女装,演小姑娘。
后来,我们几个同学又跑到桂林入了桂林中学。毕业后就到了柳州,从柳州坐火车到贵阳。那时都在大撤退。好不容易挤上车,行李都丢了。那时唐山交通大学迁到了贵阳,我就报考了。但是同学们还是决定到重庆去。在重庆我报考了中央大学的航空系和上海交通大学的造船系。结果两所大学都录取了。上交大的造船系我考了第一名。最终我选择了上交大。因为我在海边出生,海边长大,对大海有感情啊!而且上交大被称为“中国的MIT(麻省理工学院)”,理工科水平是国内最好的。
使命:对祖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孝
工作以后,经组织选派,我参加了苏联援助中国的几型舰船的转让制造和仿制工作,这也是保密性的工作。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中国希望苏方能援助核潜艇项目,被拒绝了。赫鲁晓夫提出成立中苏联合舰队,由苏联舰船保护中国国土。当然我们也拒绝了。赫鲁晓夫很狂妄,认为中国人搞核潜艇是“异想天开”。毛泽东主席很生气,下定决心,一定要自己搞成,说“搞一万年也要搞!”
那一年我就被调到了北京,一开始组织上就讲得很清楚了,这是最高密级,必须隐姓埋名,绝对不能透露工作性质和工作单位。对此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服从组织决议,保护组织机密,这是一名党员职责所在。
但是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一搞就是三十年。1956年阳历年的除夕我到广东出差,顺路回了老家,过了元旦两三天我就又走了。一直到1988年我才又回了老家。
那次见面母亲就跟我说,绍强(黄旭华原名),你从小就离家求学,我一直祈祷你平平安安的,现在都解放了,天下太平了,我们年纪也大了,希望你能常回家看看。实际上,1958年参加核潜艇研究后,工作就异常紧张,我就不可能回去,连信也极少写。母亲一直为我操心。我既不回家,也不联系家里。她就给我写信,问我,绍强,你到底在干什么呢?我无法回答。
1962年父亲去世了,我没有回去;1985年,二哥去世了,我没有回去。那时应该宽松点了。夫人对我说,你回去吧,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的。我还是没有回去。家里人意见很大,我兄弟姐妹一共九个,母亲把他们叫在一起,说,你们要相信三哥,他一定是有原因的。其实母亲也想不通,她的三儿到底在做什么呢?她自己不知道在心里流了多少眼泪。
1988年,我到大亚湾出差,终于顺路回了老家。我62岁,母亲95岁,我不知道说什么。跪在父亲的坟前,我说,爸爸,你的不孝儿子回来看你了!你会像母亲一样原谅我吧!
有人说忠孝不能两全,但是,对国家的忠,不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吗?对母亲的承诺我没有做到,但是我没有辜负对组织的誓言。这么多年,我的确亏欠父母、妻子、女儿太多了。我夫人李世英一直默默支持我,家里所有的事情都靠她一个人。
奉献: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样;
我们属于核潜艇,无怨无悔
核潜艇的技术综合性很强,三个方面“艇”指潜艇,“堆”指反应堆,“弹”指导弹缺一不可。刚开始我们只搞过苏式仿制潜艇,而核潜艇与潜艇有着根本区别。要攻克的技术难题太多了,物质条件也跟不上,但我们靠的就是一种精神,一种责任。
1988年,我们在南海按设计极限作“深潜试验”,这是最后关键环节也是危险性最大的试验。在深海,一张扑克牌大小的钢板就要承受一吨水的压力,一艘艇100多米长,只要一个小环节出了问题,那就是致命的。70年代末,美国的“长尾鲨号”在做深潜试验时就没有上来,艇毁人亡。
有的同志给家里写了遗书,做好了一切准备。同志们唱《血染的风采》,很悲壮。我觉得这样不行,就召开技术骨干会,我说,我们都是搞科学的,要用技术说话,用技术保证安全性;我们的工作做得很细的,是有一定把握的;作为总设计师,我和大家一起下去!
你问我作为总设计师可不可以不下去呢?我必须得下去!即使我不下去,万一有事,我怎么对得起大家,怎么对得起组织?我夫人也支持我下去。我说,我们不唱《血染的风采》,我们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试验成功了。核潜艇安全顺利靠岸,大家激动得哭了。后来我写了一首诗以示纪念:南征应捣龙王庙,此战惊雷震满天;骑鲸日游八万里,驭龙直上九重天。
“两弹一艇”对新中国很重要,弹是原子弹、氢弹,艇就是指的核潜艇。我们这个团队,几十年一起拼搏,一起努力,我们自己概括核潜艇精神就是四句话: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我认为这种精神永远不会过时,也适合现在的年轻人。还有,不要以为引进外国技术就什么都解决了,尖端技术,人家是不可能给你的。
核潜艇研制成功是集体智慧的结果,我只是其中一员而已。我们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没有考虑过自己的事情,事业是第一位的。有很多同志,60多块的工资一拿就是几十年,退休了也没赶上工资改革调整。我们在荒岛上试验,条件很艰苦,但是没有一个人掉队。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属于祖国,属于核潜艇,我们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