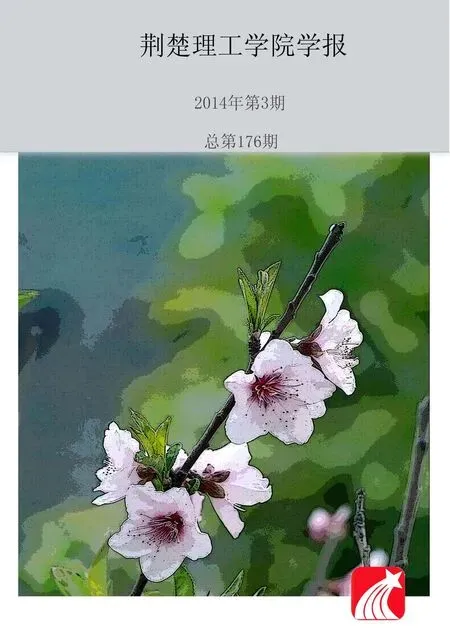关于给予义动词转化为被动标记的过程探索
刘海波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关于给予义动词转化为被动标记的过程探索
刘海波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近代汉语中的给予义动词发展出了被动标记的用法,有两条途径,一是给予义动词及其所构成的双宾语结构,首先演变为使役类结构,然后再由使役类结构进一步演变为被动式,即给予义动词经历了使役义动词这个中介才演变为被动式标记;二是给予义动词及其所构成的双宾语结构在语义和语法结构上同被动式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可以直接发展为被动式,给予义动词也就演变为被动式标记。这两者的句法结构在表层上都是相同的,但是由于具体的句法环境的差异才促使它们演化道路的不同。
被动句;使役句;给;语法化
一
(一)使役动词兼用作被动标记
“教”“著”“使”“让”都是具有“使令”意义的动词,它们的基本语法功能是构成使役式,即带有使令意义的兼语式。这种兼语式其后逐渐发展成为被动式。使役和被动是不同的语法范畴,在一些语言里被区分得很清楚,为什么汉语的“叫、让”却可以使役、被动兼用呢?对于这个问题,太田辰夫、蒋绍愚、江蓝生、冯春田等都曾做过研究,蒋绍愚[1]对于他们的意见作了概括,主要有以下四点:
(1)汉语的动词表主动和表示被动在形式上没有区别。
(2)能转化为被动的使役句的谓语动词必须是及物的。
(3)能转化为被动的使役句的主语不是施事成分,而是受事成分。
(4)事件的已然与未然对于转化的影响。例如:“这件事让我做”和“这件事让我做了”,后者可以理解为被动句。
洪波、赵茗[2]对此做了补充,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使役动词都可以转化成被动标记,只有使役性最弱、对施事的依赖性最弱的容让型使役动词才具备了转化的可能性。使役动词兼用被动标记的原因和过程已经描述得很详细了。无论是从句法重新分析的角度还是从语义链条的角度我们都可以有理由认为使役动词可以演变成被动标记。
不过,桥本万太郎[3]认为汉语使役动词兼作被动标记是汉语阿尔泰化的结果,而且认为汉语南北方言在这一点上至今仍有较明显的差异。江蓝生[4]对上述意见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她认为在探索一种语言的某一语法现象的来源时,一般应先从这个语言自身去寻找原因,如果从该语言的内部找不到合理、圆满的解释时,就须从外部——语言接触、语言渗透等因素去寻找答案。汉语使役、被动兼用完全能用汉语的历史文献、汉语的本质特征作出合理的解释。蒋绍愚[1]则主要从汉语内部的自身发展规律方面探讨了汉语使役句的重新分析,但他无法确认语言接触是否对这一演变过程产生过影响。
(二)给予义动词兼用作被动标记
给予义动词(“给”、“乞”)先后发展为引介施事者的介词,从而成为了被动式的标记,它们所经历的演变过程不同于“被”、“吃”和“蒙”,而是与使役类动词相似。“给”的“给予”义是后起的,“给”字被动式出现于明清时代。“乞”字从汉魏时代就有“给予”义,明清时代直至现代,闽南方言中的“乞”字式都可以兼表给予和被动。
对于给予义动词如何发展为被动式标记的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江蓝生[4]、袁宾[5])认为汉语给予义动词及其所构成的双宾语结构在语义结构和语法结构上同被动式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直接发展为被动式,给予义动词也就演变为被动式标记。另一种意见(冯春田[6],洪波、赵茗[2])认为,给予义动词及其所构成的双宾语结构,首先演变为使役类结构,然后才由使役类结构进一步演变为被动式,也就是说给予义动词经历了使役义动词这个中介才演变为被动式标记。给予义动词从词汇意义上具有发展出被动标记的可能性。在很多情况下,进行的重新分析是以词汇意义为基础的。看下面这个例子:
(1)秦与天下罢,则令不横行于周矣。(《战国策·西周策》)
上面例子中的“与”字之所以有表示被动的可能正是因为“与”字有允许做某事的意义。当“与”字出现的语法环境是“NP+与+NP+VP”的情况下,这种重新分析在语义上就具有了可能性。现代汉语有方言(赣方言鹰弋片)使用“等”作为被动的标记,从“等”发展为被动标记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一点线索。“等”字含有“等待”意义,发展出了被动标记。给予义动词也有“让渡”意义,也有可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从给予义动词所出现的句法环境来看,给予义动词发展出使役用法和被动用法的句法环境基本相同,都是在兼语式的使用过程中进行重新分析的结果。而且这两者的表层结构都是相同的。
(2)“又一个丫环笑道:“别给宝玉看见。”(《红楼梦·第五十六回》)
这里的“给”既可以分析成使役用法,也可以分析成被动用法。这种内部结构一样的句子正是语言演变过程中发生改变的基础,从句法分析可以看出给予义动词可以发展出被动标记的用法,不一定需要经过使役用法这一中间过程。而且这两个用法的发展过程并没有出现交叉的现象。
二
“给”的给予义这一义项最早见于元代,不过这个时候“给”作为实义动词还非常明显,我们知道“给”在向使役或被动标记发展的过程中是伴随着语义虚化的。这个时期的“给”所出现的句法环境一般是以下四种情况:①NP1+给+NP2;②NP+给+直接宾语+间接宾语;③NP1+给+NP2+V;④NP1+V+给+NP2+V。
(1)师傅给免帖一张。(《老乞大谚解》)
(2)师傅给他免帖一个。(《老乞大谚解》)
(3)主人家就这般给茶饭吃。(《老乞大谚解》)
(4)我念给你听。(《老乞大谚解》)
从上面《老乞大谚解》中的代表性例子来看,这个时期的“给”所出现的语法环境有这几个特点:一是主语都是指人,具有比较明确的施事性,“给”的语义指向也都指向前面的动作发出者,而且“给”作为及物动词的语义非常明确。(第<4>例中的“给”的语义淡化是由于前面出现了一个实义动词“念”,在这里“给”可以看作是轻动词。虽然在语义上“给”存在向标记形式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这种句法环境下是不允许的。)二是“给”后面的宾语都是受事宾语,而且一般是人称代词或者是无生命的事物。三是在例(1)和(2)当中,“给”后面只带名词宾语,这样的句式没有发展成为被动句的可能性,因为其后面没有一个承担语义焦点的主要动词,在现代汉语中“给”的这种用法还是非常普遍。在例(3)和(4)中,“给”后面还出现了另外一个动词,这种句法环境是“给”发展成使役或被动句的语法基础。这种句法环境的“给”在后代的语言运用过程中,可以不经过使役这个中介直接发展成被动句。
下面我们来考察清代主要语料当中的“给”用法情况。在这些相对共时的语言材料中我们发现,“给”的句法功能很不一致,而且存在很多重叠和交叉的情况。“给”作为一个句子中的主要动词逐渐发展出了轻动词和介词的用法,实际上是语言演变过程中重新分析的结果。这里存在着一个虚化的链条,即动词—轻动词—介词,而要实现这种演化则需要一定的句法环境。
(5)给天下儿女吐一口气。(《儿女英雄传》缘起首回)
(6)倒把房子让给远房几家族人来住。(《儿女英雄传》第1回)
例(5)中“给”的“给予”义已经十分虚化了,基本上可以看做是轻动词,而正是这种语义上的变化使得句子还需要一个主要动词“吐”。句子的语义重点在后面的动词上面,“给”的地位被边缘化,这就为“给”发展到介词创造了条件。此外,这个句子没有出现主语(或者是主语不便出现),“给”后面是个有生命的宾语,正是在“NP+给+生命宾语+V”的结构下,“给”具有了重新分析的可能性。如果例(5)中“给”理解为“让”还算勉强的话,那么例(6)中的“给”就完全可以理解为“让”了,在这个句子当中,去掉“让”或者“给”的任何一个,句子的意思没有改变,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认为“给”具有使役的用法。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给”由“给予”义动词虚化成轻动词,进而发展成使役动词的用法应该具备一些句法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句子的语义重点发生偏移、句子一定要出现第二个动词以及句子的主语和“给”的宾语在语义上要有黏合性(如前面提到的“给”后面的宾语是生命度比较高的)。这在下面的例(7)中也得到证明。
(7)因此谋了一个留省销算的差使,倒让出缺来给别人署事。(《儿女英雄传》第2回)
例(7)中的“给”同样可以理解为“让”,而且也符合上面所提到的三个句法条件。不过这个句子不可能理解为被动句,因为这个句子说的是没有实现的事情,如果要理解成被动句的话,事情必须是已经完成了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给”的使役用法和被动用法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看下面的例(8)。
(8)就是天,也是给气运使唤着,定数所关,天也无从为力。(《儿女英雄传》第3回)
这个句子只能解释为被动句,这个句子的句子结构是“NP1+给+NP2+V”。NP1是V的受事,NP2是V的施事,V必须是及物动词,而例(7)中的V则可以是及物动词,也可以是不及物动词。而且两个NP之间的施受关系也存在很大的不同,这是使役句和被动句最根本的区别。当这两种句子的表层结构一致的情况下,就容易产生两种分析,这样的“给”就既可以分析成使役用法也可以分析成被动用法。看下面的几个例子。
(9)我的一件梯己,收到如今,没给宝玉看见过。(《红楼梦》第42回)
(10)千万别给老太太、太太知道。(《红楼梦》第52回)
(11)这里地方,毒蛇狠多,若是给他咬了,立刻就死,有药也不会救得来。(《白姓官话》)
以上三例中的“给”既可以理解为“让”,又可以理解为“被”,处于两可的状态。它们的句子结构都是“NP1+给+NP2+V”,在表层结构上和只能理解为被动句的例(8)是一致的,但是这里有两点重要的不同。一是例(8)中的V是及物动词,而且必须带上宾语(宾语可以前移),而例(9)、(10)和(11)中的V虽然也是及物动词,但是可以不带宾语,“看见”、“知道”和“咬”的宾语都可以不出现,句子仍然是自足的。二是使役句偏重于未然的事实,被动句偏重于已然的事实,如果将例(9)中的“过”和例(11)中的“了”去掉的话,这两个句子就只能理解为使役句,而不能理解为被动句了。我们将这一时期出现“给”的主要文献进行了考察,得出了这个时期“给”充当使役标记和被动标记的使用情况如下表:

“给”充当使役标记和被动标记的使用情况表
上表中的“给”在用作使役义和被动义的句法环境存在很大的不同,当然这两种用法也不是能截然分开的,因此就存在两可的情况。有些例句中的“给”只能当做被动标记,不能当做使役标记,这也说明了这两类“给”的具体演变过程是不同的。虽然它们的表层结构相同,但深层的语义结构肯定存在差异。
下面从主宾语的生命度的角度来看“给”的使役用法和被动用法的区别。我们知道汉语中的主宾语与施受事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施事也可以做宾语,受事也可以做主语。但是汉语也存在这种选择性的倾向,就是生命度高的更容易充当主语,生命度低的更容易充当宾语。因此如果“给”后面的宾语是人物的话,我们更倾向于将句子理解为使役句,而如果“给”后面的宾语是无生命的事物的话,我们则更倾向于将句子理解为被动句。
(12)甘心卑污苟贱,给那恶僧支使。(《儿女英雄传》第7回)
(13)你还敢争嘴?你做事件件都给人看破了,如今不敢用你了。(《学官话》)
(14)寡剩几担豆子没有丢吊,也给海水打滥上霉了,也是没干的。(《白姓官话》)
(15)你们在大清是哨船还是做买卖的船,怎么样给风飘到这里来呢?(《学官话》)
例(12)和例(13)我们更容易将其中的“给”理解为“让”,而例(14)和(15)我们则习惯将其中的“给”理解为“被”。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个事实,在“给”字发展出使役和被动用法的过程中,基本上有两条路径:一是“给予—使役—被动”,形成这一链条的句法环境是“NP1+给+NP2+V”,其中V是及物动词,而且宾语必须出现,NP2的生命度低,NP1在意念上具有做前置宾语的可能性。二是“给予—被动”,形成这一链条的句法环境是“NP1+给+NP2+V”,其中V可以是不及物动词,也可以是及物动词(宾语可以不出现),NP2的生命度高,NP1不一定出现。
三
桥本万太郎[7]认为汉语南北方言中的被动标记存在明显的类型上的差别,北方汉语被动式从“被”字句到“叫(教)”/“让”字句的演变可以说是北方汉语的阿尔泰化。汉语南北方言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北方兼用使动—被动,而南方却保有着“给”或由其同义词转化来的被动标志。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书面语中的被动标记是“被”,而口语中的被动标记是“叫”和“让”。根据《普通话基础方言词汇集》,现代汉语方言的被动标记大抵有以下一些:阿、挨、捱、把、把到、把得、把是、本、拨、拨辣、畀、吃、赐、传、得、等、兜、兜倒、逗、度、放、分、互、护、给、给得、跟、叫、教、尽、捞、拿、拿锡、拿分、拿乞、拿畀、分拿、分乞、分畀、分锡、锡拿、锡乞、锡畀、分拿乞、分拿分、拿乞畀、分拿畀、分乞畀、拿畀乞、拿给、拿跟、拿狭、乞、乞互、乞护、让、让把、让到、让得、让是、惹、讨、提、听、驮、要、与、予、约、遭、招、找、着等。
上面这些被动标记从意义上来看大体可以分为这几种类型:1.遭受义的动词兼用被动标记(如:挨,吃)。2.使役义动词兼用被动标记(如:叫、教、让)。3.给予义动词兼用被动标记(如:赐、给)。桥本万太郎认为“给”作为很多南方方言中的被动标记并没有发展出使役这一用法,这也可以佐证历史上的给予义动词可以直接发展出被动标记的用法,其中不一定需要经过使役用法这一中间过程。据《新华方言词典》[8]上的介绍,在南昌话中的被动标记是“等”,例如:(1)碗等我搭(摔)破了。(2)脚踏车(自行车)等人家偷泼了。但是在南昌话中“等”并不具有使役的用法,也就是说“等”并没有发展出使役的用法,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汉语被动标记的发展链条并不是唯一和单向的。在被动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就“给”字句来说,“给予—使役—被动”的发展链条确实存在过。但是通过对历史材料的梳理,我们仍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一部分“给予”句并没有经过“使役”这一个中间环节,而是直接发展成了被动句。从汉语给予义动词的使役用法和被动用法的发展过程来看,汉语给予义动词的被动用法完全有可能直接从“给予”发展到“被动”,而不经过“使役”这个中介。这两者句法结构的表层都是相同的,但是由于具体的句法环境的差异才促使它们演化道路的不同。
[1] 蒋绍愚.“给”字句、“教”字句表被动的来源——兼谈语法化、类推和功能的扩展[C]//语言学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26辑:67-78.
[2] 洪波,赵茗.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81-189.
[3] 桥本万太郎.汉语被动句的历史——区域发展[J].中国语文,1987,(1):43-48.
[4] 江蓝生.汉语使役与被动兼用探源[M]//江蓝生.近代汉语探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21-236.
[5] 袁宾,徐时仪,史佩信,等.二十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M].太原:书海出版社,2001:157-174.
[6] 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123-135.
[7] 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M].余志鸿,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56-78.
[8]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新华方言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95.
[责任编辑:王乐]
2014-04-19
刘海波(1989-),男,江西余干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
H136
A
1008-4657(2014)03-005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