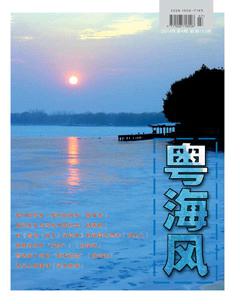读书的欲望与向度
李伯勇
一
欲望就是需求的愿望,它首先与人的生理需求相关,是人的本能。人有些欲望与动物的欲望相通,如吃喝拉睡、性欲等生存欲望,以及亲情爱情,它随着某种境况的递进(比如由小到大的年龄、睡眠不足、饥饿等)状态而强烈或衰退(如老年,吃饱、睡足、满足等)。附着于生理欲望的某种精神性,或叫做对这种欲望的感知状态,我把它称之为生存精神性,或本能精神性,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的“三年大饥荒”中,生产粮食的农民反而普遍挨饿,守着田块受饿,一拨拨人倒下去(当今有学者归之为营养不良而导致病发),这个时候为能填肚子而对树叶、树皮、野菜、观音土和蛇虫产生“吃”的欲望,就充斥“本能精神性”,什么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神圣理想来克服“生存困难”,都是宣传机器外加给乡村和农民的。从我的生活阅历和生存体验,一般民众(包括农民)在很长时间段都局限于这种“本能精神性”,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都在考虑怎样糊口,所谓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理想——诸如以阶级成分划分谁可多得食物,谁少食或不得食,表面上体现好成分者一种尊严,实际仍出于本能精神性——生存竞争意义上的排斥。
人之为人——人世间,就有个由本能精神性到超越精神性的演绎过程,人类文明得以建立和延展。所谓社会发展的停滞——生活的裹足不前,其实就是人长时间陷于生存精神状态,人的尊严和创造性价值被生存精神状态所制约,而呈一种萎缩或下降趋势。即使如此,人依然保持着基本活力,加上文化传统耳濡目染的传递,他仍有着从现有条件中捕获营养,不但应对困局,而且追求新的生活,即呈现超越性精神冲动。读书就反映了人类这种精神现象。
读书就是人读人写的书。孔子述而不作,是口头之书,他的弟子把他的言语记录下来,就成了书。虽是为帝王谋、吃帝王饭,也是人类欲望的一种。由于生产力低下,纸张阙如,印刷术姗姗来迟,所谓读书,也是止于皇家学人的授道,这跟有书摆在案前可以细读深读是不同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读书成了人类的基本行为。各式各样的学校就是读书的场所。
读书的欲望就包含生存性和超越性这样两种状态,是流动的。从“读书欲望”的本意(书籍文字具有抽象性),当然应该属于超越性精神状态,但在实际(现实)中却完全可能受制和受限于生存性精神状态,这是因为,本然的生存状态、特定的精神语境对其进行了无意有意地遮蔽。不过由于“活人”这个最关键的因素,“读书的欲望”的正面效力不可能消弭,通过“人”而不断延伸,破蔽——破生存之蔽和精神之蔽是必然的。
然而,我们在许多时候,读书的欲望总是在生存性精神圈子里徘徊,也就是老是被后者所遮蔽。
二
古代那个《漂母一饭》的故事,说的是韩信早年落魄遭人冷落,心里郁闷,这见证了韩信尚有尊严(超越性精神)意识,这样的尊严来自文化传统——士人传统被社会接受,成了中国——人类精神的有机组成,社会有了相应的共识,所以韩信固穷却还能守住一份自尊。他在城下钓鱼,饿得不行,一个在附近漂洗衣物的老妇人,一连几十天拿饭给他吃,他很高兴很感激,此时他基本处于生存性精神状态了,曾具备的超越性精神滑回本能性精神。他向老妇人承诺“我将来一定要重重报答您”,说明他心中的超越性精神尚存,其心灵尚未被生存性窘迫给彻底遮蔽。而这妇人从一开始就不是要得到报答,而是基于怜悯或恻隐这类超越性精神的人性之光。可见当时社会虽然贫困,人心中的超越性精神尚未被全然遮蔽。后来韩信显贵,以千金酬谢那位老妇人,此时的韩信就有践行“理想”(承诺)的“超越精神性”的意味了。
记载这个故事定格为“已知之理” 即已知之伦理,是后来的事——新朝记录前朝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其道德伦理的意味相当明显,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积淀。我们还发现,从古至今数千年,帝王将相公卿王侯“成长”故事所涉的精神阀域,几乎都局限于生存精神性和超越精神性之间徘徊,侧重伦理就是印证。进入当代,执政党“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宣传,仍富有这样的精神底色。就是说,在很长的时间段,它并没有真正解决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上述这类“已知之理”却被堂皇的革命理论摒弃了。当“吃饭”成了全社会的第一大事,“吃饭”也成了制敌的武器,什么读书,什么研究,在统治者看来,不就是吃上一碗饭?统治者一句“不给饭吃”,其实就是给“读书”限定了方向,也就是给“读书”平添了遮蔽,让读书始终黏附于生存考量。所以,在这样情境中的出版物,一般而言,其精神内涵皆为生存性质素所充斥。
说具体一些就是,到了现代,我们在较长时间把农民置于“求温饱”的境况中,农民——国人都停留在“本能精神性”状态。从20世纪20年代以苏俄为师开始鼓吹农民集体化(集体农庄),50年代到70年代搞中国式农民集体化,辅以城乡二元户口制度,农民被绑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走社会主义道路”,结果大批以种粮为业的农民惶惶然不脱粮荒,甚至饿死。且不说这时的“韩信们”当作旧时代知识分子被一次次批判和羞辱,“老妇人”几十天不断施饭的事也不可能产生了,因为她此时也贫乏得难以自保,渴望得到国家救助。我们的官员脸露喜色地说:我们的人民多好呀,多知道感恩呀。这也折射出官员的执政水平,或叫执政理念。几千年盛传的“民以食为天”的后面就填充着这样的精神底色,而且视为最高的执政境界(“解决了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并成为体察民情一个最基本的准则。以这种“朴素真理”自居的后面,其实是包含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在漫长的岁月里,作为人的精神特征或叫精神底色,都黏附于“本能精神性”上面的。
这又等于说,我们匍匐于“本能精神性”,也就是被“本能精神性”所遮蔽,不知道人之为人,人与动物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人不但有解决基本生存的欲望,而且在基本生存之上,要活出尊严,活出价值,就是活得像人。就是说,人应该有着更神圣、更值得追求的“超越的精神性”。人之为人,有本体性,更有主体性——今天这样的“主体性”已浮出水面。一部人类进化史、发展史或叫文明史,不就是一部人类不断展示由本体而主体——“超越精神性”即进步的历史吗?
记录人类这种“精神演进”,最可靠的是书籍;认识它,最可靠的也是读书。因而读书的天地应该是广阔无边的。
读书为解惑,既解生存之惑,更解“自我了解”“社会和自我设计”(自我超越)之惑,书籍烙下了人类这样的历史足迹,所以,“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不断迎面扑来的人类新境况中,人需要不断地认识自己;以果为因,读书让人类不断产生读书的欲望。只不过中国这类“史记”记载的多是“已知之理”。
对国人进行生存勘探,也只有在读书中才能实现。不过,在我们的社会,比如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的读书,书包越来越重,案头书堆得越来越高,那些“已知之理”的书籍大量地登堂入室,但对社会的演变——社会和人怎么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对社会的昨天和前天仍是一团乱麻,毋宁说,承载解惑的大书小书——“已知之理”的书籍倒对社会和人进行了遮蔽。
长期浸淫于既定精神格局的国人难以发觉,必须借助“他山之石”。这样的“他山之石”早已出现。
三
在我读域外书(翻译书)时,我想到了这个问题。
读书由书籍和阅读构成,读书也是人类不断地从“本能精神性”到“超越精神性”的星光大道。既然与人类“进步”息息相关,随着人类的生存生活情境的变化,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同时,人自身的潜能(包括对自身的认识)也得到激发,自然形成普世性的价值选择。不管特定的民族(国家)如何强调自己何等独特的文化特征,在历史的演进中,它的文化规范中必定越来越多地显现普世——求同的质素,在如此求同之下,方能有效有机地保存自己的特异。因而,“超越精神性”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螺旋式递进的,没有止境。
最近我花了不少时间读《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卷1,译林出版社,2012),此书收录了伯林1928—1946年的书信。它没有像我们社会习惯做的为尊者讳、为意识形态讳而突出什么、删除什么。伯林说:“我喜欢闲聊,喜欢描述事物,对人类及其本性有浓厚的兴趣,也喜欢探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这是健康正常的人类之心。此书就是一介普通人家寻常的通信,不是为刻意保留时代真相,恰恰保留了人的真相——时代真相,不是刻意突出“天才”“英雄”在幼年的不同凡响,恰恰保存了那个时代一个国家最一般的日常生活状态。
伯林在1928年12月给父亲的明信片,上面罗列了他学杂费、伙食费开销的明细情况,其中有这么一句:“我买书还需要很多钱,大约10英镑。”可见青年伯林不为他生存处境所囿,年幼的心灵就产生了“生活之问”和“世界之问”。他这句如此寻常的话包含了几层意思,一是伯林家解决了温饱;二是整个社会不是处在“生存”境况中;三是大学生思想活跃;四是能自由买书读书跟社会情境语境的宽松相宜相关。
伯林1931年9月给查尔斯的信更加证实了上述情形,还显现了他的阅读——精神个性:
我最终得到一本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入门》(1922年莫斯科出版)的书。书的作者是政治哲学家和苏联科学院研究所所长德波林。这部著作冗长、枯燥、缺乏睿智,但我兴趣十足地埋头阅读,它的论点越是糟糕反倒越让我感到趣味盎然。它的风格与其他在英国出版的哲学、经济领域的书截然不同。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它仿佛来自另外一个星球,那里的环境条件比地球更加残酷。但它宣传的信条却似乎比卢梭的思想更富有影响力。这本书除了作者令人乏味,一切都是那么有趣和令人兴奋,但它显然不适合外国人阅读。
说《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入门》的论点糟糕,当然是当时英国社会对此书的一般看法。当马克思明言“一个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大地游荡”,欧洲的发达国家如英国并没有对它围追堵截(倒是受到宣称国家社会主义的希特勒德国禁止)。伯林兴趣十足地埋头阅读,足见其视野之宽、精神触角之广。
伯林研究马克思也跟其人同样是犹太人有关;他喜欢读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作品,并加以认真比较,这当然与他幼年在俄罗斯生活过有关。除了希特勒的德国禁马克思的书(“我如饥似渴地一卷接一卷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德语原著……这个版本到了1933年就停印了,希特勒下令的”),欧洲大陆的精神气氛仍是相当宽松。
换言之,从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以及生活层面,年轻伯林感觉到了阅读上仍存各种遮蔽,因而他的阅读是破蔽式的阅读,在遮蔽中捕获微妙的营养。他以同情和理解阅读并研究时代的新思潮(他写了《马克思传》一书),逐渐形成了冷战时代不被看好的消极自由主义思想方法,他大力提倡多元主义——价值多元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他的写作是勘探“未知之理”——向着生活、向着未来敞开。
正如胡传胜在《伯林传》(译林出版社,2001)“译序”说的,“在20世纪的思想家中,以赛亚·伯林可以说是既无做大师的抱负,也自认为没有下过大师的苦功,却在有生之年成为当之无愧大师的人。”
在伯林身上,读书的欲望就是人类“超越精神性”的充分体现。他的书之所以成为当今和往后时代充满活力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正是他当年破蔽读书的结果。
四
对于阅读——精神活动,遮蔽无所不在。有的遮蔽不是人为的,比如大气层对人类的制约;有的遮蔽是人为的,比如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诫和设限。根本上,人的精神自由——破蔽行动在于人自己,人是靠自己而不是靠别人做出阅读上的选择。
当今物质丰富,生活水平提高,但国人读书少了。如果对读书进行量化分析,这读书之“少”中,又为“如何发财”“如何健身”“如何娱乐”的本能精神性所充斥,超越精神性欠缺的“阅读匮乏”成了我们社会的普遍症候。这跟前些年饥饿年代也是政治高压年代的读书的性质是一样的。在世界面前,中国是头睡醒的大狮子,可“狮子”内里的精神质素依然为“本能精神”所囿。
真正的读书就是人对超越精神的渴求和探寻。这个意义上的阅读匮乏对我们社会可不是吉祥之相。在号称世界第一的书籍大国,“阅读匮乏”暴露出我们社会的精神本相。阅读匮乏导致或见证我们社会“超越精神性”受到阻遏。
书籍大国遮蔽了阅读匮乏,由此,我又联想到我们社会无所不在的遮蔽问题,以及被遮蔽的精神之痛。与其说“阅读匮乏”被重重遮蔽,不如说我们社会的精神之痛被重重遮蔽。
太多的人体会不到这种“精神之痛”。(显然,伯林在他所在的欧洲大陆就没有这种“精神之痛”,但他后来作为英国外交官出访苏联,在拜访苏联作家时感觉到了这种“精神之痛”。)
自然我们又会发现,我们社会的昨天和前天,人们不也陷入本能精神性不可自拔么?我们的精神质地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又等于说,相当程度上我们是没有凭借“读书”所产生的张力,对自己曾经的年代毫无真切的了解。进一步追问,是无“书”,也就是没有揭示真相的书可读。这么着,我们也就能从书店(市场)那些琳琅满目、汗牛充栋的书中,看出对“阅读”构成了遮蔽。
扩大地说,物质性生活形态对读书构成了一重遮蔽。这种现象应该是本然性的社会现象,因为物质生活总是第一性的。
演进的人类社会总会出现一部分人(智者、学人)探寻生存本相,探寻“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们看书写书教书——带动社会读书,也就成了“破蔽”行动,首先就是破物质生活之蔽。最基本的物质性生活就是求生存求温饱,淹滞于此状态的民众对读书不会有欲望的。长期的普遍贫困会给人给民族的心灵造成内颓之殇。所以,现在人不读超越性精神之书,有着“穷怕了饿怕了,抓住一切机会发财致富”的生存性考虑,这是物质性遮蔽和自我遮蔽的双重遮蔽。
上面说的为“发财”“健身”“娱乐”的读书,给真正的读书同样构成了遮蔽。
一个社会为什么盛行这样的“遮蔽”,与它的“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相关。意识形态又可分为世俗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人的文化习惯、文化心理及市场意识可归于前者,现实中的物质生活和娱乐生活同样可归于前者;后者以权力为内核,在权力独大的社会,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解释(取舍)贯穿着权力意志,而权力是受少数人操控——权力者总是声称代表国家和人民,其实代表的只是部分社会成员,这部分社会成员成了既得利益者,他们合谋,以“正面”的方式,通过其操控(受控)的主流媒体和主流学人把“读书”引向与无碍权力(包括颂扬权力)的方向,显然,他们是能够容纳世俗意识形态的——但在革命之初,他们是激烈地批判世俗意识形态(唯恐民众不激进、不革命)。他们操控下的书籍标榜显示唯一的真相和真谛,恰恰遮蔽了历史和人(心灵)的真相。
政治意识形态与世俗意识形态合流,也就是香港学者杨慧仪说的,“国家、官僚机构、市场和家长统治形成串联式的权力”(《一九九〇年代的小说与戏剧:漂泊中的写作》),是今天中国的现实,而不是中国“向来如此”。串联式权力——权力合流即泛化的权力,且不说伯林和他的欧洲大陆,就说中国的传统典故(有政统、道统和学统之分),也没有过这样的“合流”。在毛泽东时代,基于彻底打倒并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追求纯粹革命——创造一个全新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世俗意识形态中诸如人性人情、社会常识,是持警惕和坚决批判态度的,也就不间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鼓吹阶级亲民族恨,以此解放全人类。在执政党操控国人一切生活生产资料、思想资源、舆情工具——极端封闭的情势下,政治意识形态具有纯粹性(跟纳粹德国一样)和高耸性。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基于原有思想根基的政治意识形态很快又发现了“新的敌人”:境外敌对势力,境内发出质疑之声的自由派。它对那些基于生存欲望的“本能精神性”需求,倒是不那么严阵以待的。所以,主流媒体强调“扫黄”,而黄赌毒却全面泛滥,“打非”(非法出版、非法媒体)却是认真的,宁左勿右。
因而有必要提到读书的另一重遮蔽,就是拒绝对“昨天”真相的检视。针对欧洲,安娜·阿伦特曾发出警示:“我们处在忘记过去的危险中,而且这样一种遗忘,更别说忘却的内容本身,意味着我们丧失了自身的一个向度,一个在人类存在方面纵深的向度。因为记忆和纵深是同一的,或者说,除非经由忘记之路,人不能达到纵深。”(《过去与未来之间》,译林出版社,2011)所以,读书还是超越既定政治和串联式权力意识形态,保持人类记忆和纵深——自身一个向度的可靠路径。
在欧洲检视前德国、前苏联已寻常化——伯林时代精神氛围继续延伸,而我们对自己的百年真实历史仍是三缄其口,比如“大饥荒年代”,“文化大革命”,无数大人物小人物的悲剧,无数大家庭小家庭的悲剧,上溯到“全民族抗战”,我们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曾经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的片面性解读上,这种以片面却貌似全面的解读已构成遮蔽。其实这种“片面性解读”——相关书籍所展示的,以及相关书籍背后的思维套数,仍是教人如何匍匐于“生存性精神”(包括进行生存性恫吓),因此,民族心灵的廓大仍是个问题。
继续辨识,政治意识形态与世俗意识形态合流,是以前者为主的,所以在“合流”的表面之下,是与世俗中那种基于传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秩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合流,而不是与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重、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朴素民本思想合流,而民为重、社稷为重、君为轻恰恰是世界大潮的渊薮。
从权力者立场,他们遮蔽历史的动机当然来自现实的利益考量,遮蔽历史跟遮蔽现实是同步的。所以国人天天生活在真实中反而看不见真实,或者说,他们只知身边一鳞半爪的真实,而无从知道整体的真实。只有知道整体真实,才能了解人的真实处境。书籍和读书恰恰是揭示和“抵达”真实的重要途径。现代化、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民族多样化正是当今了解整体真实的基本视角。
然而我又可以看到,一个正常的社会,向着未来,遮蔽和破蔽是同时进行的。
五
在“破蔽”仍是个社会话题和个人精神话题的情势下,自然就有个“从遮蔽中捕获微妙营养”——读书欲望的向度问题。“从遮蔽中捕获微妙营养”就呈现一种读书的向度。
我们又能察觉,诸多专家学者正人君子在宣传机器上的高头讲章,其实没别的新意,就是教导国人如何陷入“本能精神性”自乐其乐,说得不好听,他们是既帮忙又帮闲地营造“猪圈”,让“猪”在“圈”里享受快乐,让握有权力的高人为“猪”做主,并要“猪”认可这一“宇宙的真理”。至于猪圈里的大猪小猪穷猪富猪会叫的猪不叫的猪高贵的猪卑贱的猪,快乐或痛苦的呻吟,呼叫或沉默,那是无须计较的,专家学者替权力者说出一句俗语“你们有吃有穿还闹什么闹”就一通百通了。显然,这类训诫式文章起到了遮蔽现代国人耳目的作用。
正如杨慧仪在《一九九〇年代的小说与戏剧:漂泊中的写作》说的:“在新经济里,信息技术与通讯成为最重要的一环,因为它们是构成新消费模式的主要工具。某些书籍和杂志还是不能在大书店里买到,但都市人却每天能从互联网上得以有关消费品的最新消息。同时,参与社会运动的人和学者,他们通过电子邮件和网站建立讨论小组,交换信息;还有很多关心身边事情的大众在网上冲浪和浏览。如今,为独立自主进行的斗争,不仅要靠硬拼,还要靠灵敏的思维;在中心越来越难以维系的世界里,硬碰硬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的颠覆形式。另一方面,国家已不再是唯一的集权力量。”(载《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5期)就是说,读书所面临的破蔽,是多重的,而且是混合的,从破蔽里捕获的营养也是多重的,而且,具有一定向度的读书是形成并保持灵敏思维的必经途径。
互联网与其说是个全球化时代的新技术,不如说是不可阻遏的人类阅读自由——精神自由的一个巨大象征。
自在自为的读书——真正的读书就成了破蔽的精神之旅。在今天既开放又封闭的情形下,从遮蔽中捕获营养——遮蔽(禁忌)反而产生阅读的张力,真正读书的要义就在于此。真正的读书一旦坚持,我们就会发现,许多良知学者良知作家的书里,“破蔽”正在进行,已构成当下和未来精神营养的来源,已展示新的精神天地。
(作者单位:中共江西省上犹县委宣传部)
[注:此文题目参照了《陈先发近作选·忆顾准》诗句(《钟山》2013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