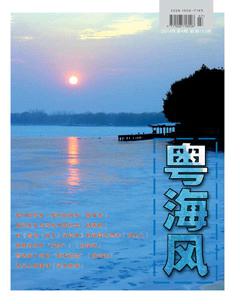鲁迅与托派:互为“疑障”的隔膜
宋欢迎
在“两个口号”论争中,就周扬等人倡导的“国防文学”,托派署名“徐行”者在论争开始前就曾有批驳,鉴于此种情况,即如茅盾所言,在鲁迅等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后,“周扬他们趁机放空气说,不但托派反对‘国防文学,鲁迅派现在也反对‘国防文学了,用意是把鲁迅和托派并列,是十分恶毒的玩弄政治手腕”。[1]然而,恰巧在“两个口号”论争开始后,6月3日,从北大求学始就崇拜鲁迅的托派临委书记陈其昌(化名陈仲山)写信给鲁迅,在攻击中共新政策的同时,吹嘘托派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试图争取鲁迅的同情与支持,趁机将鲁迅拉到托派一边,共同抵御夹击托派的两种势力:国民党和共产党内遵奉斯大林主义的王明等人。关于此事,王凡西回忆如下:
鲁迅始终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永远是一个同情被压迫被践踏者斗争的战士,因而即便不是思想上,至少在感情上他乃是阶级斗争学说的服膺者。何况,在他思想和行动的逐渐成长中,反对各式各样国家主义文学的斗争,曾起了决定性作用的。现在(1936年),提倡了多年的“普罗文学”,与国民党御用文学及所谓“第三种人”等作了长期尖锐斗争之后,忽而要掉转枪头,化敌为友,从事什么“国防文学”了,在他心里当然不会舒适安然的。于是引起了争论,而且这个“内部”争论,传到了我们耳中。陈其昌听到了这消息后非常兴奋,于是写了一封信(此信后来附印在鲁迅的复信后面,被收入全集中),附上《斗争》及另外几册中译的托洛斯基的小书,由内山书店转送鲁迅。[2]
6月9日,冯雪峰代鲁迅拟定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斥责托派“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的理论“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与此相对,赞同并支持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的“一致抗日论”,而且颂扬“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3]况且此前曾有署名“少离”者讽刺鲁迅为托派中的一员:“鲁迅在共产党文总内,曾负过一个时期相当重要的责任。但共产党内的斗争,尝使这位老翁‘生气。鲁迅翁遭受了布尔什维克铁面无情的滋味,而且他在干部派下,决难有开展的希望。所以他在几度离合之后,便与干部解缘(?)了。一边解缘,一边自然就有人在拉啦。要在残灰中做个领袖,是比较容易的,鲁迅翁便改唱托派的论调了。”[4]所以,鲁迅在此时也需做个明确的政治表态。[5]6月10日,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鲁迅重新阐释了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的用意:
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似乎糊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梦”者,我想,也是极糊涂的昏虫。[6]
当时,陈独秀等取消派反对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为那是投降资产阶级,这其实是极“左”的思想,与此相反,周扬等人以为既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么就应当解散“左联”,无需再提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文艺界统一战线中的阶级领导权,否则会吓跑同盟者,这又是偏“右”的思想。所以,鲁迅提醒必须既反“左”又反“右”,而之所以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就是为了坚持左翼文艺在文艺界统一战线中的核心地位和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革命领导权,亦即将“民族的立场”和“阶级的立场”统一起来。所以,在鲁迅看来,陈独秀等取消派以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的观点,其实是非常“糊涂”的。
在狱中的陈独秀赞成托派的观点,得知陈其昌写信给鲁迅,大为恼火,批评托派临委何以对鲁迅发生幻想,在他看来,鲁迅之于共产党就如同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已然丧失了独立的人格。陈独秀对鲁迅的判断,根本上基于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分析。当时中共内部在中国经济性质这个问题上存有巨大的分歧,“干部派”认为除开江浙等局部工业发达地区外,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生产落后,封建生产方式占绝对优势,因而“决不能从海外找资产阶级的基础,从天上掉下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来”,而且,帝国主义只是妄图将中国变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不但不助长中国的工业,反而“极力扶持封建势力,压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致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无法抬头。[7]与此相对,“反对派”(“取消派”)认为资产阶级在中国已经取得优势,中国经济的性质已是资本主义,1929年8月5日,陈独秀在致中共中央信中曾指出:
其实,中国的封建残余,经过了商业资本长期的侵蚀,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已显然不能够以农村经济支配城市,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之根本矛盾,如领主农奴制,实质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剥削农民早已成了它们在经济上(奢侈生活或资本积累)财政上的(维持政权所必需的苛捐杂税)共同必要……而且,中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之革命,无论如何失败,无论如何未曾完成其任务,终不失其历史的意义,因为他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他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之过程中,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他为自存计,势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就是说不得不下全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的经济势力,做他们各个区域内的统治基础。它们所以现在尚能残存,乃因为资产阶级受了工农革命势力的威吓,不但不愿意消灭封建势力,并且急急向封建势力妥协,来形成以自己为中心为领导的统治者,并且已实现了这样的统治,就是国民党的南京政府。[8]
需要指出的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反对派”(“取消派”)受到托洛茨基等人观点的影响。亲托洛茨基的拉狄克[9],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是位中国革命问题研究专家,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曾指出:“中国商业资本主义已经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的封建主已经完全没有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因而集中到商业资产阶级手中,他们剥削的目的,与封建主不同,因为后者不知道货币经济,他们的目的不过为得黄金,装饰品,美女而已。因此中国无所谓封建势力,只有商业资本家。”[10]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与斯大林的大纲》第三十九段发表了相似的见解,反对布哈林对中国封建势力的重视,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山穷水尽的形式”[11]。结果,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陈独秀由于把国民革命视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当前又只能进行这种革命,在阶级关系上,容易接受并执行斯大林的对资产阶级让步、给它当苦力的政策。同时在革命方式上,陈独秀对军事北伐的消极,又反而成全了斯大林全力支持蒋介石的路线。于是把革命领导权特别是革命武装和北伐战争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成了斯大林和陈独秀共同的轨迹。同时,由于二人都自欺欺人地把国民党视为国共两党和四个阶级联盟的党,因此他们在推行这条路线时自认为是应该的,而不认为是对革命对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背叛。瞿秋白认为对资产阶级应该斗争,应该争夺革命领导权;同时又坚决支持北伐和土地革命,坚决不退出国民党。这使他也成为国际路线的执行者,在大革命后期和失败之后成为陈独秀的替代者。” [12]
事实上,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在“国共合作”等问题上的分歧与斗争由来已久,如“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托洛茨基曾经愤怒地指出:
斯大林应为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政策承担责任并要共产国际也承担这份责任,正如他不止一次应为……蒋介石的政策……承担责任一样。我们与此毫无共同之处。我们不想为武汉政府和国民党领导的行为承担丝毫责任;我们紧急建议共产国际拒绝这份责任。我们要直接对中国农民说,如果你们不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而是追随国民党左派的领袖的话,他们……必将背叛你们……将十倍地同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人和农民。[13]
另据史唐回忆:“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卷入革命是暂时的、投机的,它必然要动摇、叛变,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绝对保持独立;而斯大林则认为国民党是群众组织,是工人、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四种成分的联盟,中国共产党应该直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即‘党内合作方式),这样有利于争取群众,争取领导权,打击右派,并领导这个组织夺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当时就是这样执行的,许多党员和党的干部,公开参加了国民党并进入其各级领导机构。”孙中山逝世后,托洛茨基已经预料到“国共合作”形势将发生变化,曾力主中共立即退出国民党,防止“中国资产阶级的叛变”,但遭到了斯大林的驳斥。后来,在斯大林的各方运作下,斯大林和“反对派”(第一个是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莫斯科反对派”,第二个是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代表的“列宁格勒反对派”,两个反对派后结成“托季联盟”)的斗争,历时五年,到1927年年底联共(布)十五大时,终于尘埃落定,75名反对派被开除出党,斯大林取得全面胜利。[14]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中国革命变成了他们争论的一个问题,但是“他们双方都不是出于关心中国革命的最大利益而进行争论,而不过是用争论的成败作为赢得(对托洛茨基而言)或者保住(对斯大林而言)权力的一种手段”。平心而论,“斯大林——布哈林领导轴心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即使以表面价值而论,也远非完美无缺。而在付诸实践时,斯大林和布哈林就更是错误累累,而且情节严重”,与此相对,“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中国革命的某一特定阶段所发出的警告,以及他们在某些问题上建议采取的政策,并非概不足取”。然而,“双方都热衷于权力之争,都不愿意冷静考虑对方的主张,并开诚布公地加以讨论。他们各自坚持己见(或者说是偏见),而真正受害的则是中国和中国人民”。[15]
因此,1927年共产党遭受到惨重的损伤,同共产国际执委会(斯大林、布哈林等)的决议密切相关,而斯大林等却把共产主义在中国失败的过错推诿给中共领导陈独秀,谴责其未能正确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实质上,斯大林共产国际的路线有力地支持了迅速壮大的资产阶级右派蒋介石集团,这才是把革命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致使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尽管托洛茨基对“国共合作”的隐患早有预感,但是受斯大林及共产国际的蒙蔽,继陈独秀而上任的瞿秋白依然未能认清共产国际的误导。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1931年年底,瞿秋白作文《陈独秀的“康庄大道”》和《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批评陈独秀缺乏阶级意识,堕落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托洛斯基、陈独秀的真面目,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都冒充着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派在1927年武汉时代自己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实行机会主义,等到那次革命失败,却来说什么‘共产国际断送了中国革命。这叫做死不要脸。”[16]鲁迅对苏联情况的了解基本上全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因此,他对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共产国际以及中共内部政治斗争的实际情况是不了然的。换言之,托洛茨基以及中国的托洛茨基派于鲁迅而言都是“疑障”[17]。所以,陈独秀之于鲁迅,鲁迅之于陈独秀,双方在当时是隔膜不相知的。
虽然陈独秀反对陈其昌抱着幻想拉拢鲁迅,但陈其昌看到他写给鲁迅的信和鲁迅强烈反驳的回信公然出现在杂志上后,陈其昌难以压抑自己的“愤懑”,7月4日,他又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开篇毫不客气地将鲁迅痛斥了一番,认为鲁迅“拿辱骂与诬蔑代替了政治问题的讨论”,并称鲁迅“回信的态度是‘中国现代文豪之思想与行为的最最无情的讽刺!”接着,陈其昌分析当时中国政治形势,指出:
中国斯大林党遵奉第三国际的命令,认为一切阶级可在日本压迫之下联合反抗,因而他们派代表,到宁、粤、香港与刽子手军阀官僚们去接洽,并高喊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联合战线。抗日是目前中国民族的生死问题,如果各阶级各党派真能联合起来挽救了民族的危亡,那自然是当欢迎的。然无奈这是一种幻想,事实上,尤其在目前的中国办不到,即使变相的办到,其中还含有最可怖的前途。中国的主要阶级,如各派资产阶级与工农劳动阶级,后者与前者是死敌,对于抗日问题,则根本说来,这两阶级是背道而驰的——资产阶级以不抗日为生,而工农劳动阶级以抗日为生。详言之,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是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相依而存的,所以根本上它不会抗日。在事变发展中,尤其在受到工农大众的威胁时,它只有降日。它与帝国主义固然有利益的冲突,但他们之间的这种冲突比之它们与工农大众的利益冲突,小得不算什么。所以在工农未起来时,资产阶级在口头上甚而在行动上会表示抗日,但当工农起来而威胁到它的生存线时,它与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将降到近于零,它们会联合起来对工农来一次大屠杀。这就是我们亲身经过的“四一二”。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各阶级关系的根本认识。而且中国目前的阶级关系又与别国别时期的不同;现在的统治政权就是在“四一二”的屠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它更害怕民众起来,更依赖帝国主义;宁坐看华北丧失而不敢放松它对“红军”对抗日民众的压迫。革命政党的战术必须建立在这种对阶级关系的根本认识上,才能应付万化千变的形势。本此,中国布列派指出了“必须打倒资产阶级国民党才能达到抗日胜利”之大道。
那么是否可以就因此而认为资产阶级各派绝无抗日作用了呢?只有蠢才才会这样想。资产阶级可以因时因势而常向“左”摇摆;在它们真有抗日行动时,我们在战略上决不应该离开我们的基本认识,在策略上也不能离开太远。我们必须设立堡垒以预防“四一二”之猝然到来;这即是说,无产政党必须时刻揭明自己的旗帜不使与资产阶级的混淆,时刻指示给工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与叛变性,使他们时刻提防同路人,时时团结并扩大本身的力量。这样,仓促遇到“四一二”屠杀时他们才不至于措手不及,致认不清敌人和自己人。这就是中国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抗日运动的道路之大略。[18]
陈其昌所言的上述这些革命的“战术”与“战略”,要而言之,便是坚持“反蒋抗日”以避免重蹈“四一二”的覆辙。不难发现,就这个问题而言,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托洛茨基派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观点是一致的。而如前所述,鲁迅等左翼文化界人士也一再强调,坚持无产阶级在联合战线中的主体性和确保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其根本用意也是为了防止重演“四一二”的悲剧而进行真正的“反蒋抗日”。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虽然陈其昌对鲁迅的批驳相当激烈,乃至在信末还向鲁迅叫板道:“你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把我的信与你的答覆故意以那样的标题公开发表,并且还不仅发表在一个杂志上。而你那公开回信的内容,又不谈我向你诚恳提出的政治问题,而只是由我而诬辱到中国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并诬蔑到托洛斯基,你是讲‘道德的人,你既然这样做了,我就不得不再诚恳的请求你把我这封信公布在曾登过你的回信的杂志上。标题用《托洛斯基一分子对鲁迅先生的答复》,这里,我在热烈的企待着鲁迅先生的雅量,革命者向来不回避堂堂正正的论战,你如愿意再答,就请摆开明显的阵势,不要再躲躲藏藏的造谣诬蔑。你的话在中国人中是有吸引力的,如出言不慎,那必将遗害青年,必损你的盛名,并有害革命。”[19]但鲁迅只在7月7日的日记中写下“得陈仲山信,托罗茨基派也”[20]几个字,此后再也未理陈其昌的挑战,究其原因,除了鲁迅以“战士的思维”[21]抵挡那种特殊境况下的种种恐怖之外,还有就是鲁迅对政党内部的风云变幻是隔膜的,但他基于自己切身的经历,始终坚持着“反蒋抗日”的革命策略。鲁迅逝世一周年之际,陈独秀发文《我对鲁迅之认识》,改正了先前对鲁迅的误解:“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死。”[22]由此可见,陈独秀最终还是明白了鲁迅的本意。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1]茅盾:《我和鲁迅的接触》,鲁迅研究资料编辑部编:《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72页。
[2]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0年,第207页。
[3]鲁迅授意、O.V.(冯雪峰)代拟:《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同刊于《文学丛报》第4期和《现实文学》第1期,1936年7月。
[4]少离:《鲁迅与托派》,上海《社会新闻》第7卷第2期,1934年4月。
[5]冯雪峰曾回忆指出,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时期的政治态度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据我了解,当时文艺界之外的广大群众对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大多数是不大了解情况,也不大注意和感兴趣的。他们注意的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鲁迅拥护毛主席党中央政策的态度和立场。鲁迅几篇文章所发生的巨大影响首先也是在政治上和在群众中。(当时文艺界中也有不少人对于口号论争不感兴趣,他们注意的也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鲁迅的态度和立场。)”冯雪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间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零碎参考材料》,《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57-258页。
[6]参见鲁迅口述、O.V.(冯雪峰)笔录:《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同刊于《现实文学》月刊第1期和《文学界》月刊第一卷第2号,1936年7月。
[7]参见李立三:《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布尔什维克》第3卷第2、第3期合刊,1930年3月15日。
[8]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国中央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727—728页。
[9]拉狄克的观点当时在中国具有广泛的影响,如拉狄克的《中国革命史》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编印的《中国19世纪与20世纪之革命运动史》所确立的“侵略—革命”模式,把中国近代史看做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人民起而反抗的革命史。中国的历史学家李鼎声(孪平心)在1934年撰写的《中国近代史》就是直接来自这一叙事模式。盛岳回忆指出:“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卡尔?拉狄克教中国革命运动史。这门课包括对中国历史一般的论述,可是课程的重点自然是近代革命运动。拉狄克的观点同中国共产党历史家范文澜极为相似,也许范文澜就是从拉狄克那里搬来的。范文澜坚持说,全部中国历史是一部农民革命史。”范文澜曾写道:“从西周初期到现代,中国历史延伸了两千多年。从现象上看,史料浩如烟海,说明历代兴亡盛衰,乱治交替,而乱多于治。然而本质上问题只是一个,即土地所有权问题,也就是农民反对地主阶级,争取土地所有权的斗争。”参见〔美〕盛岳著、奚博铨等译:《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65页;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简编》,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0年,第5页。盛岳还说过:“事实上,拉狄克在1925年3月14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孙中山博士的文章,他在文中声称,太平起义的领袖洪秀全是孙中山的先驱,他在中国革命史课中对这一观点重复了许多次。”关于此,朱承志在其所著的《近代史》中曾说,拉狄克写了一本题为《太平起义》的书,断言太平起义是一次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成分的农民运动。而范文澜的思想与拉狄克的这一论点近似,认为在第二阶段资产阶级团结正在争取土地的农民。参见〔美〕盛岳著、奚博铨等译:《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88页,注②;简又文:《马克思学派的太平天国史观》,台北《问题与研究》第2卷第3期,1962年2月20日。除此之外,宋云彬在《鲁迅先生往那里躲》的开篇,引用拉狄克的言论:“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宋云彬:《鲁迅先生往那里躲》,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1927年2月。
[10]〔俄〕拉狄克:《中国革命史》,转引自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黄山书社,2008年,第163—164页。
[11]〔俄〕托洛茨基:《中国革命与斯大林的大纲》,转引自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黄山书社,2008年,第164页。
[12]唐宝林、陈铁健:《陈独秀与瞿秋白·序言》,团结出版社,2008年,第9页。
[13]〔波〕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著、周任辛译、刘虎校:《被解除武装的先知 托洛茨基:1921-1929》,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365页。
[14]参见史唐:《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回忆》,《百年潮》,2005年第2期。
[15]参见〔美〕盛岳著、奚博铨等译:《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87页。
[16]秋白(瞿秋白):《托洛斯基派和国民党》,《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6期,1931年11月10日。
[17]孙郁曾指出:“我相信鲁迅对苏联情况的了解是含混的,他还不知道个性主义在苏维埃政权中的厄运。直到他死,托洛斯基的存在对他也仍是一个疑障。虽然他受到了瞿秋白、冯雪峰传递的信息的干扰,知道了托氏的流放,受挫。可他对这位多才的斗士的理解,多基于中国社会的经验,而不是俄国的经验,于是在晚年,终于与托洛斯基疏离了。”孙郁:《鲁迅与陈独秀》,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2页。
[18][19]陈仲山:《陈仲山致鲁迅》(1936年7月4日),鲁迅博物馆编:《鲁迅研究资料》(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9—171、第175页。
[20]鲁迅:《日记二十五》,《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11页。
[21]关于鲁迅与“托派”的纠葛,孙郁曾发表过这样的看法:“鲁迅的卷入对‘托派的批评风潮,并非像陈独秀那样染有政党政治的痕迹。他对自己对立面的理解,大多在艺术理论的层面上,纠葛的是文学理论与口号上的问题。《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不过是被动地一种政治表态,涉及的是中国自身问题。我以为在全球左翼势力遭受围剿的时刻,他考虑的首先是保卫左翼(包括苏联),而不是相反。在随时有死亡威胁,恐怖笼罩一切的时候,只会有战士的思维,用学人的目光要求鲁迅,那是不得要领的。”孙郁:《鲁迅与陈独秀》,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6页。
[22]陈独秀:《我对鲁迅之认识》,《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5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