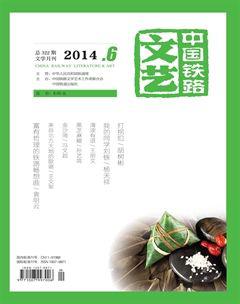清波有语
王丽文
一
深秋,晶莹剔透的寒霜,装点了含蓄雅致的白桦、蓬勃墨绿的侧柏、耀眼金黄的落叶松与酒红沉醉的枫树……五色交织的长白山脉层林尽染,多彩的秋叶如纷飞的蝶,舞向了云水之间。
残阳如血,夕辉晚照,东北抗联第五军一师仅存的八名妇女团战士与百余名官兵,在历经三个多月的千里西征与激烈战斗之后,来到了乌斯浑河岸畔,准备渡河向北经马蹄沟、碾子沟,到依兰县土城子一带牡丹江边的克斯克山区,去寻找抗联二路军总部及第五军部。
连绵的秋雨,将原本几十米宽的乌斯浑河河道,扩展到了数百米。没有渡船,也看不见渡口,湍急的浊浪,咆哮着一往无前。天色已晚,过河的希望极其渺茫。已经连续27天粒米未进的战士们,一直靠着白水煮蘑菇、煮野菜度日,忍着饥饿行军打仗。眼下,衣衫褴褛、疲惫至极的战士们,只能在乌斯浑河与牡丹江的交汇处柞木岗山露营,等待天亮时再做渡河的打算。
秋夜,荒无人烟的山谷里温度降到了零下十度左右,冷气袭人。为了御寒,战士们拢起了篝火。篝火旁,八位女战士,背靠背地打起了瞌睡。
23岁的指导员冷云怎么也睡不着。她侧耳倾听着乌斯浑河的流水声,遥望着天穹上亮晶晶的星星。流水声里,传来的似乎是女儿奶声奶气的呼唤;一闪一闪的星星,渐渐地变成了女儿一眨一眨的毛茸茸的眼睛。屈指数来,女儿现在有半岁多了。想起女儿,冷云的心就会生出负疚,负疚自己未能尽到做母亲的责任。西征前那个月明风清之夜,她强忍着丈夫牺牲的悲哀,把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交给了军部副官谢清林,送到依兰县的一家朝鲜族老乡抚养。她一只手搂着女儿,一只手轻轻地拍着女儿。女儿在悲伤的《摇篮曲》中入睡,稚嫩的脸上还挂着泪滴。她知道在枪林弹雨中奋战,生命转瞬即逝犹如家常便饭。此行也许就是与女儿的永久分离。没有了爸爸,再没有了妈妈,女儿是否能够平平安安的长大?
冷云深深知道,战争是越来越残酷了。七七事变之后,日伪当局为了镇压东北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动员了6万余的兵力,对乌苏里江、松花江、黑龙江下游进行空前规模的大讨伐。他们强制推行了“集团部落”、“保甲连坐”的政策,威逼群众归并大屯,到处以深沟高垒严密封锁,切断了抗联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部队的给养经常中断,弹药和军需品极难补充,东北城乡的地下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为粉碎敌人企图“聚歼”抗联部队的阴谋,抗联第二路军主力于1938年5月,向五常、舒兰一带西征,以期打通与南满、热河方面抗日部队的联系,开辟新的游击区域。
美好的愿望常常被冷峻的现实所打破。在“内无给养,外有追兵”的困难境地中,经过几个月的辗转游击的西征部队,已由出发时的680多人,减员至 100余人,西征的主要领导人、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叛变投敌,抗联第4军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相继牺牲。30多名抗联女战士只剩下了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原第四军被服厂厂长安顺福,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慧民、李凤善。这样下去,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年轻的战士要血洒疆场?
冷云的思绪,被躺在怀里的小战士王慧民的梦呓打断了。小惠民的父亲是抗联第五军军部的副官,就在前不久的一次战斗中,王副官倒在了冰冷的血泊中。想到这里,冷云不由自主地抱紧了小惠民瘦弱的身躯。
“女人是为爱情而生的”,爱情是残酷战争中蕴藉于心中深处的一抹春色。
此时此刻,17岁的郭桂琴,满怀对恋人冯文礼的思念,仰望着天上的半轮冷月,憧憬着抗战胜利的那一天,能够与心爱的文礼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白头偕老。思念与憧憬交汇,恍恍惚惚的她,真的看见了带着大红花的文礼,骑着高头大马来迎娶她。笑眯眯的文礼亲手挑起了红盖头,把她抱到了马背上。睡梦里,她高兴地笑出了声。笑声中,她找到了去年冬天冻掉的两个脚趾头。渐渐地,冻僵的双脚暖和了,原来是文礼把她的双脚放到了怀里,那一刻,电流暖到了全身。
漂亮的杨贵珍,平日里总是喜欢在头上戴一朵山野里的花。此时,她思念的是随队西征的丈夫宁满昌,不知道他的枪伤是否还有阵痛?而安顺福,正在猜想着西征前送给老乡的儿子是否已经安睡?
朦朦胧胧的战士们没有想到,篝火在带来温暖的同时,也带来了致命的危险,战争,不仅无情地剥夺了她们享受亲情、向往爱情的权力,生命也已经接近了死亡。
二
夜半,一双邪恶的眼睛,发现了山谷里跳跃的篝火,紧接着日本守备队收到了抗联部队在乌斯浑河岸边宿营的信息。日军熊谷大佐立即集合了一千多日军与伪军,向柞木岗子扑去。
骤响的枪声,在晨曦中划破了静谧的天幕,惊醒了被重重包围的抗联战士。别无选择的他们,最大的希望,是渡过乌斯浑河突围。为了女战士的安全,指挥员命令师部参谋金石峰带领她们先行渡河。深谙水性的金石峰把女战士隐蔽在河边的柳条丛里,待到寻找到安全的涉水路线后,再来引领女战士们安全渡河。
金石峰刚刚游到对岸,密集的敌军就向一师部队发起了进攻。抗联指挥员一边组织火力反击,一边撤退。躲在柳条丛里的女战士们,眼看着突围的战友们惨死在敌人的机枪下,不禁焦急万分。为了给大部队创造突围的机会,冷云果断地把战士们分成3个小组,分别从隐蔽处同时开枪,将敌军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身边。突遭袭击的敌军被打得蒙头转向,于是立即调转重机枪,组成了重重的火力网,步步向女战士藏身的河边逼近。
在凶残强势的敌军面前,没有丝毫的惊慌退缩,女战士们将一颗颗仇恨的子弹,直射敌人的胸膛。在她们的掩护下,部队从柞木岗方向得以突围。而女战士们只剩下了最后的3颗手榴弹。此时,狰狞密集的敌军在前;疯狂咆哮的乌斯浑河在后……
狭路相逢勇者胜。命悬一线的生死关头,冷云没有半点犹疑,她坚定地说:“同志们!我们是抗联的战士,我们宁死不能做俘虏!”她的话声刚落,战士们就纷纷响应:“一定要过河,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冷云、安顺福和杨贵珍用力把最后3颗手榴弹甩进了敌群。弥漫的硝烟中,她们挺起胸膛,手挽着手踏进了乌斯浑河。迫击炮弹一刻不停地追逐着她们的身影,冷云的肩头中弹,王惠民的左胸受伤。激流中,胡秀芝扶住了冷云,安顺福抱起了王惠民,她们互相搀扶着,向河的深处迈进。激烈的排炮在她们的周遭不停地爆炸,渐行渐远的身影,在湍急壮阔的水面上化作了一尊石质的群体雕像,毫不犹豫的随着寒冷的江水汇入了牡丹江、松花江,去向了更广阔的海洋。河岸上,弹痕累累的白桦林与静穆飘零的红枫林,一任萧瑟的秋风哀鸣。一瞬间,乌斯浑河的流水里有了人类血液的色调。那色调如同经霜的红叶,泛着血色的光环。
东方欲晓,初昇的太阳与乌斯浑河一起,记住了花季生命陨落的时刻——1938年10月20日。这一天,年龄最大的冷云和安顺福23岁,年龄最小的王慧民只有13岁,她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残酷的战争,毁灭了豆蔻年华般美丽女性的生命。
世界最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曾经说过,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在生与死需要抉择的关键时刻,八位行为善良与高尚的女性,选择了爱国捐躯的大情大义,坚定顽强地战斗到最后一刻,树立了一个气壮山河的民族英雄群体的典范。在走入江心的时候,她们也曾经回望过大部队突围的山头,也曾经回望过河边的岸柳,这是她们对生的留恋,对死的坦然。“作为悲剧主体的她们”,却以惊人的韧性和凛然的英气,坚持抗战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不仅仅是一部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深刻意义更在于,她产生了长长久久地支撑中华民族历尽劫难而后生的巨大能量。
“为祖国而死,那是最美的命运啊!……”
带重兵袭击西征部队的日本兵熊谷大佐,也记住了中国女性的坚强。在此后不久,被周保中率领的部队包围的时候,熊谷感慨地说:中国女人是那样的英雄,死了的不怕,中国是灭亡不了的。话闭,绝望的他剖腹自杀。
三
人们常说:“女人是水做的。”因而,世界上好多著名的河流,是与优美的女性同辉共荣的。譬如,罗蕾莱女神是莱茵河浪漫的象征,白衣素裹的降水女神是塞纳河的源流,“印度的母亲”是恒河文明圣洁的摇篮。在中国,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的黄河也被称颂为母亲。八位绿鬓朱颜的战士,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壮举,使原本不起眼儿的乌斯浑河成为了不朽的圣河。
时光流过了75年,花开花落轮回了四分之三世纪,乌斯浑河的涟漪里依然闪现着她们不灭的灵魂,依旧保留着她们青春的体温,她们的死亡依然令人荡气回肠。在河水哀婉低吟的语速中,人们不停不歇地寻觅着她们与蓝天碧水永处的生命印迹。
最早的寻觅,始于八女殉难的当天晚上。突出重围的战友们回到了乌斯浑河战场,沿着河岸向下游寻找烈士们的遗体。在河边的柳树茅子里,他们首先发现了王慧民的书包,书包里还有半个赖以充饥的萝卜,其后找到的是五具被河水泡得变了形的尸体,凭着体态辨认,其中有冷云和王慧民。战友们含着泪水,将她们的尸体掩埋在河岸旁。
当年的东北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在11月4日,写下了:“乌斯浑河畔牡丹江岸将来应有烈女标芳” 的日记。从此,乌斯浑河的流水,一直在将军的心中回荡。1944年,霜染枫林的时候,在前苏联担任国际88旅旅长的周保中,组织编写了以八女投江为内容的《血泪仇》话剧,教育抗联战士要像女英雄们那样,忠诚于祖国和人民,坚定驱逐日寇的必胜信心;1946年,在纪念抗战胜利的那天,时任辽吉军区司令的周保中,率骑兵警卫排风尘仆仆地赶赴乌斯浑河八女殉难地,对天鸣抢,脱帽默哀,告慰英灵。
最早打破时空界隔,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了解八女投江英雄事迹的人,是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剧作家颜一烟。新中国成立前夕,她先后采访了周保中、冯仲云等100多位抗联指战员。殉难于乌斯浑河的女性英雄形象,在女剧作家的视觉里仿佛凤凰涅槃般升腾,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她圆满完成了电影剧本《中华女儿》的创作。影片于1950年获第5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争取自由斗争奖”,成为新中国第一部获国际大奖的影片。世界电影史家萨杜尔在观看了这部史诗般的影片之后,把八位女英雄之死比作夏伯阳的牺牲。此后,赞颂八女投江的歌剧、越剧、舞蹈及报告文学等作品源源不断地问世。
最为悲痛的是八位女战士的亲人。其中,冷云的母亲因为想念女儿哭瞎了双眼;杨贵珍的父亲在1962年才知道女儿早已经牺牲了的信息。战友们千方百计地想找到冷云与安顺福当年送给老乡的孩子,可惜的是至今也没有下落。
在乌斯浑河水目送着八女投江远去整整70周年纪念日的那一天,林口县委、县政府在八女投江遗址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岸边,耄耋老者冯文礼犹如塑像般的伫立。他前不久才从周保中将军当年的警卫员刘玉泉的口中得到信息,自己苦苦寻觅了半个多世纪的恋人郭桂琴,早已经殉国于乌斯浑河。
祭奠中,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滚滚的波涛。涛声波影里,映出的是郭桂琴17岁时那俊秀的圆脸庞,他的思绪飞回了70年前与郭桂琴分别的情景。那一天,年少羞涩的她给即将随军西征的文礼送来了手套和围巾,文礼回赠给少女的是一方手帕。小巧的礼物代表了少男少女千丝万缕的脉脉温情,闪烁的是人性的光辉。南征北战中,文礼常常将藏在身边的礼物捧在手里,忆念着恋人甜美的笑容。这份情意,随着渐长的年轮也愈发沉重了。如果郭桂琴还活着,应该是87岁了,他们的膝下一定是儿孙满堂,一定会恩恩爱爱共度天年的。
残酷的战争,弥漫的硝烟,阻隔了亲人、恋人之间的音信,给亲情与爱情带来了永远的创伤。
四
八位英雄的战友徐云卿,当年也是抗联第五军妇女团的战士,她和冷云等人分别于西征前夕。1939年,她听到了八女投江的史实之后,眼前总是闪现着八个战友手挽手向她走来的画面,乌斯浑河水也总是想和她说说话。解放后,她提起了沉重的钢笔,撰写了《英雄的姐妹》一书。周保中将军亲笔为她的作品撰写了序文,高度赞扬了东北妇女参加抗日游击战争的英雄事迹。《英雄的姐妹》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不仅再版重印,还参加了国际文化交流图书展。
徐云卿的女儿白福兰是听着八女投江的故事长大的。她把母亲的作品赠给了我,并向我深情地回忆起母亲在撰写八位战友时的伤痛——
残酷的战争可以使孩子早熟,可以逼迫孩子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
13岁——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权威的专家曾经这样说过。王惠民那时候恰恰是一个13岁的活泼天真的小孩子。每天夜里,王惠民都要枕着母亲的胳膊入睡。可平时行军打仗,她却总像一个小大人似的:她常去炊事班帮着做饭,去伤病院送信。她常说的一句话是:“爸爸被鬼子打死了,妈妈和弟弟妹妹在家受罪。我是大女儿,我得快点儿把鬼子打走,好回家找他们。”
爱是力的基础。“八女”之一的杨贵珍是母亲最熟悉的战友。母亲第一次在林口县刁翎镇见到杨贵珍的时候,发现她的头上插了一朵带孝的白花。原来,杨贵珍是个童养媳,结婚不到一年就死了丈夫。公婆恨她克死了儿子,总是打骂她,她觉得苦难没有尽头,甚至想到了死。在母亲的启发下,杨贵珍剪掉了疙瘩髻,穿上了抗联的军装。入伍后很快就锻炼成了勇敢、坚强的战士,并且与连长宁满昌结为夫妻。她深深地爱上了抗联部队,她说是抗联给了她新的生命。
离别的那一天,杨贵珍与母亲难舍难分。她把爱人宁满昌送给她的红色毛线衣留给了母亲作纪念。离别时,杨贵珍紧紧地握着母亲的手说:“再见时,我一定无愧地伸出自己的手。”离别之后,母亲一直用这句话鞭策自己,努力工作。母亲说,是残酷的战争,割断了她与战友之间那浓浓的真情。
五
日本的侵华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民族危亡的苦难改变了女性的命运。侵略者的烧杀抢掠,使杨贵珍、郭桂琴、胡秀芝、李凤善等重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成了辛酸的童养媳、苦命的小寡妇和凄苦无依的孤儿。在战争中,八位女英雄每个人都有刻骨铭心的伤痛——
冷云、安顺福的丈夫都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安顺福的父亲与兄弟在日军的大搜捕中遇害;黄桂清的家是抗联的堡垒户,房子在并屯中被烧毁,一家人下落不明;杨贵珍的丈夫、郭桂琴的恋人随部队西征安危无常;王慧民的父亲牺牲了,母亲与弟弟妹妹生死未卜……巨大的哀痛使她们不约而同地告别亲人,勇敢的直面血火焦灼的杀戮,承担起了为民族生存而抗争的职责,在惨烈的战争中获得了新生。假如没有日本侵华战争,杨贵珍、郭桂琴、胡秀芝、黄桂清们很可能会重复无数乡村女性的命运,守着亲人度过辛劳而安宁的一生;王慧民在挎着书包蹦蹦跳跳的上学之后,会伏在父母亲的膝上撒娇。但是,战争打破了宁静。她们既是野蛮的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也是反侵略战争最英勇、最坚决的奋斗者。在家破人亡的极度痛楚中生发出的报仇雪恨的朴素思想,逐渐形成了保家卫国的共同理想。
冷云是典型的知识女性。从她遗留下来的裘皮袄与照片等物品中可以看出,假如没有侵略战争,她会浪漫地过着知性女子的理想生活。当教师的她,身着旗袍,手把遮阳伞,周身散发着唐诗宋词的韵味,展现的是温柔婉约、安之若素的岁月;着戎装的她,端庄秀丽的面容上蕴涵的是对和平的向往,从容凝重的眼睛、紧闭的嘴角与倔强精干的短发,分别传达出了中国女性勇于承担历史使命、不屈不挠不畏强暴的战斗意志,以及对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念。两张照片之间的时空,是女性在反侵略战争中由妩媚静好逐渐向勇敢坚定转换的真实写照。
在参加抗联之前,冷云曾经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为了党组织的安全,她不得不与伪警察结婚;为了参加抗联,她不得不顶着“私奔”的恶名离开家。她对告别的校友说:“我们这一生都交给了党,在哪里工作都是为了挽救我们的祖国。”她在赠给校友的留言中写道:“两山不能迁,两人能相见,盼那天盼相逢,祖国换新颜。” 她把所有美好的向往,都化作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力量。
在抗日战争中,冷云等抗联女战士所承担的角色最为复杂。身为战士的同时,她们还是思念父母双亲的女儿,也是思念儿女的母亲,还是牵挂丈夫的妻子。多重的角色,使她们更加珍惜生命。然而,侵略战争逼迫她们失去了浪漫单纯,失去了母亲、妻子、女儿的多重身份,放弃了珍爱生命、厌恶杀戮的本性。在短兵相接的战场上,她们甚至消失了女性柔弱的性别特征,不得不挑战女性的生理特点,承受其中的苦恼与麻烦:她们用破布,用捶软的树皮里层纤维代替月经垫,长途行军磨破了阴部和大腿,有时候甚至引起流血化脓。她们还要承担起创造生命的天职,冷云与安顺福等抗联女战士,都是在深山老林、甚至是马背上、战场上度过分娩的“鬼门关”。只有在战斗的间隙,她们才能够以阳刚之美的品质,展现出阴柔之美的情怀。采野菜、扒树皮、煮蘑菇、补衣服,是她们的强项。歌声是抗联队伍中最有诗意的享受。徐云卿多少年以后还记得王慧民最喜欢唱的那首歌,“日出东方分外红,曙光照满城,大家快觉醒,看看鬼子多奸凶,国家人民全叫它坑。”歌声给艰难困苦的抗联增添了乐观喜庆的气氛。
她们的坚强,让我感悟到了伏契克的经典语录:“每一个忠实于未来,为了美好的未来而牺牲的人都是一座石质的雕像。”“而每一个妄想阻挡革命洪流的腐朽过时的人,即使他现在带着金色的肩章,他也只能是一个朽木雕成的木偶。但也需要看看这些活木偶是多么卑鄙可怜,看看他们是多么残暴和可笑”。她们的英勇,让我看到了石质雕像与朽木木偶的强烈反差,伟大与渺小之间的强烈反差。
那是怯懦、自私的一群。他们在生命还没有死亡之前就被铁定在了耻辱柱上。其中,有抗联第二路军西征的主要领导人,吉东省委书记、抗联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1938年7月31日夜,在西征部队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对抗战前途绝望的宋一夫,以巡查岗哨为由,携款带枪,偷偷叛逃。8月26日宋一夫到伪哈尔滨警察厅投案自首,在他的引领下,巴彦、木兰、东兴的数百名中共党员及爱国群众惨遭杀害。1939年2月1日,中共吉东省委执行部发出通告,永远开除宋一夫的党籍。1946年宋一夫被哈尔滨人民政府逮捕处决。
还有一个朽木木偶是抗联第二路军西征的另一个领导人,抗联一师师长关书范。在八名女战士用生命掩护了他和部队的转移之后,被吓破了胆的关书范,经常在部队中散布悲观失望情绪和假投降理论,他借口外出侦察,背着第五军领导,秘密与敌军达成投降协定。1939年1月,第二路军司令员周保中得知关书范准备投敌变节的信息后,立即召开吉东省委干部会议,将关书范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判处死刑。1月15日,关书范随敌伪工作班来到刁翎时被逮捕, 16日凌晨被枪决。
直接向日军告密,造成八女投江悲剧的朽木木偶是葛海禄。葛海禄原是抗联八军军长谢文东(1939年叛变)的副官,因为贪生怕死叛变投敌,当了日伪特务。那天晚上,他在“侦察守望哨”发现柞木岗子附近的篝火之后,立即向日本守备队告密。1955年,被公审枪决。
历史公正而无情,越是贪生怕死的懦夫越是短寿;而八位把个体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的女性,却虽死犹生。正如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所说的:“死亡征服不了伟大的灵魂”。
清波有语。乌斯浑河呜咽的流水,朝朝暮暮地诉说着——八位女英雄的精神足以吸引今生来世的人们,永生坚定对于崇高使命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