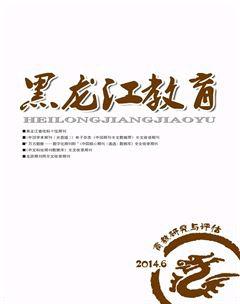论教育学专业价值危机的表征及其超越
摘要:教育学专业面临着一定的价值认同危机,其价值危机与“教育学无用论”共谋,表现为“他者”和“学习者”视域下的教育学专业价值危机,以及自身发展不完善所致的价值危机;其价值危机的出现与育人的“单向度”——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和教育意义的失落相关。其价值危机的超越,在于发挥教育哲学的启蒙功能;实现对教育学学科专业原有认知的超越和倡导一种“主体间的指导学习”;培育学习者学习教育学的自觉意识。
关键词:教育学;价值危机;无用论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107(2014)06-0056-03
1632年,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问世。“在教育学史上,一般把夸美纽斯的这本书看成是近代第一本教育学著作。”[1]之后,赫尔巴特对教育学的发展和创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在世界教育学史上被认为是‘现代教育学之父或‘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他的《普通教育学》(1806年)被公认为是第一本现代教育学著作。”[2]不管是从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还是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问世为起点,教育学的独立发展史也至少在二百年以上。但其存在价值一直备受质疑。这一直困扰着教育学的研究者和学习者。专业的学习者也都存在着“教育学无用论”的看法,并对教育学本身充满了不肖、嘲讽等,没有所学专业的归属意识和荣誉感。因此,教育学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对教育学学科进行积极的价值辩护也是必要的。
一、教育学价值危机的表征
“教育学无用论”背后的教育学专业价值危机,是教育学学习者对其专业价值不能满足其自身价值需求和步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认知凸显。综合审视,发现“教育学无用论”背后的教育学价值危机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的表征。
(一)“他者”视域下的教育学专业价值危机
这里的“他者”主要指高校的非教育学专业的学习者和以家长为代表的社会成人。 首先,在“他者”的视域中,教育学是一门非常陌生和冷门的专业,也是很无用的专业,与经管类和工科类等时髦专业相比,教育学专业面临着未能被“他者”承认的尴尬境地。在大学里,也被别的院系学习者所歧视,正如文学大师钱钟书所言:“在大学里,理科生学生瞧不起文科生,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系学生,教育系学生没有谁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3]其次,对于家庭来说,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学习一个时髦和好就业的专业,找一个好的工作,以此来改变家庭经济现状和社会地位。这种价值欲求体现了家长对专业的功利需求。显然教育学的现实困境不能满足这种价值需要。教育学专业也就在家长的视域里失去了宠信的地位。再次,在社会世俗价值和功利欲求的影响下,人们都认为毕业后能获得巨大经济利益回报的专业是好专业,反之则不是好专业。因此,教育学专业也就被整个社会遗弃。
(二)“学习者”视域下的教育学专业价值危机
这里的“学习者”主要指高校教育学专业的学习者(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在 “教育学无用论”的群体中,教育学专业学习者认为,学习教育学专业的结果是工作不好找和面临着专业不对口或得不到专业承认的尴尬境遇。而且其专业的学习并不能给他们带来预想的经济回报。面对这种期望与现实的反差,让教育学专业的学习者们对教育学的学科价值产生了质疑。这是教育学学科专业价值危机最为典型的表征方式。另外,学习者群体中,本科生大部分是被调剂到本专业的,考取教育学的研究生,也大部分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而进入到教育学的学习中的。对于本科阶段的调剂者,他们是“被选择者”,因此存在着被选择学习教育学的不满情绪和反抗意志。教育学专业的学习,并不能满足自己的价值追求和兴趣。对于以研究教育学为专业的研究者生而言,在学习生涯开始之时,才发现教育学的现状并不是当初考研时的理想状态,也不符合自己的期望,考研选择时的激情和理想,在研究生学习的现实生涯中,陷入了自我失落的困境。因此,“教育学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就是在瞧不起教育学和教育学的先生们,以及瞧不起自己的过程中度过了烦恼且卑微的学习生涯和研究生生涯”[4]。教育学学科在自己的“学习者”面前,遭遇了得不到自身认同的价值危机。
(三)教育学专业自身的价值危机
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一门高深学问和高校学科群的一员,在高校里并没有显赫的地位。它不像哲学、社会学、文学等那样发展成熟,而且教育学学科的发展史中,对其他学科(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的依赖极大,这可以从“复数的教育科学”的状况一目了然。这种对其他学科的依赖,本身就展现了自身的先天发展不足,从而很容易导致“他者”和“学习者”视域下的价值危机。另外,教育学学科发展自身面临着来自现实的困境和悲哀,“悲哀一,教育学在各种有代表性的学科分类中要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要么隐藏在某一角落之中”[5]。“悲哀之二,在整个社会科学界,教育学遭到其他学科普遍的漠视”[6]。“悲哀之三,伟大的教育学家往往不是教育学专业出身”[7]。“悲哀之四,是一线教师的教育实践工作与教育学理论常态化的分离”[8]。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曾就教育学是否终结,展开了一次小争论,“教育学终结论者认为,由于‘教育学是从‘教仆这个词派生出来的,而它又作为关注教育过程的应用艺术,很少受到尊重,所以从词源上看,‘教育学没有深奥的‘科学含义”[9]。这种来自教育学自身的价值危机,源自学科本身的不成熟和不完善,说明我们的教育学学科缺乏一种自我理论自信。这种理论的不成熟、不完善和不自信,也就很容易影响教育学专业的学习者和家长以及社会对其价值的认知态度。
二、教育学专业价值危机的归因
教育学有用,这是学界的共识,也是无数教育学家和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当代哲学、美学大家李泽厚曾说:“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生长和发展、形成和塑造的科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学科。”[10]即使如此,仍旧难当教育学无用论的来袭。而且持“教育学无用论”观点的主体是我们高校教育学学科专业的学习者,这就更需要进行反思,为走出“教育学无用论”的价值困境而寻找路径。
(一)“单向度的人”:教育育人功能的单一价值取向
“马尔库斯关于单向度的人(单面人)的理论,表述了深刻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11]。现代学校教育生活过程中,技术理性大行其道,充斥着学校教育生活的方方面面。具体的充满生命活力的学习者被奴役和消解在了以考试选拔、竞争为取向的学校生活中,进而“人由此被消解在了给定的秩序中,丧失了批判和超越的维度,成为与现状认同的单面人或单向度的人”[12]。这折射出现实的教育育人功能的单一化。单面的人(单向度的人)缺乏丰富的生活情趣和多元化的兴趣爱好,更缺乏自由选择和担当的独立意识与能力。因此,当这样的学习者进入大学之时,不能按照基于个体的价值判断、爱好、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作为自己学习与研究的领域。认为能获得好的利益的学科专业才是适合自己的价值追求,当遭遇到教育学专业的就业困境与其单向度功利价值诉求相矛盾时,个体易陷入自我迷失和失落的困境中,也很容易产生错误的价值判断和不良的情绪体验,进而迁移于自己的专业学习中,认为这门学科缺乏应有的价值,难以获得预期的利益诉求。这是教育学价值危机出现的原因之一。
endprint
(二)工具理性:专业选择的工具价值取向
工具理性是由西方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的,是与价值理性相对应而言的,一般“意指反映在计算、测量、组织、预测等技术行为中的认识能力,其目的在于追求行动的‘效率和功利的‘最大化”[13]。“不是将‘人性解放而是将‘技术控制作为自己的目的”[14]。审视当下的学校教育生活,处处充斥着这种以工具理性为旨归的教育,高考完了选择专业,具有工具价值的专业备受社会、家长和学子的青睐。反之,那些不具有工具价值和不能带来利益最大化的专业成为冷门专业。教育学的专业显然不具有较强的工具和实用价值,尤其不能给家长和学习者带来巨大的功利利益,也不能满足其近景期望。另外,“教育对国家的意义,似乎主要是在增强国民经济水平方面,教育对企业的意义,似乎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教育对个人的意义,似乎主要是增加经济收入”[15]。国家、社会企业、个人在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实现了一定的藕连。都以工具理性为价值取向,这对教育学的学习者也无疑具有潜在的影响,进而进一步加剧教育学专业的价值危机。
(三)教育意义:教育主体教育意义的失落
“教育的意义问题就是要探讨教育如何成为‘教育的,即某种被称为教育活动的社会活动如何真正地呈现出‘教育意义”[16]。这种呈现出来的教育意义是以“德智体美劳”的健全发展和人性的完善、卓越为目的,即是说“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但是现实教育却是“人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这种以育人为目的教育意义被现实教育目的逐渐地消解,以至于有“老师在自己的课堂上告诉学生或试图使学生明白,‘念书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上大学、挣大钱、娶美女”[17]。学习者认为,现实的教育就是这样,社会的价值取向也是功利的,教育学的理论学习对现实的教育实践是无意义的。因此,也就形成了一种教育学理论之于教育实践无用的悲观论,持这种教育学理论悲观论者,很容易将这种悲观的情绪衍生到教育学的学习上。而且,教育学的学习者也经历了这种不具有教育意义的教育生长过程,也强化了他们对教育悲观论的持有。
三、教育学价值危机的超越
“教育学无用论”的价值认识,基于我们前文的分析,具有多重的表征和成因,需要进行反思。基于教育哲学的视角,笔者认为超越的路径如下。
(一)教育哲学:实现对学习者的启蒙
哲学是爱智慧的学问且以反思世界、人类自身和社会为己任。而“教育哲学可以以任何一个具体真实的教育问题为基点,用自身所具有的反思性、批判性和规范性来将教育观念中的内在与本真唤醒,展现教育哲学所具有的启蒙意识”[18]。同时,基于教育哲学的反思性、批判性和启蒙精神,对教育无用论的知识基础和价值观念进行分析诊断,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对其产生这种教育学无用论价值观念的思想基础进行批判和评价。实现教育哲学对教育学价值的积极辩护和对教育学学习者的启蒙。从而超越教育学无用论的价值观念,致力于用一种新的视角来超越原有的认识偏误,重新认知和建构教育学的学科价值。最终,让学习者自觉地超越自我认知困境和进入教育学意义的探索世界中。
(二)自我反思:实现对教育学认知的超越
“人对世界首先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文化,认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19]。之于教育学的学习,就是要求其学习者,先从自我的认识和反思开始,深刻地剖析和认识自我,认识和反思自我的受教育和学习过程,逐步认识和完成自我从原有的先验思维观念和认识转向永恒可靠的“理念”认识。学会反思我们日常教育及其教育生活的不足,走出现实教育的“意见”世界,学会“跳出教育看教育”,从而为教育学的学习和利用教育学的理论思维审视现实教育的不足奠定基础,进而增强对教育学学科价值的自我认同,感受其教育学的价值和魅力。另外,教育学的学习者通过教育学的逐步学习,要摆脱绝对论的观念,认为教育学的学习必须要以改变不合理的教育现实为绝对追求,这种观念实际上忽略了教育学理论自身的建构和完善。任何一门学问并不仅仅都是以变革现实实践为唯一的价值追求,它也有完善和建构自我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追求。合理地看待教育学存在的价值,从而增强教育学学习的价值归属感和自信,避免陷入无用论的泥潭。
(三)主体间性的指导学习:开启学习者的学习自觉意识
“主体间性是主体之间在语言和行为上相互平等、互相理解和融合、双向互动、主动对话的交往特点和关系,是不同主体间的共识,是不同主体通过共识表现的一致性”[20]。关于“指导”,教育家杜威在其《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里有很精辟的论述,认为“指导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词,表明把被引导的人的主动趋势引导到某一连续的道路,而不是无目的地分散注意力。指导表达了一种基本的功能,这一功能的一个极端变为方向性的帮助,另一个极端变为调节或支配。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慎防有时加进‘控制意义”[21]。另外,我国学者认为:“指导学习就是教育或在教育者指向和引导下的学习。”[22]因此,“主体间性的指导学习”对教育学的教学和学习启示极大。要求教育主体和学习主体要打破原有的“教和学”的二元对立的交往模式。实现“教与学”的统一,构建“相互平等、互相理解和融合、双向互动、主动对话的交往特点和关系”的教育模式。这种主体间性的教育模式是有指导的学习,当然这种指导是有意义的,不是朝着“控制”的指向一方延伸,而是朝着具有帮助性的一方延伸,终极旨归是让学习者能体会学习的意义,自主进入学习的意义世界,实现自主自觉的学习,即指导学习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不教”。最终,让教育学的学习者在教育学的世界中建构自己的教育意义世界。
参考文献:
[1][2]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教育学基础[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17.
[3]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78-79.
[4][5][6][7][8]李政涛.教育科学的世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7,28,29,29,30.
[9]郑金洲.中国教育学60年:1949—2009[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77.
[10]李泽厚.世纪新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17.
[11][12]衣俊卿.现代性焦虑与文化批判[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167.
[13][14][16][17]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02,202,258,259.
[15]毕淑芝,王高义.当今世界教育思潮[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173.
[18]张旸.学校教育价值的危机的凸显及超越——基于对“读书无用论的反思”[J].中国教育学刊,2013,(3).
[19][20][22]郝文武.教育哲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14,41,40.
[21][美]杜威;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30.
收稿日期:2013-11-20
作者简介:张小刚(1987—),男,宁夏西吉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哲学研究。
endprint
——评《批判教育学的当代困境与可能》
——《教育学原理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