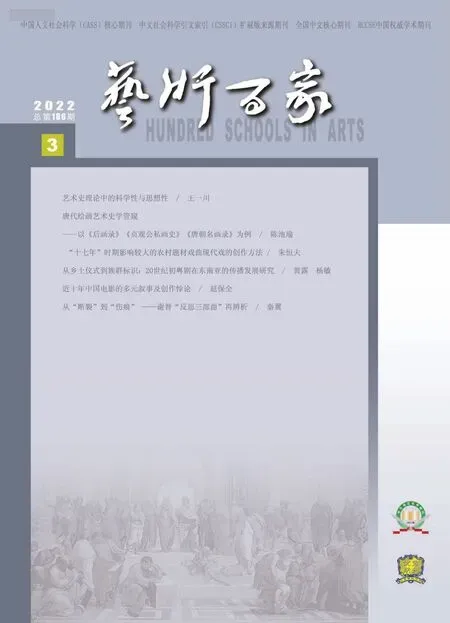世阿弥能乐的艺术表现形式及其美学思想*
谢 明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一、能乐的集大成者——世阿弥
“能”又称为“能乐”,是日本古典戏剧的代表。“能”在明治维新前被称为“猿乐”,而“猿乐”来源于中国唐代盛行的“散乐”,是日本古典艺能与从中国传来的艺能相融合的产物,主要包括平安、镰仓时期流行的杂艺,镰仓初期的滑稽剧等娱乐性演技。日本南北朝时代以后,猿乐的表演趋向于带有情节性和戏剧性,逐渐演变成“能”。
世阿弥(1363-1443)出身于能乐观世流宗家,是观世流始祖观阿弥的嫡子。观阿弥之后,由他独立领导观世一座,承蒙室町幕府将军爱顾活跃于京城能乐舞台,名极一时。世阿弥的艺术创作活动不止限于舞台表演,他对能乐的杰出贡献在于其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并提出了较为系统、完备的能乐理论。目前能够考证的世阿弥作品(包括新作和改作)已达五十多部,能乐理论著作二十一部,他的剧作和能乐论在同时代的演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世阿弥本人也成为能乐历史发展进路上一位“集大成者”的能乐家。世阿弥对能乐的兴盛和内在品质的提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由于他的努力,传统演剧能乐的基础得以巩固,室町初期能作为演剧才有了急速的进步,直至今日仍使观世一座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二、世阿弥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歌舞能”与“梦幻能”
世阿弥视剧本的创作为能乐者关乎性命存亡之事,在《花传第六花修》中曾言:“书能本一事,乃此道之命也。”他上演的多数作品都是独创或对古曲的改编。之前有研究认定多半经典作品都是世阿弥所作,虽有牵强,但不能否认世阿弥确实是一位卓越的能作家。
在世阿弥自笔书中已言明是独创,或据文献资料和作品考证确定为世阿弥作品的有《高砂》、《弓八幡》、《老松》、《井筒》、《砧》、《当麻》等三十九部;据古作改编的作品有《葵上》、《通小町》、《通盛》等十三部;另创作有十几首曲舞等独立的曲子。这些作品大部分还保留着世阿弥时代的风貌在舞台上演。在其部分作品中仍可见父亲观阿弥时代能乐的风貌,但更多的作品却展现出世阿弥的独特艺术表现,其中最主要的创新即对“歌舞能”的引入和“梦幻能”的确立。
世阿弥对“歌舞能”的引入得益于近江猿乐比叡座的犬王。继观阿弥之后能够与世阿弥比肩的只有犬王,世阿弥对犬王的评价也极高,认为他歌舞优美,尤擅长天女舞,和其他模拟物态的能不同,犬王更注重幽玄美的表现。犬王的艺术风格对世阿弥有很大影响。观阿弥坚持的大和猿乐传统的以拟物为主体的趣味性能向以歌舞为主体优美型能的转变可以说是世阿弥在借鉴了犬王能乐风格之上的二次艺术创新,形成了能乐的歌舞剧化。
在能乐歌舞剧化之前,一般认为,五十岁再演鬼能等消耗体力的剧目就很勉强。而在歌舞剧化之后,能乐从拟物为中心转变到歌舞为中心,大动作的表象艺术转变为小动作的追求玄幽境界的艺术。这样,过了五十就不能登台表演的“鬼能”等动作幅度大的剧目和不戴面具的“直面能”的数量在减少,老年演员出演也变得可能,甚至说年龄越大反而越适合演。能乐歌舞剧化实际上拓展了演员出演的范畴,延展了演员的艺术生命。而从能乐发展史上看,演员高龄现象实质上揭示了能从以“拟物”(「物まね」)为主体到以歌舞为主体的一个转变过程。世阿弥对能的改革后,脱离了对肉体美感的依赖,转入对玄幽的内在美的追求。他的改革标志着能的发展从初期的表象美转到了更内敛的意识美。
将传统的梦幻能最终确立为以歌舞为中心追求幽玄的表现风格则是世阿弥在艺术形式上的又一创新。与现代能剧相对,梦幻能描写的是旅人或僧人在梦境中与故人的灵魂或鬼神精灵相遇、听闻奇谈旧事、重现昔日场景的故事。其艺术原形和内容多取材于《伊势物语》、《平家物语》等古典文学,再配上与人物相符的歌舞,按照序、破、急的段落构成创作出新的能乐形式——梦幻能。梦幻能作品结构类似但内容各不相同,情节多样。加之古和歌与古文的巧用,和歌式的修辞和连歌的展开,使之文辞瑰丽、抒情和叙事结合得天衣无缝,构成了优美的诗剧。
概言之,世阿弥的梦幻能通过视听的两相关照,展现了丰富“余情”的美的世界,由此其艺术生命力不仅延续至今,且影响广泛——后代能作家频频效仿,不断创造出同一系列的作品,能乐的“世阿弥风”遂蔚为大观。
三、世阿弥能乐理论——“花”与禅意
根本上,世阿弥能乐富有生命力和艺术张力的艺术表现形式得益于其精深、完备的能乐论的支撑,他的能乐论对后世能乐的发展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目前学界所探明的世阿弥的二十一部能乐论著作中,“花”成为中心课题,也是贯能乐论的一条主线。如在世阿弥首部能乐理论著作《风姿花传》中,围绕着习艺的不同年龄阶段,世阿弥始终都在探讨艺人在学艺中“得花”、“失花”、“再得花”的循环往复的习艺之道。再如《花镜》和《三道》则强调“花开”之效果应达到玄幽之美,而《却来华》中凸显的世阿弥晚年时期的艺术风格“却来之境”也是旨在阐释让“花开”的高级手法。
那么世阿弥提出的“花”的含义究竟何指呢?在《花传》的部分章节中,世阿弥集中论述了“花”在能乐艺术理论上的意涵:所谓“花”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指能的魅力,能乐人给观众带来的感动,和《花传》中所说“珍贵之处”、“有趣之处”有相似的意思。应该说,世阿弥所有能乐论都指向“花”,但在其长达三十余年的著书过程中,不同的时期又有不同的理论内涵和艺术指向。这种变化不仅是能乐审美情趣变化在艺术理论上的反映,与世阿弥作为能乐者个体境遇变化亦有重大关联。
世阿弥所处的时代正是足利义满将军统治的时代。足利幕府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力倡导“花”这种普遍的美意识来统合民众、维护政治稳定。而世阿弥倡导的“花论”正是义满时代的产物,迎合当时主流的审美情趣也是现实需要。但是,应该说世阿弥的“花论”更多的还是源于自身艺术创作过程中的深切体认,有自体对“花”的独特理解和感悟。
世阿弥“花论”的成型,不仅再一次印证了马列主义关于政治与艺术同属上层建筑且互为作用之论断的真理性,也表明艺术史上的特定时期的特定流派和艺术风格通常都浸淫着那个时代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是那个时代风物人情在艺术上的深刻体现。
另外世阿弥对禅语的借用也是其能乐论的显著特点之一。如《风姿花传》中就使用了禅语“情识”一词:“据本人习艺经验,概括戒律如下:一、好色、博弈、嗜酒,此为三重戒。自古之训。二、稽古坚持不懈,戒骄戒躁。”
其中“稽古坚持不懈,戒骄戒躁”一句反复出现在世阿弥的能乐论中,足见其重视程度,这句也被誉为世阿弥稽古论的“金言”,他把此条和古人三大戒“好色、博弈、大酒”同视为能乐者必须遵循的戒律,表明了其严谨自律的习艺态度。世阿弥所用的禅语“情识”实际是“我慢情识”的省略用语,禅也把“我慢情识”视为修行戒律,孽障。由此可见世阿弥的艺能修行和禅修行有相通之处,都有明确的清规戒律,通过稽古、修炼达到至高的境界。
同样的,在《风姿花传》中,世阿弥还使用了“公案”一词:“专心思考,如对自己艺术水平有准确定位,此时艺术之‘花’,永不会谢。如过高估量,已开之‘花’也会凋谢。此真理应记于心中。”
“公案”出自禅语,是禅宗师探索佛理给弟子留的课题。和禅宗“公案”的形而上相比,世阿弥的“公案”是形象而具体的,引申为对此下工夫、思索之意,在《花传》中被活用为动词。“公案”所要思索的具体内容当为下文的:“如对自己艺术水平有准确定位,此时艺术之‘花’,永不会谢。如过高估量,已开之‘花’也会凋谢。”世阿弥在此直接点破戒律,省略了“悟”的步骤,实际上把“悟”的过程放入习道稽古中去,通过登台表演日积月累的经验才能悟道。
四、结语
作为能乐集大成者的世阿弥在重视时代审美情趣与关照个体审美体认的基础上提出了“花”这一深刻而富于创见的能乐论旨,不仅完备了能乐论,也在艺术形式上开创了富有生命力和艺术张力的“歌舞能”和“梦幻能”。而他别出心裁地将禅林用语导入能乐论中确立了稽古戒律,将能乐稽古由传统的流于艺人专习的技艺提升到了艺术性与艺人的道德性相互兼顾,甚至“德”超于“技”的高度,使能乐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为后世能乐的有序传承和延续提供了内在的保证。而将禅语“公案”一词由名词活化为动词,将其意涵流布于稽古修习的全过程,在提高艺能之人习得和悟道的水平同时,也疏浚了能乐与禅的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