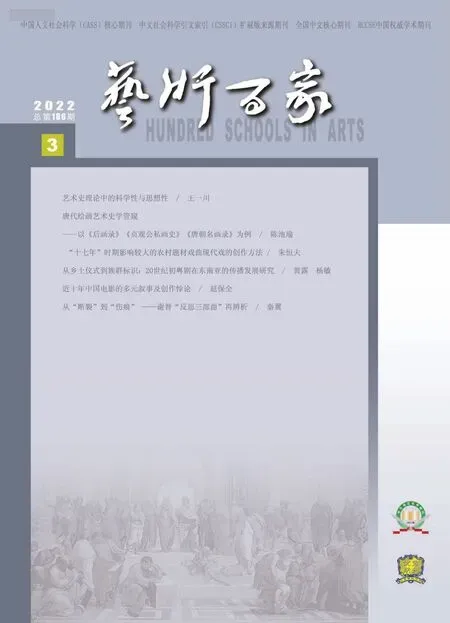丢失地方的地方戏*——当下地方戏生存忧思
王长安
(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安徽合肥230001)
就戏曲生存而言,所有产生于中国的本土戏曲都是地方戏。宋金院本是“大都”地方戏;南戏是“临安”地方戏。元杂剧所分“南北曲”,实质上就是南方中国和北方中国的地方戏。人们习惯地用“昆山”、“海盐”、“余姚”、“弋阳”四大声腔来概括明代戏曲,除了表明某些剧种的声腔所宗外,也切割出了各剧种鲜明的地域特征。这种方式还直接引出了对清代地方戏的地域性分切,即所谓“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戏曲通常会因多元积聚,产生出吸纳较多地域元素从而覆盖范围更广的超级剧种,即所谓“大剧种”。如明代的昆曲和清代的京剧。京剧虽号称“国剧”,其本质依然是“北京”的地方戏。这从其一度名之为“平剧”①即可略见一斑。
颇富意味的是,由这种积聚而产生的“超级”地方戏或大剧种并不能始终保有对曾经所代表地域的情感亲密,不能风光永驻,一劳永逸。由于封建帝国的集权性质,所有这些超级剧种一旦形成就蛰伏或依附于权力中心,为权力所用,依权力而在,借权力而扩张。逐渐失去了对其所由产生和弥散扩张地域的代表性,渐次变得苍白而空洞。由此,多域的帝国、多样的地方、多彩的民风、多元的生活和多族类的民众便又不得不重新创造各自新的地方戏。史学家曾给了它们一个十分恰切而形象的名字——“花部”。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地方戏其实一直是在“由地方走向非地方”;“由建立地方性到丢失地方性”;“由整合——解除多样,复由多样——颠覆整合”这样的循环轮转中生存并发展着的。这其中,地方是它的母体,需要是它的前提,差异是它的本质。
一、忧思之一:需求弱化,个性丢失,中心地位不复存在
到1949年,中国成熟戏剧已经走过了近千年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前的约200年间,可以说是地方戏风起云涌的时代。那时,由于交通、通讯及语言甚至趣味的限制,“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言”,中国大地几乎所有的民众聚集区都有自己的“地方戏”。人们在相对固定封闭的狭小区域里依据自己的喜好和可能,用戏剧的方式娱乐着自己。正所谓“乡里狮子乡里舞”,“自己唱曲自己听”。尽管旧制度对戏曲打压,战乱又使之雪上加霜,但到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地方戏曲剧种依然多达360多个(有的版本统计为374个)。这既说明民众空前的创造力,也说明民众对戏曲的需要。然而随着新中国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如今公路、民航、高铁已密如蛛网,四通八达,真正是“千里江陵一日还”;电话、手机、互联网无处不在,几乎人人都有了“千里眼”、“顺风耳”,所有地域的信息均可实时传递,无缝对接;广播电视和网络可以把任何演出直接展现在每一个人的面前。由于教育的普及和普通话的推广,人们可以无障碍地欣赏非本域娱乐形式。于是,本地“狮子”便不再是戏剧审美生活中的唯一。需求度减弱,中心地位便不复存在。随着视野的打开,本域“狮子”也在一夜之间难入法眼了。如此,地方戏在生它养它、赖以发生发展的“自家领地”中也一朝失宠,饱受冷遇,其生存情状自然也就岌岌可危。
新中国成立时,由于京剧“一统天下”的地位已经形成,在人们的意识里普遍认为京剧是“大剧种”,是“国粹”,是中国戏曲集大成者。各地方戏剧种对其顶礼膜拜,纷纷效而法之,以期克服自身的“小”而“土”。尤其是到了“移植样板戏”的年代,更是连声腔、板式也要做得与京剧一般无二。那些本以“两小戏”、“三小戏”为主的地方戏剧种,本不讲究什么“四功五法”,却硬要“翻墙”、“开打”。结果不是请京剧或杂技演员帮忙,就是自己刻苦训练,“创造条件也要上”,致使剧种形象模糊,面貌扭曲,个性荡然无存。再加上一度盲目学习西方表演体系,如“心理体验”、“最高任务”等等。表演话剧化、舞台实景化,使地方戏特有原生形态的鲜活本色被消解。心事沉重,自我迷失,疏离根本,生命力退化。面对衣食父母、乡亲故旧、玩伴发小,也只能是“相逢不相识”了。丢失了个性就丢失了存在的理由。至21世纪初,我国的地方戏剧种迅速锐减30%,仅剩260余种。这种个性的消泯,还使它丧失了走出本域,在更广大空间存在的理由。据相关资料显示,全国200多个剧种中,能经常参与全国性演出活动的仅40个。有74个剧种仅有一个职业院团,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团”。②
二、忧思之二:时过境迁,载体丧失,生存空间日益萎缩
我们知道,地域是地方戏之源,是地方戏赖以存在的载体。地域人是其活态保存的前提。戏剧属于非物质文化形态,有人演有人看就存在;没人演没人看就不存在,无法以物质形式存有或流通。当今地方戏所遭遇的最大危机莫过于载体的丧失。
早在20世纪末,媒体就宣称“上海将成为我国第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由此带动了中国的城镇化热潮。据统计,至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就超过了50%,达到52.57%③。这就意味着中国半数以上的地方不再是农村,半数以上的人口不再是农民。另据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004年到2011年,平均每年减少7700多个村委会”,每天有约80-100个自然村消失④。过去十年,中国共消失90万个自然村。原来占据国土面积3/4以上的中国村落在减少、在萎缩、在消失。地方戏原本是依托村落而发生的,是村落的劳动生活和村民的心理需要引发了地方戏的出现。当地的土腔土语土俗就是它形成的最初胚芽。依靠村落间的交流和联系,通常是“赶集”或“庙会”,地方戏得以传播和发展。而今高速度的城镇化进程,使得一个个或一片片村落蓦然间消失,这等于拆了地方戏的巢穴,毁了地方戏的根基。使其如鸟儿没了树林,庄稼没了土壤,一下子身如飘蓬,无处立足。正所谓“一朝漂泊难寻觅”,“白鹭飞来无处停”。
在村落快速消失的同时,农民也在骤然减少。据统计,我国现今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之比已接近1.1:1。截至2012年,我国农民工总数已达26261万人,其中举家外出的农民工3375万人⑤,高校招生数已突破800万。这就意味着农村在人口意义上已经变得荒凉。本域消解,地方虚化,地方戏所赖以发达的人口基础也在流失。更何况,走出去的都是青壮年,是乡村人口中最活跃、最有质量的部分。留下的大都是老人和娃娃,他们的审美需求不是已经退化就是还未形成,很难实现对本域剧种的承载与托举。当然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戏消费实体和地方戏存活的宿体。
另一个问题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了高增长,创造了物质的极大丰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毋庸讳言,这种高速度,基本还是靠资源的高消耗和劳动密集以及增加劳动时间所获得的。广大劳动者为了经济目的,不得不“辗转各地”,“加班加点”,“多拉快跑”。这从每年春运的滚滚人潮和物流业频频出现的疲劳驾驶以及连连发生的富士康跳楼事件或可略见一斑。人口的大迁移,为生存而出没各地,使得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再是本域人口的独有领地,任何一个“当地”也都不再具有人口和文化学的固有含义。由此,地方戏的受众群体被肢解,任何一地都不再是它的“流行区域”;任何一个群体也都不再是它的“基本观众”。在一地较长时间的“驻演”由此而成为非分之想。
再者,人们的“多拉快跑”,还带来对闲暇时间的挤占,对心理空间的挤压。多数人几乎不再有娱乐时间,学生要补课(不能输在起跑线);工人要加班(时间就是金钱);知识分子要兼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恨不能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换钱。学生体质下降,工人过劳死,知识分子英年早逝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挣钱的压力巨大,所谓“效益就是生命”,哪里还有时间和心情去关注哪怕曾经真的喜爱过的地方戏呢?以上海越剧为例,2013年1-7月共演出越剧108场,足迹遍布上海市区、嘉定、松江;浙江乐清、嘉兴、温州、德清、金华、绍兴、温岭、杭州、余姚、海盐;海南海口;江苏苏州、南京、常州;湖南岳阳;湖北武汉和深圳、香港等⑥,所演出的剧场有大有小,平均以千人计算,总座位数也只有10多万个。而这些地方的人口总数当以亿计,也就是说即使场场爆满,看戏的人数也不足千分之一。一个地方通常也只有一两场或两三场。我们曾在一个社区调查,近五年没看过任何一场戏曲现场演出的居民竟占64.8%。某省重点高校新招收的戏剧戏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竟有2/3以上的同学入学前没看过一场戏曲演出。由此可见,地方戏固有生存空间的改变和人口成分的变化以及人们心理压力的加重,使得地方戏处境艰难,回天乏力,风光难再。
三、忧思之三:先天不足,后天罹患,发展道路愈见迷茫
要说地方戏的先天不足,首先就应当看到我国的各地方戏剧种其原本就是特定历史阶段、特定区域的产物,与时代和地缘密不可分。究其本质,它们是阶段性、过程性的。当历史发展,时过境迁抑或物是人非的时候,它的衰落甚至消亡便在所不免。有道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地域之皮不存,地方戏之毛便无所依附。诚然,由地域文化而产生并代表地域文化是我国所有地方戏的基本特征。在一定历史阶段它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黑格尔说过,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但他同时又说,一切合理的都是注定要消亡的。这就指出了事物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因为存在的合理是由存在的阶段赋予的,而阶段只是一个过程,是必然要向前运动的。变化了的阶段迅即会宣告原有存在的荒谬。在新的阶段面前,如不能与时俱进则必然消亡。但“与时俱进”之后便很可能又不再是原有的“存在”了,这似乎已是一个悖论。这里,地方戏鲜明的地域特征、地方属性成就了它,也桎梏了它。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全面公有制的变革中,不切实际地把剧种行政化,剧团剧种化,演员单位化,使得这种先天的不足又因后天的罹患而加剧。
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们国家大体分为29个省级行政区,每省又有10多个市级行政区。于是,我们就把曾经在这些区域产生或流行的地方戏以行政区划命名,使之具有区划标识,从而与“地方”密不可分。例如,安徽曾是徽班的故乡、徽调的发源地,新中国成立后重新组建的徽调演出团体就被命名为“徽剧团”,意即代表安徽的地方戏剧团。之所以未称“皖剧团”,是因为当时的决策者误以为徽班徽调源于徽州,而“徽”在人们的语言习惯上又可代指安徽。安徽省会合肥,旧称“庐州”,简称“庐”。20世纪50年代组建国营剧团时,就把曾发生在以合肥为中心的皖中一带的“倒七戏”(又称“小倒戏”)定名为“庐剧”。是时,各地有影响的剧种都被冠以了区域标识,与行政区划捆绑在一起。在江西的叫“赣剧”;在山西叫“晋剧”;在广东的叫“粤剧”;在广西的叫“桂剧”;在河南的叫“豫剧”;在湖南的叫“湘剧”;在四川的叫“川剧”……这里也还有两种例外,一种是虽然没有用新的行政区划简称作剧名,但却以当地旧称作剧名,如陕西一带古称秦,其地方剧种就以“秦”名之,叫秦腔;浙江一带古为越地,其剧种就取名“越剧”;湖北一带古称楚,其地方剧种就叫楚剧。与上面的命名方式如出一辄,可谓殊途同归。只是古代中国行政区划较粗,板块较大,这类名称实际涵盖的区域远比今天广大。另一种是在当时看来历史较短,尚欠成熟的地方戏剧种(俗称小戏),则以其曲调、表演形式或发生地命名,如采茶戏、彩调戏、花灯戏、二人转、黄梅戏、柳琴戏、泗州戏、荆州花鼓等。这类剧种由于没有明确、单一的行政区划归属,反而获得了较多的空间自由。
这样的剧种划分,乍一看是承认了地方戏的地方存在,但实际上却是限制了地方戏的发展自由,固化了地方戏的生存空间。
地方戏的本质是地方民俗,是以语言、声腔和习俗、情趣为分切的。行政区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兼顾历史沿革、族类风俗,但更多地还是从管理需求和利益调和出发的,地方戏纳入行政区划,无形中就疏离了区划以外原流播区域的受众,也缩小了它的生存空间。更何况区划内的人群也并非都是它的接受者。一省之内,又有若干小地方戏剧种各占领地,肢解了这些以省份命名的“大地方戏”的接受群体。这也是几十年后这些“大地方戏”剧种境况不佳甚至岌岌可危的因由所在。相反,那些曾经不被看好、只以曲调、表演形式或发生地命名的“小地方戏”剧种倒曲径通幽、柳暗花明、异军突起了。如在安徽,徽剧明显不及黄梅戏;在江西,赣剧也不及采茶戏;在广西,桂剧比不了彩调;在湖南,湘剧也没有花鼓戏吃香……
与此相联的是剧种的剧团化。
以往的戏班,大多“一专多能”,兼善别样,很少单一经营。最著名的就是徽班,其不仅唱徽调乱弹,也唱昆曲,而且唱得很有成就。也正是由于它的这种多管齐下、多种经营,最终迎来了京剧的诞生。早期的黄梅戏班社也是黄梅戏、徽调、京剧、青阳腔“几下锅”,严凤英甚至还带头演过方言话剧。这使得初生的黄梅戏呈现了旺盛的生命力,王少舫先生就说它是“吃百家奶长大的”。遗憾的是,上世纪50年代我们一股脑儿为全国300多个地方戏剧种建立了不同层级的所谓“专业剧团”,虽然对于促进地方戏剧种的专业化功不可没,但也始料不及地限制了剧种的横向联合与多向度吸收。以本剧种为主的多元融合的生态格局被打破,使得剧种的抗衰能力明显不足,相当于盆栽的花卉和圈养的畜禽。这也是为什么60多年来,我们只看到地方戏剧种的日益减少和衰落而没能看到任何一个集多剧种之优长在新的时代凝结、诞生的新剧种的原因所在。一句“像不像”就足以棒杀剧种的全部好奇心。剧种一旦吸收了别曲,做了丰富,就立刻被斥为忘本、背叛、“四不像”。1956年康生在看了为党的“八大”演出的黄梅戏《天仙配》后,就曾对黄梅戏对其他剧种的吸收借鉴大加挞伐。说它是“话剧加唱的典型”,“力仿越剧”,“传统的表演技艺尽失”,并喝令黄梅戏“悬崖勒马”,“回头是岸”⑦。剧团守住剧种的纯粹性仿佛女人守住贞操,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
另一个问题是演员的单位化。
中国戏曲最初只有演员,是一门以演员表演为核心的现场艺术。20世纪,西方理论家在主张戏剧艺术的质朴时曾经发现戏剧的本质是演员和观众。也就是说,只要有了演员和观众,戏剧就存在。反之,则戏剧不存。中国戏曲,中国全部的地方戏早就用实践揭示了这个命题。只要有演员在,到处是舞台;只要有观众在,处处是剧场。演员属于有一技之长的自由职业者,可以四处搭班,是戏曲艺术中最活跃的因素。中国戏曲的程式化既是这种演员流动的产物,也是其前提。使演员可以很方便的流动搭班,无障碍通行。不要小看演员的这种流动自由,它带来了戏班和剧种的变革和优化。当年的徽班就曾在粤闽、江浙甚至川陕各地广纳人才,使其创造力大增,徽调徽班脱颖而出。当年的黄梅戏也是因为有蔡仲贤、王少舫这样的徽调、京剧演员的搭班才使得剧种快速成长,后来居上。20世纪50年代,随着演员身分的变化,所有的演员都依剧种分切被固定在一个具体的戏曲院团中,从此切断了与其他表演团体搭班合作的可能。久而久之,演员的创造力退化,表演欲望削弱,剧种最活跃的因素也因此沉寂下来。无论剧院(团)状况如何,他也只有一次选择定终身,从一而终,哪怕一辈子没有机会上台。演员创造的活力不解放,剧种的发展也就只能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
近30年来,由于评奖的利益驱动,又在这种剧种、剧团和演员的专有之外派生出剧目的专有。再好的剧目也只能在一个剧团上演,因为移植演出不属“原创”,无法参与评奖。即便是首演剧团,也不能在获奖后继续演出这个剧目,因为它还得创排下一个剧目去参加下一次评奖。久而久之,便只见奖牌不见剧目;只见创作不见保留;只见名声不见流传。演员也往往因为获奖而被雪藏——因为剧团需要推出更多的获奖演员。获奖之日往往就是演员的“谢幕”之时。
① 北京曾一度易名“北平”。
② 《当前舞台艺术创作生产现状、问题及对策》,文化部《艺术通讯》,2013年第7期。
③ 高云才、顾仲阳《城镇化改革:城乡共享红利》,《人民日报》,2013年11月7日,第2版。
④ 黄庆明《过去十年全国每天消失80个自然村》,《都市快报》,2012年10月28日,第11版。
⑤ 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3年5月27日发布。
⑥ 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上海越剧院网站。
⑦ 《康生看〈天仙配〉后的一封信》,《中国戏曲志·安徽卷》,中国ISBN中心,1993年版,第739-7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