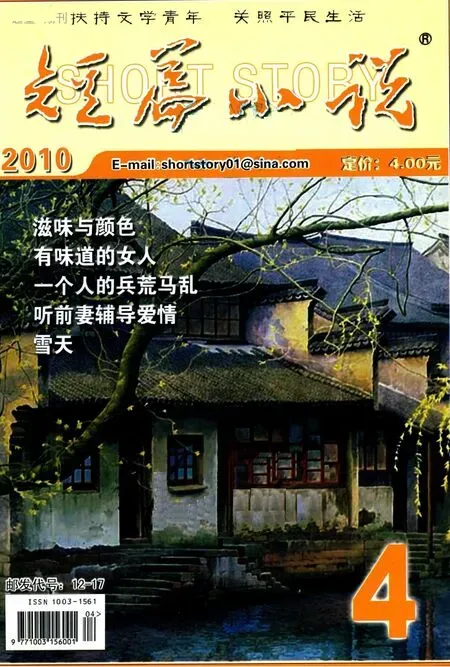小说二题
◎余文飞
小说二题
◎余文飞
棺材木
有栓老汉丑时就睡不住了。
昨夜商量的时候有点晚,罐子茶也吃大了,加上心里有事,猫抓火燎般的,这小半个夜里,有栓老汉根本就没曾合过眼。昨晚商量好的,等夜深人静后,连夜动手。可自打沾上铺头开始,那些商量好的细节又在有栓老汉的脑海里放映。怎样动斧头?树要倒向哪个方向?树倒后怎样快速修枝断节?甚至连丈量树筒子,都想了三个方案,用传统手拃?用臂展快速划拉?还是就用量好的尼龙绳子扯拉?想到这里,有栓老汉啪地给了自己额头一下。那尼龙绳是有弹性的,一拉一扯量得就不准确了,干嘛不用麻绳之类的,糊涂啊。还是用自己的手拃算了,虽说浪费些时间,可心里底气足。
一想到时间,有栓老汉再也躺不住了,一咕噜爬起来。
天空的星光稀稀疏疏,只透着些微弱的光亮,像萤火虫的屁股。这个日子是有栓老汉翻了几天老黄历选的,初三,宜祭祀,祈福,求嗣,斋醮,开光,入学,订盟,冠笄,伐木,修造,动土,起基,放水,交易,开池,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宜了。加上月黑风高,占齐了天时地利人和,办起事来指定顺当。
有栓老汉窸窸窣窣地摸到东厢房。屋里传出此起彼伏的鼾声,间或还有几声梦呓。
这几个狗崽子,有栓老汉低低地骂了一句。想了想,把要推开门的念头打消了。让他们多睡一会儿,养足精神才是。得叫女儿和儿媳赶紧起来弄口吃的。有栓老汉赶紧又向西厢房摸去。
到底是女人家,警醒。有栓老汉轻扣了两下门,屋里就传来大女儿的声音,爹,起来了。
有栓老汉趁着女人们起身的工夫,摸出烟袋,卷了一支烟点上。几口惬意下去,身上暖和了不少。
三个女儿鱼贯出了门,唤了有栓老汉一声就进厨房去了。儿媳压后了几步,嘴里嘟嘟囔囔着什么。有栓老汉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在黑夜里却没有烟锅上的火头明亮,只好干咳了一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老话说得好,女儿是父母贴身的小棉袄。儿媳是人家的小棉袄。有栓老汉在心头叹着气。
有栓老汉就在心里想着老伴。老伴也是自己的棉袄啊!可惜还没穿够就先去了。
厨房里亮起了蜡烛,有了声响。有栓老汉闲不住了。把顺当在门后的家什拿了出来,点了一截蜡烛,一一看了个遍,把几柄斧头拿在手里,啐着吐沫星子,试试锋利的程度,还是不放心,又找来磨石,逐个磨了一遍。
儿媳走向东厢房,招呼男人起床吃东西,叫了几声都没有动静,声音便大了几分。有栓老汉急了,虎着脸吼了一声,声音小点不行吗!
儿媳慌了一下,怔怔地看着有栓老汉。老汉一愣,随即明白自己的声音更大,赶紧闭了嘴,把想涌出的第二句狠狠地咽回喉咙里去。
三个姑爷都起来了,揉了揉惺忪的眼睛,在儿媳的引领下进了厨房。厨房马上就响起了稀里哗啦的吸面条声。
有栓老汉一看儿子还没影儿,几个大步就冲进东厢房。儿子还在捂着被头呼呼着哩。有栓老汉气不打一处来,又不敢大声呵斥,一拉被子就把儿子扯下床来。儿子惊了魂,跳起身来。随手就把床头灯打开。耀眼的灯光刺了有栓老汉一个措手不及,忙不迟疑地用手遮住眼睛,一叠声就低低地骂开了,小狗日,你怕不招摇啊,坏了事老子剥了你的皮。
儿子自知理亏,赶紧熄了灯,也不等有栓老汉再骂,提着外衣就抢出门去。
每人一大海碗面条,里头还卧着四只煎蛋。有栓老汉划拉了一口,把四只煎蛋每人一只拨到四个男人碗里。男人们推辞躲闪,一看老汉虎着脸,只得接了。面条下了肚,有栓老汉冲三女儿努努嘴,吩咐道,去,把我铺头底下的那罐酒拿来。霜降节气过了,夜里冷得很,几个男的每人只准喝两盅,多了误事。女的也勉强喝几口,暖暖身子,别被寒气侵了骨头。
酒拿来了,大家咧着嘴,都喝了。儿媳端着杯子,迟迟不肯下口。有栓老汉催促了几声,皱了眉头。
儿媳红着脸,好半天才嗫嚅着说道,爹,我怕是,怕是又有了。
有栓老汉看向儿子。
都三个月了,前两回不是没保住流了吗,怕这回也……所以就没给您说。儿子声调瓮声瓮气的。
你这龟儿子,这么大的事都不跟老子商量,差点坏了老子的孙子唷。有栓老汉噌地站起来,一巴掌就扇在儿子的肩头上,脸上却堆上了笑,转向儿媳细声说道,闺女,你就别去了,赶紧回去睡觉,老大,老二,赶紧送弟妹去休息。
爹,没事,我去帮助拿拿手电什么的也好。
要你去!几个大男人,一棵树嘛,还不是菜地里拔棵葱一样轻松。有栓老汉声音低了一个八度。
大女儿和二女儿赶紧喜滋滋地拉扯着弟妹去了。
三女儿要收拾碗筷,有栓老汉赶紧拦住。吆喝道,大家赶紧收拾东西,走,别误了事。却忍不住呵呵地笑出了声来。
目的地其实不远,就在村西头的洼子地的地埂边。大家蹑着脚步,踩着刚刚染起来的白霜,有桩喜事暖着心,浑身都轻快了不少。有栓老汉刚刚抽完剩下的半截叶子烟,就到了。
田野里稀稀疏疏矗立大大小小的树木,像一个个暗夜里的武士。
有栓老汉把烟锅头往腰上一别,一路小跑冲向了其中的一棵大树。
只见大树耸立云天,那些泛着微光的星星就像蹲踞在树梢的小精灵。
虽然隔三差五都要来看看,可有栓老汉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从大女儿手中接过手电筒,绕着大树就转了几个圈。转着转着,抱着大树吚吚呜呜地哭了起来。
寻阳村千百年来传下来一个传统,一个孩子出世,他的家人就要在自家的田间地头种下一棵树,唤做棺材木。这棵树在家人的精心照料下伴着孩子成长,直到孩子老了,数十年的时间,树木已经长大成材,适当的时候,就把这棵树伐了,做成棺材,为老人仙去后入土送终。
这样的习俗伴着寻阳村人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最近几年,忽地冒出来个护林养林,禁止乱砍滥伐的政策。寻阳村里那些大大小小的树木就被相关部门盯上了,隔三差五到村里张贴告示,召开村民大会。把村里的大小头头唤到乡里、县里,左叮嘱右勒令。就是一句话,种树不反对,多多益善,砍树就不行。村子里的墙面上,到处都是用石灰浆刷的诸如“栽树就是修水库““谁砍树谁坐牢”等字眼的标语。
寻阳村的人傻眼了,没了棺材木,人咋死哩!
就在大家心里没了底的时候,村长九十六岁高龄的爹忽地卧床不起了,村长家葛根塘地边的大松树一天夜里忽然不见了。等到老人出殡那天,新做的棺材散发着松木的清香。等到相关部门闻讯赶来,村长说树是被人偷了。无凭无据的,相关部门草草罚了村长一百元钱,罚村长家种二十棵树,事情就过去了。
有了先例,那些大树便偷偷地没了影儿。
有栓老汉今年七十有二了,上个月刚过了生日,用农村人的计算方法,已经年满七十二,吃着七十三的饭了。俗话说“七十三(丧)八十四(死)”,村里的人和儿孙们虽都说有栓老汉有硬朗朗的身子,活个一百岁还有零头,可有栓老汉心里不踏实,担心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谶语。大前年没了的栓柱老汉,七十三岁,卸一背篓苞谷,蹲下去就再没有站起来。由于事先没有准备,花了大价钱从别人家买了一口棺材,好歹还是亲戚,人家还八九分的不乐意。
偷着砍树是个公开的秘密,有栓老汉偷偷问了几个知心的人,人家只是嘿嘿地笑,说那事只能自己掂量,聪明人装糊涂就行。怎样操办?人家不说,问急了,拍拍屁股就走。有栓老汉知道大家的顾忌,这些年,人心不古,谁愿意给人留下口实。
就着过生日的当口,有栓老汉把几个女儿、姑爷和儿子、儿媳叫在一起,把事儿就定了。偷偷把树砍了,偷偷把寿材备下,计划不如变化快,免得夜长梦多。
三个女儿贴上前来,好说歹说,劝住了父亲的悲声。
有栓老汉定了定神,四处看看听听,确定除了风声就没了其他异常迹象,便一一做了分工,儿子瘦小,先爬上树拴绳子,方便一会儿拉拽树的倒向。三个姑爷和自己分两班砍树,轮休下来的两人望望风。三个女儿打手电,打打下手。
静寂的夜晚开始紧张起来,斧头创造着有节奏的声响。刚开始,砍几下歇一会儿,查查周围动静,到了后来,胆子大了起来,便一个个嘿哟嘿哟地出着夯力。
歇口气的机会,有栓老汉又把周围仔细地看了一遍。白天装作漫不经心松过的地应该是能消减树倒下的声响。小心驶得万年船,虽说偷偷砍树村里人睁只眼闭只眼。可村子离乡镇也就四五公里,乡里林业站的人兴头上来时还是会来偷偷蹲点。一个月前,长命家半夜砍树就被逮了个正着,几个喷着酒气的汉子还把长命那个日鼓冒天的儿子打了一顿,罚款二千元。事后才听人说,几个林业站的家伙打了半宿麻将,吃了回宵夜,不知是谁提的建议,说出来溜溜酒气,稀里糊涂地就把车开到寻阳村头了,长命家的树刚砍了七七八八,树倒的声音把人给引来了。撞在枪口上的兔子还会得到什么好的。
有栓老汉一边想着一边走远了些,周围还是只有风声,心里惬意了起来。胡乱地尿了一气,不由得激灵灵地打了个寒战。
回来时,儿子已经拴好绳子,从树上下来了,帮着砍树。女儿心疼着要父亲歇一歇。有栓老汉也不推辞,卷了一只叶子烟点上,左左右右地散转着指挥砍树。
村里传来了一声鸡啼。已经寅时了。有栓老汉有些急了,拎着斧头支开儿子,木头渣片四散飞溅起来。
爹,可以了。儿子低声道。我们一起拽拽试试。
有栓老汉扔了斧头,叫着大家牵着绳头使劲拽了几下,大树还是纹丝不动。几人轮番上前,又砍了一气。
眼看粘连不多了,有栓老汉招呼大家扯着绳子又折腾了一回,大树似乎晃了几晃,还是没有倒的意思。卸了气,有栓老汉皱了皱眉头,骂道,这狗日的还硬邦得很。转头对儿子说,等到咱孙子出世,种棵柏树得了,这狗日的松树绵得很。顿了顿,叹了口气,又道,唉,你和老子一样,中年才得子,也不知以后的树能不能长成材。
儿子应了一声,闷闷的。
有栓老汉四处看了看砍口,粘连确实不多了。吩咐道,你们拽着绳子,我再来几下。
大女儿有些担心,说道,爹,还是让他们年轻人来吧,万一一个不慎,树倒了,他们灵活些,闪得快。
没事的。有栓老汉抹了一把汗水,仰着头看了看大树,喃喃自语道,这狗日的,和我较上劲了,我倒要看看,它的骨头硬还是我的斧头硬。
你们拉扯着,让树往西边倒才好,砸在松软的泡地里声响也小些,要注意避让啊,小心那些树枝。说完,有栓老汉抡起斧头,狠狠地劈了下去。
忽地,平地起了一阵风,只听得嚓嚓几声爆响。大树轰的一声,倾金山倒玉柱似的砸了下来。有栓老汉着地一滚,却被田埂一挡,没有滚开,顿觉眼前一黑……
咯咯——咯——村里传来了第二遍鸡啼……
日 蚀
凌晨时分,长山憋不住了,一咕噜起来,急匆匆地撞进茅房,掏出鼓胀胀的家什就尿了一气。随着粪池里那飞流直下才弄得出的声响渐渐小去,胀得有些隐隐作痛的小腹舒服了不少,坚挺着的家什也渐渐疲软了下来。长山莫名地笑了,掂量了几下那活儿,把不情愿的几粒抖落。拾掇好裤头,看了看四周,仍然黑黢黢的,吹着飕飕的风。
回到屋里,长山不情愿地扒着门楣又看了看天空,天上的星星依旧亮得耀眼,丝毫没有隐退的样子。远处传来几声犬吠。长山侧着耳朵听了听,应该是老黑,便嘿嘿一笑,自言自语道,这狗杂种,中气十足,门倒是把守得实在。
今天答应帮水莲割谷子,可黑黢嘛咕的也不好就去叫门。想了想,长山决定再躺一会儿,刚才那一泡尿,弄得都有些虚脱了,得养养精神,今天可是帮水莲,得要加倍的干劲才行。
回到床上,长山掖了掖被子,把头枕在脑后,一闭上眼,水莲就浮现了。水莲白皙得很,与这个高天厚土的云贵高原的小山村有些格格不入。山里女人,整天风里雨里,加上与太阳离得近些的缘故,一个个晒得或暗红或黝黑,跟土地的颜色差不了多少。水莲可不同,用她男人的话说,水莲抹下一把汗都是白生生的,可惜男人无福消受。一次,犁地的牛发了疯,犁头把男人犁成了血糊糊的两半,遗言都没有留下半句。水莲便拉扯着幼小的儿子和婆婆相依为命了。
那头肇事的畜生被村里人乱棍打死了。长山忽然觉得自己就是水莲的牛了。想到这,长山忽地睁开眼,嘻嘻地笑,胯下蓦地兴奋了起来,忍不住摸了过去,发着狠劲地撸了几下,哼唧了几声,弄了一裤裆黏糊糊的东西。脑里一片空白,浑身轻飘飘的像一团棉花,索性也懒得收拾了。一侧身,昏昏然睡去。
水莲粉嫩的脸羞答答地抬起来,长山四处看了看,刚要凑上嘴去,忽地从田埂下冒出来一个黑影,扬起镰刀刈了过来。长山啊的一声怪叫,直挺挺地坐了起来,出了一身冷汗。
长山定了定神,听得门口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水莲好听的声音从门缝里挤了进来。长山赶紧翻爬起来,感觉裤裆有些黏肉,一回味,羞了个大红脸。赶紧胡乱拉扯好裤头,应着声开了门。
门一开,初起的阳光绣花针样地扎来,刺得长山睁不开眼,赶紧用袖口遮住眉骨。依稀看到水莲一脸的嗔怪,赶紧道歉,起迟了,起迟了。
水莲拧了下眉头,关切地道,长山哥,你莫不是生病了,咋一脸红通通的。要不推迟一天再割吧。反正也不在乎早一天晚一天的。
没……没事……睡的……睡的。长山感觉额头出了汗,赶紧用袖口顺势抹了一下。
真的没事?水莲扑哧一笑,看你急的!
田里已经插了些人,看到长山来了,都扯着嗓子打招呼。
长山啊,今天帮水莲家呀!
嗯哪。
哪日帮我家打两天谷子?
快啰,快啰。
长山,你可是几天前就答应过我家的活的啊……
忘不了,忘不了。
还有我家哩,大后天,掰倮倮桃树的那片包谷,早就把酒都给你打好了的。
是呢,是呢。
……
长山应着声,手上可没闲着,嗦嗦嗦嗦就撂倒了一趟。水莲赶紧跟上,捆好谷把,谷茬朝下团着一顺,谷把子便直立着叉开,整整齐齐地摊晒开来。
嗦嗦——嗦嗦——
镰刀在长山的手里飞快地划拉着银光。水莲左一把右一把地甩着侵略到眼窝前的汗水,那些抹不及的就顺着衣领溜了进去,像一群顽皮的虫子在爬,痒酥酥的。水莲只好趁着长山不注意,胡乱挠几把。
不一会儿,田里已经立起来一溜串谷把。
难得的好天。长山直起身,使劲锤了几下腰,抹了一把汗,眯着眼看了看太阳。太阳已经四五根竹竿子高了。
是呀,谷把晒到傍晚,也怏怏的了。长山哥,歇会儿,喝口水。水莲随手拾了两个谷把往田埂上一横,当做凳子,招呼长山坐下歇歇。
递过一块毛巾,水莲便扭身去埂边拎水壶。
长山把毛巾印到脸上,有些湿润润的,透着淡淡的体香,该是浸着水莲的汗液。慌得赶紧拿下来,捏在手里。
水莲拿过水壶,倒了满满一杯水,递给长山。长山接在手中,眼睛的余光不经意地扫了水莲一下,只见水莲已湿透了衣服,浅色的确良衬衫掩不住多少秘密,该凸该凹的地方便有棱有角了,随着水莲的动作乱颤,顿时臊了个大红脸,赶紧把目光游离开来,扬起罐头瓶子,装作喝水,咕咚咕咚下了一气。还好罐头瓶子是个装过樱桃的,红红的标签贴纸还没有撕去,倒还掩映了脸上的气氛。
水莲夺过毛巾,嗔道,看你累的,汗也不擦擦。也不由分说,一股脑儿就把长山的脸和脖子抹了一遍,抹得长山低着头嘿嘿地笑。
水莲愣了愣,脸上泛起了红晕,心里涌起些心事来。
长山是个孤儿,孤苦伶仃的那种。不仅没有父母,连身世也没有。村里集体土地下放那年,村南头的水碾房角落里蜷缩着一个嘤嘤抽泣的孩子,把半夜里巡查碾房的村长吓得怪叫。
村里人几经盘问,孩子除了胆怯地缩作一团,就只会摇头。在那样年代,村长也不敢收留,汇报到乡里、乡里汇报到县里,最后来了几拨人,问不出个所以然,县里指示就地解决,随便安置在村里得了。
土地包产到户,牲口也到了各家各户的房檐下。村里的牲口房空了,村长做主,孩子就住了进去,有了个户口。
孩子后来就叫了长山,身世一直成谜。只是有一年,村里逮住了个小偷,闲散多年的民兵队长二胡子,兴高采烈地用纸片糊了套牛鬼蛇神的行头,伙同几个闲汉押着小偷游街。长山看到后,浑身发抖,当场就昏厥过去,躺了几天。
长山象征性地分得几块薄田,小时候种不来,就给别人种,自己饥一顿饱一顿地讨嘴,吃着百家饭,穿着百家衣长大。身子骨有些样子了,土地收了回来,学着拾掇,慢慢就侍弄得顺溜了。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长山长成农村里的好把式,又舍得出力,自家的几块小土地随便几个来回就弄完了。便开始感恩,张王李赵,只要吆喝一声,不冲突,立马就应承了,出些夯力,顺便也弄个肚饱。
随着长山年龄的增大,看在眼里的好心人便偷偷帮着央了几回媒婆子,女方一来,虽然人是没话说,可看看破屋烂椽,还是摇头而去。一来二去,时间的河流把长山从毛头小伙子洗刷成了三十好几的老光棍了。
长山也断了念想,倒是越发助人为乐了。
水莲从远村嫁过来时,长山跟着去迎的亲。那天宴席上打赌,长山一口气吃了八碗泛着油光的红烧肉。水莲的男人无话可说,垂头丧气地看着水莲,苦着脸笑。一帮亲朋好友瞎起着哄,推推搡搡地要长山香水莲一口。长山急了,红着脸奋力钻出人堆,嚷道,哪能呢!哪能呢!玩笑着哩!
长山的想法冒了头却是在水莲的男人死后。
那天傍晚,长山像往常一样和老黑在河埂上溜达。老黑忽地对着苞谷地里乱吠了几声,长山走近一看,河边散乱着一堆衣物。便唆使着老黑往苞谷地里冲了进去。在一片压倒的苞谷秆上,水莲赤裸着上身,嘤嘤呜呜地哭。老黑顺着噼里啪啦乱响的苞谷稞追去,不一会儿,扯着一块血淋淋的裤腿折回来。
水莲没有说是谁,只是哀求长山不要把这事说出去,免得婆婆担心,也省去村里人说闲话。
长山知道寡妇门前的是非像一盆越洗越脏的水,便把事儿沤在了肚子里。事后,长山两天三夜睡不着觉,一闭眼就是水莲花花的白。再后来,长山一咬牙,把相依为命的老黑送给水莲家,老黑死活不肯,长山就天天夜里牵着老黑蹲在水莲家墙角下,直到老黑接纳了水莲一家……
水莲——水莲——长山娃儿——长山——婆婆老远地叫唤把两个人的心事惊醒。
水莲赶紧应着声,一抬头,婆婆拄着拐杖拎着个提篮踽踽而来。老黑在前面开路,早一溜烟冲到长山面前,一个虎跃,没头没脑地舔了长山一脸的粘液。
娘,您咋来了!
大妈,您咋来了!
水莲和长山几乎同时叫出声来。都不约而同心里一紧,水莲赶紧接过提篮,把娘扶坐在田埂上。
婆婆四处看看,叹了口气,唉,你们两个娃儿呀!一个早就割了那么多!都日上几个三竿了,也不回去填填肚子。这点谷子今天割不完么明天割吧,累坏了咋办哩。我在家做好饭左等右等,人家其他家都回家歇工喝茶了,可就是不见你们回来,只好自己送来了。水莲唷,你咋能把长山当牛使唤。
娘,苦着您了。水莲一边说,一边赶紧添好饭菜递给长山,歉意地笑笑。
闻到饭菜香,长山才觉着确实饿极了。跟婆婆客气不了几句,稀里哗啦就下肚了三大碗饭。
吃好了饭,婆婆要帮助捆谷把,水莲和长山赶紧好说歹说把婆婆劝走了,嘱咐她赶紧回家照看孙子。
肚子少了吵闹,长山来了干劲。那些回去吃饭的还没影儿,一大片黄澄澄的稻田里除了偶尔有鸟儿撒着欢的一两声鸣叫,就只有一把镰刀嗦嗦嗦嗦的声响了。
天空忽地暗了下来。
长山和水莲都不约而同地直起身来看了看天空。太阳像被一大块煎饼贴住,顿时面对面不见人影。
长山哥,咋了?
狗日的二郎神的哮天犬,吃吃月亮就行了,咋太阳也咬。
长山哥,你在哪儿?我怕!
不怕,我在你身边哩。长山扔了镰刀,顺手摸了过去。
水莲一个趔趄,扑倒在长山怀里。脚下谷把一绊,两人滚倒在地。
四野黑得瘆人。长山紧紧地搂着水莲,软绵绵的两只兔子贴着他的胸口,瑟瑟发抖。远远地传来敲锣打鼓的吵闹声,是村里人在用古老的方法驱赶天狗。
时间飞快,天空忽地有了亮色。稍许,太阳出来了,那团黑乎乎的面饼不知甩到哪里去了。
长山回过神来,轻轻地扶起水莲。好一会儿,水莲才缓过劲来。
水莲看上去还心有余悸,喃喃地道,长山哥,咱们回去吧,今天邪门得很,剩下的明天再割也不迟。
长山想了想,点点头。
两人收拾了家什,一低头,看到对方的身上都糊上了许多的烂泥,都红了脸,略一踟蹰,便默默地帮着鼓捣了几下。
忽地,田埂头蹦出个人来。一叠声嚷了起来,你们两个干的好事。
一抬头,二胡子一副暴跳如雷的样子。
干……干啥好事。长山怒吼了一声。
长山哥,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咱们走!水莲狠狠地剜了二胡子一眼。扯了扯长山,扭头就走。长山略一踟蹰,脑海里闪过早上的怪梦,闷哼了一声,拔脚就走。
你们等着,两个不知廉耻的东西。
长山急了,几个箭步冲到二胡子面前,抬手就给了两记狠的。叫道,狗东西,你骂谁不知廉耻。
二胡子瘪了嘴皮。周围也不知什么时候,来了几个拎着镰刀的赶活计的。大家纷纷连说带劝,把扭在一起的两人拉拽开来。
二胡子见来了人,嘴皮又鼓了起来。嚷道,大家给评评理,我晦气得很,不小心撞见两个不要脸的人干的好事,还不得了,想杀人灭口哩。
大家都知道二胡子的劣行,哂笑了起来。二胡子急了,叫道,你们看看,两人在田里乱滚,那一身泥还在呢!
水莲气急了,你——你血口喷人——话音刚落,晕了过去。
长山赶紧扶住水莲,瞪圆了眼,吼道,我们清清白白,只是刚才——刚才——黑咕隆咚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
摔倒了,滚在一起了吧!二胡子左顾右盼,肆虐地眨着眼皮。
看着大家似信非信的眼神,长山急了,抡起拳头就冲了过去。
二胡子赶紧躲在别人身后。
村里人都看着长山长大,见状都劝住长山,表示不会听二胡子乱嚼牙巴骨。
二胡子骨碌了几下眼珠,故作神秘地说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一回,河埂边,苞谷地里——
你说什么?幽幽醒来的水莲怪叫起来,明明是你这个无赖,却要冤枉——
长山冲破人群,硕大的拳头结结实实地砸在二胡子眼眶上,一个乒乓球大小的东西掉了出来……
长山被派出所带走了,他后来被判了几年,出狱后就再没有踪影。
二胡子瞎了一只眼,有一天夜里,掉进了自家的厕所里。捞起来的时候已经硬了,喉咙处似乎被什么东西咬了几个血窟窿。而从那以后,老黑就不见了,人们找遍了周围十里八村,都没见到它。
责任编辑/董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