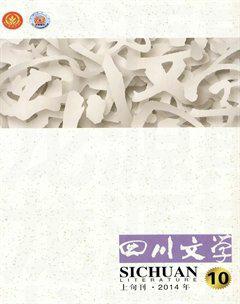短篇二题
◇刘平勇
井
之前,整个营盘五十多户人家就只共用一口井。天刚放亮,挑水的人们就排着长队来到井边挑水。排到后面的,至少要等半个小时。
正和老汉的家离井足有一里地,隔着一个小山包。路是土路,泥是黄泥。二尺来宽,对面走过,必须侧着身子。正和老汉挑着空木桶,爬上缓坡三分钟,走下缓坡三分钟,便可到达井边。要是挑满了水,爬上缓坡四分钟,走下缓坡四分钟,方能到家。到了雨季,挑水就特别艰难,路滑难行,黄泥淹过脚背;到了冬天,冰雪覆盖地面,行走起来一步三滑。经常会有人摔倒,轻则弄得满身泥泞,重则摔烂木桶,伤了身子。营盘村每年都有因为挑水摔伤身子的事发生。正和老汉两年前就摔断了一只小腿,半年才能行走。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常常回忆起那时许多温暖的场景。挑水的人,大多是大小伙、大姑娘们,如果家里孩子还小的人家,大人当然就得亲自去挑。男男女女排成长队,大小不一的木桶担在肩上,蔚为壮观。大家说说笑笑,窄窄的河埂上充满了欢声笑语。姑娘小伙们窃窃私语,大人们嘻嘻哈哈说着成人的话题。也说家长里短,也说奇闻怪事。张家的猫一窝下五个儿,李家的鸡一天下三个蛋,王家的女儿出嫁三转一响全部配套……
后来,正和老汉的四个儿子在家门口挖了一口两丈多深的水井,还买了一个坠了铁块的桶,用绳子拴好,只需轻轻往井里一丢,桶就歪在水里装满了水,一提,就把清亮亮的水提了起来。这井水又旺又清,味道又好,正和老汉很是高兴,用一个很大的竹簸箕罩在井口上,谨防孩子们到水井旁玩水,又防止草屑灰尘被风吹到井里。
再后来,营盘村的好些人家,都仿效着在自己家门口挖了水井。隔壁的正德老伴家,由于只有一个儿子,劳力欠缺,没有挖井。正和老汉就主动上门,让正德老伴到井里打水。
正和老汉说,大嫂子,你就没有必要跑那么远去挑水了,用我家井里的吧!那井可深了,水清幽幽、满当当的,井水嘛,又不花钱的东西。
正德老伴说,大兄弟,咋个好意思呢?
正和老汉笑着说,有啥不好意思的,隔壁两邻的,不就像一家人吗?
正德老伴说,等儿子打工回来,我也让他给我挖一口。
正和老汉说,有啥必要呢?何必花精力!说着就提了正德老伴的两只木桶往外走,我去帮你打来!正德老伴说,不用不用,我自已去打呀!连忙放下手中的活儿追出来
一会儿,正和老汉就提着装得满当当的两只木桶回来了,放下木桶,直起腰来,脸微微发红。正德老伴在一旁笑着说,大兄弟,都这个岁数了,还这么有劲!
正和老汉说,大嫂子,我小你两岁呢!大男人嘛!正德老伴笑,正和老汉也笑。
之后,正德老伴就经常过来打水。正德老伴提着空木桶过来,正和老汉就帮着打水,然后提着装满水的木桶去正德老伴的家。正和老汉走在前,正德老伴走在后,两三句话的工夫,就到了家里。话还没说完,于是俩人就站着再聊一会儿。
孩子们去上学后,正和老汉一个人守着四间瓦房一个场院。正德老伴是一个人守着一间瓦房一个场院。每天都做着大同小异的事。就是扫扫场院,做做饭。太阳好的时候,提个凳子坐在场院上晒太阳,看云彩,听风在院墙外呼呼地吹,或者打瞌睡,或者随心所欲想些远远近近的事。要是天气冷,就坐在火炉旁看着空空荡荡的屋子发呆。
因为打水的事,正和老汉和正德老伴交往就多了起来。他们经常坐在场院里有一句无一句地说话,说的无外乎是村子里的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情,当然也说他们年轻时候的事情。有一搭无一搭的,断断续续的,有时甚至是前言不搭后语的,颠三倒四的,就像是日子是一个花瓶,哐啷一声掉在地上,满地的碎片。他们东一块西一块地拾着,但无论如何都拼凑不出原有的样子了。
正德老伴说,那晚老牛皮家的牛被两个贼偷走了。老牛皮发现了,要冲上去,但贼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刀。老牛皮就大喊抓贼,不一会儿,村里听到喊声的老人们都起来了,有几个孩子也起来了,但是大家不敢往前追,也追不上,只有两条狗追了上去,但被两个贼用刀砍伤。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贼赶着牛走掉。
正和老汉叹息说,村里的年轻人都去打工了,咋个行?遇着这样的事,咋个办呀!
正德老伴说,我也是觉得,村里的年轻人走光了,要不得。你看前不久黄狗大爷死了,连个抬棺的人都找不到,幸亏黄狗大爷的儿子有办法,花钱在城里请了一帮抬棺队的人来,才把人抬了。你说,要是换了别人家,咋个整呢?
说着说着,话题不知不觉又转移了。
正和老汉说,大嫂子,你该记得,你刚嫁给正德大哥时,我还去闹房,我说了个吉利:清水下田,浑水栽秧,先生儿子,后生姑娘。你的脸呀,比柴火还要红。那时呀,我也老大不小的了,还躲在你家后窗下听床呢!
正德老伴笑了起来,张着掉了门牙的嘴巴。说,我知道的,那时就数你调皮!
正和老汉呵呵笑着,说,那时我和几个小伙伴,就肯当跟屁虫,在你身后偷看你的大辫子在屁股上甩来甩去。
正德老伴用手摸了摸稀稀疏疏的白发,叹息说,那时我的头发就是好,有人用一百个鸡蛋换,我都没有换。现在都白了,快掉光了。
正德老伴又呵呵笑着说,说起鸡蛋,我想起来了,你那时好能吃呵!供销社的老刘跟你打赌吃八十个鸡蛋,你要是吃不下,又就要为他家挖出两亩田。你居然一口气吃掉了!害得老刘家婆娘跟老刘吵了一大架,老刘的脸被抓了五条血痕,老刘家婆娘也被老刘打落了两颗牙齿!
正和老汉呵呵笑着,一脸的骄傲。说,我那时的力气是营盘村最大的,我挑过二百八十斤洋芋走十里山路不歇一口气!
长马头细马尾的事翻来覆去地说,总也说不够,总是呵呵笑着,开心的样子,像两个老儿童。
正德老伴今年六十二岁了,大正和老汉两岁。正德老伴的丈夫正德在十年前,死于非法开采的小煤窑,正德老伴哭了七天七夜,哭瞎了一只眼睛。她的儿子儿媳三年前就到广州去打工,年初出去,过年回来,丢下一个六岁的女儿菊花在家里,由正德老伴照管。现在,正德老伴的孙女儿菊花都九岁了,在村小学读三年级。正德老伴做事麻利,爱干净,经常把菊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菊花学习又好,屋里的墙上都贴满了一排大红大绿的奖状。正和老汉为此很羡慕,他的四个孙儿看上去也很聪明,但就是很少拿到大红大绿的奖状。
正和老汉的生日是腊月二十七,再过两天就是除夕。之前正和老汉是没有过生日的,因为农村只给老人过生日,在农村人的心目中,只有年过花甲才算老人。今年正和老汉就进入花甲了,就变成货真价实的老人了。可就在腊月二十三的中午,一件没有任何预兆的事发生了。
正和老汉有四个儿子——大树,二树,三树,小树。年龄都是只相差一岁。也就是说,正和的老婆刚生完老大,立即就怀上老二,以此类推,直到生完小树后,正和老婆患了怪病丢了性命为止。正和老汉的四个儿子又分别生了儿子。大树的儿子八岁,读二年级,二树的儿子七岁,读一年级,三树和小树的儿子都才五岁,读学前班。他们虽然都各自有自己的大名,但正和老汉习惯把他们叫大宝二宝三宝小宝。
四个娃儿的爸爸妈妈都到外地去打工了,说是去挣钱回来盖砖房,供娃儿们读大学。正和老汉就在老家照管四个娃儿的学习和生活。正和老汉的四个儿子儿媳很感激他们的父亲,他们能够放心地到外地打工,全靠老父亲照管孩子。每年回来的时候,都买了好多东西来孝敬正和老汉。正和老汉很高兴,出门进门都是满脸的笑,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今年四个儿子齐刷刷地向正和老汉承诺,说老人已到花甲之年,他们一定提前到腊月二十四赶回来,用两天的时间准备,热热闹闹地为父亲庆贺六十大寿。正和老汉满心欢喜,进入腊月间就开始数着日子,盼着儿子们回来,照管孙子也更仔细了。他晚睡早起,为孙子们准备早点,为孙子们做好早饭、晚饭,督促孙子们写作业,照管孙子们洗脸、洗脚、睡觉。正和老汉对孙子管得很严,好在娃儿们很听话的,偶尔调皮也没有过分。
腊月二十三这天,阳光很好,村子里外出打工的人陆续回家过年了,天空中不时响起孩子们燃放的鞭炮声,正和老汉想,明天四个儿子齐刷刷地回来了,他们回来为他庆贺六十大寿。
都中午了,正德老伴还没有过来提水。这是不正常的,一般她都是早饭后就过来提水的。
大宝二宝三宝小宝在场院上追着玩。正和老汉对几个娃儿说,你们玩着,离井边远一点!我过去看看菊花的奶奶就回来!几个娃儿高兴地回答好。正和老汉每次要出去,都要这样交代,井口用竹簸箕盖着,正和老汉从来不准他们掀开竹簸箕。
正和老汉不知道的是,他越是禁忌,孩子们越是好奇。看到爷爷出门去了,四个娃儿可高兴了,二宝率先奔到井边要掀簸箕。
好在年龄最大的大宝还有点当哥哥的意思,连忙喊,二宝,当心爷爷的竹条!
二宝就把伸出去的手缩回来,讪讪地说,我又没掀开,我只是看看。
几个孩子大眼瞪小眼的,大宝便回屋去了。这时二宝对三宝和小宝说,你们看,这竹簸箕像不像观音菩萨的莲花宝座?
三宝小宝齐声说,像!
这段时间,娃儿们都在看《西游记》,对孙悟空腾云驾雾和观音菩萨坐在莲花宝座上的样子羡慕极了。
二宝说,我们不掀簸箕,只坐上去当一回观音菩萨好不好啊?
三宝和小宝齐声说,好!
二宝看了看屋子,没有见大宝出来干涉,就抢先坐在 “莲花宝座”上。双手合十,模仿着观音菩萨的神态。
三宝小宝看着二宝当了观音菩萨了,闹着也要坐上 “莲花宝座”,二宝不让,三宝小宝自顾着爬上去。刚挤着坐下, “莲花宝座”噼噼啪啪地散架了,刹那间,三个孩子全都掉进了井里。
正在屋里专心地玩着变形金刚的大宝,听到响声,连忙跑出来,不见二宝三宝小宝的影子,见井里有噼噼啪啪的声音,就跑过去一看,二宝三宝小宝像煮饺子一样地在井里扑腾。井水离井口足有两米深,大宝吓得不知怎么办,忽然想起来了,抓起门口的一把锄头从井口伸下去,大喊,二宝三宝小宝,你们抓住锄头,我把你们捞起来,下面是有人抓住了锄头,可大宝提不动,他努力地使劲,最后连人连锄头,倒被拉到了井里。
正和老汉从出去到回来,没有超过十分钟。
正德老伴果然病了,说是感冒,身子发烧,躺在床上,菊花正在端着碗为奶奶喂药。
正和老汉说,我说咋个不见你过来提水,就过来看看!
正德老伴说,她好久没有洗澡了,想到过年了,洗个澡吧,就烧了一盆水,抹一下身子,哪晓得就感冒发烧了,哎,老了,真的老了,身子骨变娇气了。要是在以前,一天到黑淋着大雨劳动都不会病。
两个老人长一句短一句地说了一会儿。
正和老汉说,我屋里有一种药,叫快克,可好了,我上次感冒,也发烧,吃两颗就好了。我回去拿来给你吃。大儿子上次带回来的。
正德老伴感激地说,尽麻烦你,谢谢了!不必不必!都快好了的!
正和老汉转身就要回去拿药,刚走出门,又转过身,提起两只木桶往外走。
到了场院,一看,四个娃儿不见踪影,他以为都呆在屋里,喊了几声就先去给正德老伴打水,这下,一眼就看见井口是敞开着的——
正和老汉的头嗡的一声,三步两步奔到井边,井里飘着几颗脑袋,有一颗脑袋还在动,是大宝。正和老汉连忙抓起一根木棒,伸到井里,大声喊,大宝,你抓住木棒!大宝就伸手抓住木棒,但好像没有半点力气,只是头露出了水面,嘴里吹出一口水,还微微睁开眼睛看着正和老汉!正和老汉往上提,那双抓住木棒的手就往下滑。正和老汉不敢再往上提了,他怕大宝的手完全滑离木棒,那就完了,看来大宝实在没有力气抓紧木棒了。
正和老汉就紧紧握住木棒,嘶着声音喊,大宝,你不要松手,我喊人救你!他就大声喊,菊花!菊花!你快过来!
菊花跑过来了,一下就被眼前的场景吓懵了。正和老汉说,你快去村子里喊人,喊年轻人来救人!
菊花一溜烟跑了。菊花在村子里大喊救命!喊出好多老人和小孩来,菊花就往回跑,后面跟着一群老人和孩子也在跑。
在外打工提前回来的年轻人王三狗听见了喊声,连忙跑了出来。他们赶到正和老汉的场院,正和老汉一脸绝望地扑在井口抓着一个木棒,他哭着说,救人!救人!
王三狗把木棒抓在手里,对着井里喊,抓紧木棒!抓紧木棒!井里没有半点反应。王三狗抬起头,看着周围的人,悲伤地摇了摇头。他快速地将拴着胶桶的绳子一头拴在木棒上,一头拴在自己的腰上,把木棒横担在井口,下到井里。他让村民再找一根绳子来,他用绳子拴住孩子的腰,让几个还有些力气的老人往上提,一个一个地把四个孩子提上来。
四个孩子摆在场院上,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站了一场院。悲伤的泪水,让空气都变得咸咸的。哭得最悲伤的是正德老伴。正和老汉已经不会哭了,他已晕过去好多次了。刚一醒来,他就用拳头砸地,他的一双手血淋淋的,十个手指都露出白骨。围着他的是一大群老人,他们束手无策,只是陪着流泪。
腊月二十四这天中午,正和老汉的四个儿子四个儿媳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陆续回来了。眼前的场景是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他们变得像木头人一样杵在场院里,之后就是抱头痛哭,把他们的头发一把一把地抓下来握在手里,大包小包的东西凌乱地丢了一地。
整个村子的人们都在忙着为四个娃儿准备后事。
谁也没有精力去在意正和老汉像个死人一样躺在床上。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正德老伴想去看看正和老汉。忽然有人惊叫着跑了出来,正和老汉死了。正和老汉是咬断自己的舌头而死的,嘴里含着半截舌头,枕头上的血都快干了,变成褐色的血块。他的眼睛绝望地睁着,怎么抹都闭不下去。
小广播
小广播姓黄,名字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了。营盘镇上至六七十岁的老翁老妇,下至三四岁的小孩,都叫她小广播。一是因为她的声音大,二是因为话多,三是因为嘴不稳,该说不该说的,都整天呱唧呱呶地说,就像村头电杆上的喇叭一样。
要是她家地里的黄瓜番茄被人摘了一两个,小广播可以站在地里骂个三天三夜,那些骂人的话,全是最恶毒的话:烂孤寡,五保户,望门寡,绝子断孙的,砍血脖子的,五马分尸的,有娘养了无娘指教的……若有人来劝,她就恶狠狠地说,老娘就是要骂,叫他把吃下去的东西都吐出来!
小广播的这张嘴,严重影响了她儿子找媳妇。儿子二十五岁了,多次说媒提亲都黄了。虽然个子小,其实小伙子也还算英俊,眉清目秀的,人也能干,跟她恰恰相反,儿子的话特别的少,三锤打不出半个屁。有人说,凡事都讲个平衡,儿子之所以三锤打不出半个屁,是因为小广播把儿子一生的话都讲完了。提亲相亲的人家还来不及了解儿子的能干,一听是小广播的儿子,就望而生畏望风而逃了。
小广播不只是她话多,不只是她骂人厉害,还极其吝啬,不近情理,不讲人情世故。请媒人说亲,俗话说:成不成,酒三瓶。但小广播心疼礼钱,只是趁着村里办红事或者白事的机会,在人群里串,求人家给她儿子做媒。人家表面上答应她,实际却一点也不上心,有的还对她这种没诚意的做法不满,反倒悄悄给女方家说一些坏话。
有好心人对小广播说,你要请媒人,还是不要在人群中去遇了,你就买点东西亲自上人家的门,诚心诚意地请人家,这样才有希望!
小广播嘴上说要得要得,其实她哪舍得买东西去上人家的门。
她儿子外出打工,终于被同乡不同村的一个姑娘看上了。姑娘才十六岁,俩人在一个工地上干活,一来二去就好上了。过年的时候,姑娘先跟着儿子回来看看家境。
小广播大喜过望。这个姑娘高个子,鸭蛋脸,牙齿白白的,看上去很不错,身体也健壮。小广播知道自己的毛病,这次她尽量闭嘴,声音也降低了八度:二喜,你去街上割一块肉来,要瘦的,肥的翠翠不爱吃……二喜,你爹怎么还不回来呢,天都麻沙沙的了……
姑娘回自己家里去了,小广播就跟儿子和丈夫商量,要尽快给儿子和姑娘把婚事办了。她怕夜长梦多,好端端的一个姑娘又飞了。
小广播这次狠了心,买了三瓶金六福酒和两封月中桂绿豆糕,请了王三娘做媒人。媒人得了好处,也尽了力。姑娘的爹妈也过来看了情况。最后提出,要一万六千八百元的彩礼,六只火腿,一千六百八十斤大米,礼到了就把女儿嫁过来。
小广播一听,晕了三分钟,醒来后就泪流满面。这么多钱和这么多东西,她怎么不心疼,但是一咬牙,双手往脸上一抹,把泪水往地上一甩,就笑了。毕竟儿子有媳妇了。
接着就算开了账,儿子打工存了一万,她在家养母猪下猪仔又卖了五千,再借点终于凑够了一万六千八百元。大米家里倒有现成的,圈里还喂着三头肥猪,小广播五马调六羊的,卖了两个猪,留一个办酒席,将卖两个猪的钱买了六只火腿,剩下的四千元添着办酒席。
送钱送米送火腿到姑娘家的时候,出问题了。
十七个雪白的尿素口袋装满了大米。在农村,这些口袋可有用了,装这装那都要用。有时要上街也带着,要买点什么或者卖点什么都拿它装,小广播笑着对姑娘的爹说,米腾在哪儿?这口袋我还得带回去。姑娘的爹不高兴了,觉得小广播在为难他,就高声说,不用腾了,你都带回去吧,我家要不起!小广播连忙赔笑脸,用手在自己的脸上啪啪地打了两下,连说,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这张屁股嘴,不会说话,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原谅了我们吧!
姑娘的爹的脸色才变了过来。小广播双手递过钱去,说,亲家,你要好好数一下,一万六千八百元,一分不少。姑娘的爹接过钱,放在茶几上。小广播急了,说,亲家,还是好好数一下,当面不数,过后不认。俗话说,爹亲娘亲,赶不上钱亲,你还是好好数一下吧!
姑娘的爹抓起钱就向小广播的脸砸过去!拿着滚回去!我家的姑娘不嫁人了!
小广播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不知道怎么就得罪了姑娘的爹。她啪地跪在地上,一个劲地用巴掌打自己的脸。边打边说,你这屁股嘴,叫你乱说!叫你乱说!亲家,你就原谅我吧!都怪我空长百岁,不会说话,不会做人。
直到小广播嘴唇流淌出了鲜血,姑娘的爹才让小广播站起来。
儿子结婚那天,小广播穿上了压在箱底起了折子、有了怪味的新衣裳,满脸都是高兴。她估计连上亲戚和村邻,至少也有十五桌。至于朋友,小广播头脑里是没有这个概念的。通过村里的几个厨子,一头四百多斤活生生的猪,变成了酥肉、墩子、排骨、肉片、肉丸子……尽管小广播的吝啬出了名,但唯一的儿子终于娶媳妇了,她得忍住心疼。即便疼,也疼在心里。
村里的一个小伙子帮忙去买十五只鸡,连蛇皮口袋共九十二斤八两,拿回来小广播一称,就只有九十二斤。小广播像牙疼一样笑着对小伙子说,怎么就少八两了呢?十一块钱一斤,八两,就是八块八角钱,够买好几斤米了呢!小伙子不高兴,说,我亲自看着他称的,秤杆还翘得老高的呢!怎么少了八两我咋知道呢?鸡又是好好的,难道我会割一块肉藏起来?这时一个厨子看不过,就说,别说少八两,就是少一两斤,都是正常的,都半天了,鸡不会屙屎吗?一个鸡屙掉一两屎,十五个鸡就屙了一斤半,这才少八两呢!小广播看了一眼厨子,有些不满,但又不敢得罪。就皮笑肉不笑地说,就是屙屎,也屙在口袋里,我是连口袋称的。另一个厨子说,有些鸡屙的是稀屎,老半天了,难道稀屎里的水分不会蒸发掉?蒸发掉了,你又怎么能称得出来呢?兴许那八两,就是稀屎里蒸发掉的水分。
又一个村邻笑着说,还有,鸡是在院坝里自由自在地捉虫子吃,你把它装在口袋里,它知道活到尽头了,又闷又气,气瘦掉几两也是可能的嘛。大家就哈哈大笑,说,是呢是呢!
小广播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一块老脸上挤出几丝笑容,说,是呢是呢!我只是说说,只是说说。买鸡的小伙子吐了一口痰,一转身走了,后来饭都没来吃。
几个厨子在酥肉,每酥一锅,都会夹一点在嘴巴里,尝咸尝淡、尝生尝熟。小广播看着厨子嚼吃东西的嘴巴,心很疼,但又不好直说,就时不时看一眼厨子,眼神里满是不愉快。厨子看在眼里,也不收敛,反而对旁边帮忙的人说,你们尝尝,你们尝尝啊!看看我们的手艺咋样?大家就尝,都说,不错不错,比城里的厨子手艺还高呢!
小广播没听到人们说什么,只是看着这些人动不动就吃肉,心疼。在心里安慰自己:这么大的喜事,人家吃点肉算得了什么?再说,这会儿多吃些,到吃饭的时候不就要少吃一些吗?还不是一样的呢!早吃晚吃,都是那个肚子。
几个大火塘的火,燃得红花绿焰的,有的火塘上煮着菜,有的煨着水,有一个火塘上,什么都没有,由于天气冷,一些帮忙的人围着烤火。小广播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心想,浪费呀!少烧一个火塘不是也可以吗?更让她觉得浪费的是,火还燃得旺,厨子就要用火钩往下面掏,红艳艳的炭块滚落在地上,刺得小广播的眼睛生疼。她拿着一铁铲子,把那些炭块撮起来,到离火塘不远的地方,用一个小铁锤慢慢敲,把表面燃烧过的灰烬敲落,剩下未燃尽的炭放在一只锈迹斑斑的铁桶里。冷风打着漩涡,把她敲起来的白灰扬起来,落在锅上,落在饭菜上,落在人们的头上。一个年纪大一些的厨子看不下去,就说,小广播,你等事情过了再慢慢敲不行吗?还怕哪个回来跟你争?你看,饭菜上都是灰,不想给客人吃啦?
小广播笑着说,要得要得,我是说趁现在得闲,敲一敲,以后农活来了,忙不赢呢!我就拿远点敲,拿远点敲啊!小广播就到房子后面去敲,北风像刀子一样割,但小广播还是流着清鼻涕一个劲地敲。
十八个菜摆满了桌子,每碗菜都舀得很满,像小山一样,尖尖的,一桌吃完了,只把尖尖的小山顶吃平。然后又把这些菜分类返回锅里,下一桌再舀出来。小广播用一个盆端着一些米饭,把饭倒在每一个装过菜的盘子和碗里煸一下。一边煸,一边说,可惜了,油噜噜的,事情过了慢慢热了吃。
小广播的丈夫饿得受不住了,就跟着客人一桌子吃饭。小广播把瘦小的丈夫揪起来,拉到门背后,压低声音恶狠狠地说,你这不懂事的老五保户,剩菜剩饭那么多,你还去吃新鲜的。你不会等着客人走了,我们热剩菜剩饭吃?油噜噜的,害怕填不饱你的狗肚子?
有几个吃了饭的客人悄悄说,酥肉是煳的,肉片太咸,排骨简直啃不动。几个厨子在火塘旁有说有笑,眼神和笑声都显得意味深长。
小广播计划的是十五桌,可到最后只有六桌。准备的菜除了鸡是十五只,鱼是十五条,别的菜都至少够三十桌人吃。
小广播看着锅里、盆里堆成小山一样的剩菜,唠叨着:这么多剩菜,怕到明年二三月间都吃不完,还要放得住才行。
有人说,天冷,放得住的。
也有人说,哟,怪了,这么冷的天,怎么排骨和肉墩都有些臭了?
小广播一尝,果然有了臭味。
一个厨子说,哎呀,搞忘了,这些做熟的菜,不应该放在火塘旁烘着,都是烘出问题来的!
小广播眼里就有泪水了。她恶狠狠地吃了两块有臭味的肉,压低声音恨恨地说,再臭,也是肉!我也要把它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