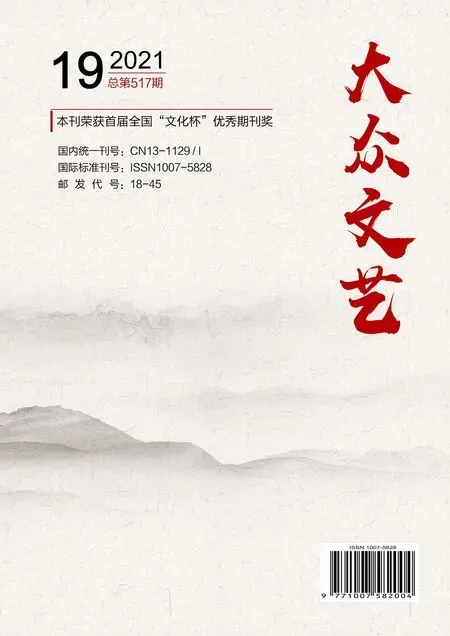初探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杂文创作的转变
(延安大学文学院 716000)
五四运动以后,文人们开始将改造人们灵魂的文种瞄向了杂文,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作家,通过杂文的创作,以图改变国民的内心,并指出,杂文是“匕首和标枪,要锋利而切实”,是“和读者一同杀出生存血路的东西”。杂文的创作爆膨,是“五四”运动以后文学创作出现的一种现象。延安时期的杂文创作延续了“五四”以来杂文的一般特性。
3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的动荡与民族矛盾的加深,中国开始滑向战争泥潭,目睹了当时的困境与国共两党在处置相关问题的做法,大批作家为了理想信念,经过选择奔赴延安。这些“文化人”的到来,丰富了延安的革命生活。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作家们也重新开始进行思考与创作。
杂文的创作离不开时代背景,来延安的作家们自然而然不会丢弃他们手中的短剑。延安虽然平静光明,但从全国来的作家们却从未从悲怆中走出,他们目睹过沦陷区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比原本生活在根据地的人们更富有革命热情、战斗激情。因此根据地的作家拿出手中的笔充当战斗工具,以笔为枪进行创作。而其中最富表现力的文种,当属具有战斗精神的杂文。
从整个延安时期的杂文创作历程来看,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抗战的全面爆发到1942年5月
这一时期的杂文,首先是身处延安的作家对时局的审视,对时弊的针砭。延安的知识分子,在解放区革命根据地进行文学创作,享受着在国统区与沦陷区范围内享受不到的自由,高度的创作自由,杂文文风的犀利,符合了时代主题与战斗精神的需求,丁玲在其主编的《文艺月报》1941年1月创刊号上,曾经写过《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一文,通过文艺专刊,向文学精英传达了一种自由开阔的创作之风,希望作家能积极创作、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将自己的想法与观点大胆的表达出来。如田家英的《从侯方域说起》评说讽刺国民党统治的跋扈专制;《科举与选举》则揭露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封建官僚一转身,继续充当统治者的残酷性;周扬的《文学与生活漫谈》是通过自身的感受,号召文艺工作者走出身边的小圈子,积极地融入到群众的生活,将创作与群众生活的实际能够紧密联系起来。
1942年之前的杂文大致可分为“讨外”“视内”两类,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杂文,对延安外部存在的现实提出批评讽刺,同时对革命队伍本身给予重视与意见。当时延安作家们的作品涉及方方面面,以不同于“五四”时期的激昂文风的杂文,以朴素、平实但不失智慧的语言,初步形成了延安时期杂文创作的独特文风。
1942年是延安时期杂文创作的分水岭,其一,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文章,号召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在尊重现实、尊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大胆言论,正确的错误的都表达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作家的杂文创作。其二,根据当时的抗战形式,抗战已经到了最艰难的相持阶段,文艺工作者大都来自大城市,物质上、思想上的双重困境,让他们有了更迫切需要表达的切入口。
以此为界,在1942年初,影响延安时期杂文创作的数篇文章登上了报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全部出自1942年的春天,这些文章通过作家的实地见闻,自身对革命事业的美好愿望,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当时解放区在日常工作、思想认识上的弊病,引起了社会上的各方关注,表现出了杂文应有的“揭露黑暗”的特征。
这几篇杂文的发表,是整个延安时期文艺界的大事件,首先,先前的杂文,内容表现出对旧制度的批判与国统区的不足,涉及到解放区的杂文多为号召、建议性质的,而这一系列杂文的发表,则是直指知识分子眼中的“光明中的污点”。“大胆地但过当的揭破一切黑暗与肮脏,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等重要”。其次,杂文的发表带给众多在延安的知识分子青年相当的共鸣,产生了比杂文本身内容更深层次的影响。第三,这些文章的发表触及到了革命者自身,引起了政治上的相关反应。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夕,延安各界在毛泽东在《讲话》中所作出的相关指示中,对这些杂文的作者进行了审视、批判,尤其以王实味为代表,以致后来,原本一同与王实味揭露黑暗的作家,如丁玲、艾青开始倒戈、为求自保,转而批判王实味,到最后王实味自身不能坚持,在《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一文中,王实味的话语开始不再一味的追求自己所坚持的观点,不再是硬着骨头有话就和上司说的王实味,丁玲在此时为了脱离干系,将自己的《三八节有感》单独列出,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放在一起,进行批判与自我批判。
联系到在延安各地的文艺家、作家、知识分子,毛泽东根据许久积压出来的创作中的问题,众多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的邀请下,各聚一堂,在1942年5月,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中国近代以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一方面,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的讲话,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文学创作的经验与教训。另一方面,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对中国整个文艺创作的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有的文艺观点至今仍对文艺界有重要影响,是中国文艺创作的根本方针。会议统一了思想,“要求文艺工作不能脱离群众”,要求“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群众中去”,要求“文艺要服从于政治,文艺是服从党在一定时期内规定的革命任务”。
杂文的创作也受到了此次会议的影响。王实味等人发表的几篇杂文,可以看成是延安整风运动需要被树立的反面典型,是党的高层为统一作家思想所需要斗争的目标。
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杂文创作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与之前相比,发生了巨大的扭转与变化。
首先,王实味因文生罪很大程度上对解放区作家的创作心理起到了抑制作用,很多青年作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响应了号召,走向了前线。丁玲更是在文艺座谈会后,在杂文的创作中长时间封笔,相当的作家对杂文的创作讳莫如深。
其次,在杂文创作“揭露黑暗”与“歌颂光明”的论辨过程中,“歌颂光明”成为主基调,毛泽东在对丁玲的谈话中说到,“要进行批评,先得肯定人家的好处,说他怎样艰苦,怎样打胜仗,怎样有功劳;说我们的党是了不起的、伟大的、光荣的。然后再说我们还有一些缺点……”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文艺需要服务政治,因此,揭露黑暗的这一题材渐渐的淡出了解放区的杂文创作体系。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几乎再没有出现《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谈对解放区存在问题的直接揭露的杂文。具有鲁迅风格的短剑一样具有战斗精神并直面问题的杂文,不断地在解放区被边缘化。
再次,战争形势的转变,1942年之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外部现实的变化让杂文创作的选择与内容上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杂文的内容再次转向根据地之外,对时事进行评述,记录事件发生后产生的感想,与先前针对生活、学习、风气、思想上创作的杂文存在着较大的区别。丁玲的《窃国者诛》、默涵的《讽刺与幽默》等文章,是典型的1942年之后的杂文,通过感想、讽刺反动统治来反衬边区的光明。
最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杂文主题虽然已经发生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其中仍有相当部分的杂文具有很高的水准及现实价值。虽然文风不似从前,但仍然在战争年代起到了引导作用。
延安时期作为近代史以来的一个特殊时期,在思想、政治、文艺创作上都有其特殊性,作家的创作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革命的不同主线上,发挥自身改造人类思想的能力,而在作为特殊时期的作家,其另一任务就是创造出能够支撑当时的人们的斗争与生活的精神产品。而杂文这种短促有力的文体可以更直接的与现实对话,也更能适应读者的需要。
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界,延安时期的杂文分成的两个阶段,是有其显的特征,前者保留了一定程度上鲁迅杂文的风范、追求批判。但由于境界及环境背景的限制,现实批判不及鲁迅杂文中文化批判以及思想批判。而座谈会之后的杂文由于政策纲领的制定,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杂文所需描述的范围,使延安时期后期的杂文缺少了一些锐利之风,多了些号召的意味。
杂文作为一种短小精悍的文体,是知识分子进行观点宣扬,思想交流的工具,延安时期的杂文基本上符合了以鲁迅杂文为范式进行批判的标准。延安时期的杂文作为抗战文学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人们的思想。更由于1942年3月,丁玲,王实味的杂文的发表,推动了延安整风运动的高潮,并成为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一个重要诱因。延安时期的杂文创作数量并不多,但重要篇目不少,有数篇杂文成为影响一个时代的航标。
参考文献:
[1]姚春树,袁勇麟.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史[M].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
[2]延安文艺丛书·散文卷[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3]金灿然.论杂文[N].解放日报,1942.7.
[4]丁玲.我们需要杂文[N].解放日报,1941.10.
[5]罗烽.还是杂文时代[N].解放日报,19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