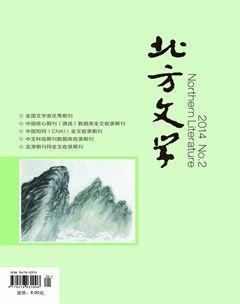“安全感”的缺失和寻找
汪静
摘 要:对“安全感”的需求是人类的本能,从白先勇的作品可以看出,“安全感”并不仅仅来自一个具体的“家”,而是一种鲜明的情绪、情感诉求。论文主要以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孽子》为中心,探究白先勇笔下人物“不安全感”的表现,并对他们产生人生“不安全感”的原因加以分析。
关键词:白先勇; 安全感; 家; 《孽子》
白先勇是华文文坛一位极受重视的文学家。迄今为止,他旅居海外已40多年。如今,高龄的白先勇频频往返于大陆、台湾和世界各地,特别是近些年白先勇多次受邀访问他的出生地桂林。许多媒体对于白先勇的桂林之行,纷纷下大标题称其为“回家之旅”。然而,对白先勇来说,“家”究竟在哪?
白先勇是前国民党将军白崇禧的第五个儿子,1937年出生。那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岁月,可以说是生于忧患。白先勇7岁时,经医师诊断患有肺结核,不能就学,因此他的童年时间多半独自度过。抗日战争时他与家人到过重庆。日本投降后,白先勇迁至上海和南京,小学就读于南洋模范小学。1948年白先勇又迁居香港,就读九龙塘小学及喇沙书院。随着国共内战的失败,白先勇又于1952年移居台湾。由于白先勇曾梦想参与兴建三峡大坝工程,于是,在1956年建国中学毕业后,他以第一志愿考取台湾省立成功大学(今国立成功大学)水利工程学系。翌年发现兴趣不合,乃转学国立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改读英国文学。1965年,白先勇在美国取得艺术创作硕士学位后,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从此在那里定居。
从白先勇青少年时代辗转流离的人生来看,对于大多数人所认为的“家”的安全感,他似乎很难拥有。也许正是如此,白先勇缺乏对一个具体的“家”的确定认同感。在1967年接受《幼狮文艺》的采访中,白先勇就被问到关于“家”的话题。他回应说:“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记忆的总和,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想得厉害。”[1]可见,白先勇所谓的“家”,也许不是任何具体的地理所在,也许是一个能给他身体和心灵“安全感”的所在,或者是文化,或者是生命感觉。
可以说,对于“家”的渴望、对“安全感”的需求是人类的本能,白先勇也不例外。因此,白先勇的文学创作也可以理解为他对生命某种“渴望”的延伸——对“安全感”的渴求。通观白先勇小说,可以发现这是他小说一种鲜明的情绪、情感诉求。这种对“安全感”的渴求,在他作品的人物世界中不乏线索。例如,《台北人》中那些“身”在台湾却一心沉溺于过去(大陆)辉煌的老兵、舞女、将军;《纽约客》里拒绝融入异国文化的大学教授、风华绝代的留学生;《孽子》中挣扎在社会边缘的同性恋者。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生中,不难发现,他们所认同的有“安全感”的世界,有的存在于过去,有的存在于难以抵达的空间,有的存在于社会伦理无法认同的未知处。但他们都缺乏“安全感”,因为“缺乏”,所以“寻找”。白先勇作品中那些寻找“安全感”的人们,有的成功了,有的妥协了,有的被这个不安的世界吞没了。
本文主要以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孽子》为中心,探究白先勇笔下人物“不安全感”的表现,并对他们产生人生“不安全感”的原因加以分析。
一、成为少数人的恐慌
传播学中有这样一个理论——沉默的螺旋,即人类社会的凝聚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值观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就会形成舆论。舆论在政治事务和其他许多问题上对普通社会成员构成心理压力,进而影响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行为。而选择与处于优势的舆论不同的立场和行为方式,将可能导致个人在社会中被孤立、被排斥。因此,如果人们认为自己的观点与大多数人的观点一致,他们一般会自信地表达这些观点;然而,如果人们觉得自己的观点只与少数人类似、相同,那么他们将会谨慎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沉默。在这个过程中,强势观点被不断强化,弱势观点不断失去话语权[2]。在白先勇许多关于“同性恋”主题的文学作品中,“同性恋者”就是这样一群被主流社会孤立、排斥而无法拥有话语权的社会边缘人。
在《孽子》中,阿青因为和主流社会不同的性倾向,而被迫离家出走。在“同性恋”生活方式无法得到认同的主流社会里,他不仅不容于学校,而且不容于家庭亲人之间,人生倍感孤独。阿青只得和一批同样无家可归的同性恋青年,流浪到台北新公园,建筑了他们自己的小王国。在他们原来的生活轨迹中,突然有一天他们认识了真实的自己——他们将是不容于正常社会的“异类”。但他们依旧渴望有人诉说、有人理解、有人关爱。但是生活没有给予他们认同,他们被放逐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在那团昏红的月亮引照下,我们如同一群梦游症的患者,一个踏着一个影子,开始狂热地追逐,绕着那个莲花池,无休无止,轮回下去,追逐我们那个巨大无比充满了爱与欲的梦魇。”[3]这些彷徨、沉默的灵魂,只能带着这种无法同亲人分享的伤痛挣扎在社会的边缘。白先勇在1986年《人间》杂志中发表了《写给阿青的一封信》,文中对于这种痛苦有十分贴切的描述:
那一刻你突然面对了真正的自己,发觉你原来背负着与大多数人不同的命运;那一刻你可能会感到你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那突如其来的彷徨无主,那莫名的恐惧与忧伤,恐怕不是你那青涩的十七八岁年纪所能负荷及理解的[4]。
这份压在这些青年心上沉重的负担,就是他们孤独、漂泊感的来源。他们比任何人都需要有一个港湾,让他们停止漂泊。而新公园就是作者构建的一个属于他们的王国。在那里,他们都是同类,就如《孽子》中所述,“在我们这个王国里,我们没有尊卑、没有贵贱,不分老少、不分强弱。我们共有的,是一具具让欲望焚炼得痛不可当的躯体,一颗颗寂寞得发疯发狂的心。”[5]于是他们惺惺相惜,互相理解、关怀。对于这些青年来说,台北新公园就是能给他们心灵“安全感”的所在,一个近乎于“家”的存在,他们暂时地在这里获得了些许人生安慰。但是,新公园并非真正安稳的所在,它仅仅是虚构了一个“家”的外壳,它时刻都处于主流社会的窥视、破坏之中。
二、家庭亲情的缺乏
白先勇将自己唯一的长篇小说命名为《孽子》,正是有意识地以“家庭”关系的构筑去表达作家心中的隐痛:“孽子”意味着子女们对家庭伦理的颠覆,意味着一种正常家庭伦理的缺失。小说中,大多数的同性恋者都是被父母放逐的子女,在身体和心灵上总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漂泊感。因此,他们对感情的追寻中,总难免会不自觉地想找回那份家庭亲情。
阿青对于一些比他年幼的孩子特别温柔照顾,那是因为从他们身上能找到与早夭的弟弟的手足之情。在《孽子》中提到的赵英,他吹口琴的样子让阿青想起他的弟弟,进而对赵英产生了一种变异的爱。“我的双手从他背后围到他前面,紧紧地箍住了他的身体。我的面颊抵住了他的颈背。我的双臂使尽了力气,箍得自己的膀子都发疼了”。[6]另一方面,阿青对一些中年男人特别仰慕,很大程度上是想求得自己父亲不能给予的谅解和关怀,这在他与王夔龙的交往中得到很好的体现。王夔龙同样是不被父亲谅解的“孽子”,甚至连父亲的葬礼都无法参与。他遇到阿青便像遇到年轻的自己,而阿青在听夔龙讲述他与父亲的往事时,也找到了互诉衷肠的人。“常常在午夜,在幽冥中,在一间隐蔽的旅栈阁楼,一铺破旧的床上,我们赤裸着身子,两个互相隐瞒着姓名的陌生人,肩并肩躺卧在一起,陡然间,一阵告悔的冲动,我们会把心底最隐秘最不可告人的事情,互相吐露出来。我们看不清彼此的面目,不知道对方的来历,我们会暂时忘却了羞耻顾忌,将我们那颗赤裸裸的心挖出来,捧在手上互相观看片刻。”[7]他们心中有相同的伤痛,他们对对方的依恋,是因为能在对方眼中看到自己,能完全坦诚地释放自己,从彼此的隐痛中找到安放自身的安全港湾。
endprint
小玉是小说里一个八面玲珑、讨人喜欢的角色。小玉出身坎坷,他从小听母亲告诉他父亲是一个日本人,当年来台湾做生意时认识小玉母亲。小玉母亲怀孕,小玉父亲回到日本,从此断了音讯。母亲多年寻找未果,于是母亲的“寻夫”夙愿就成为小玉的生活动力。“寻父”是支撑他生活的唯一终极目标,尽管屡遭挫折,但对父亲的爱、恨交织的浓烈情感让他不屈不挠地继续着“寻父”之路。甚至最后小玉为此私渡到日本——即使知道这似海底捞针:“找完了新宿的中岛正雄(小玉生父姓名),就找浅草、涩谷、上野,一直找下去。东京找完了,等我攒了点钱,便到横滨、大阪、名古屋去。我要找遍日本每一寸土地,如果果然像傅老爷子说的,上天可怜我,总有一天,我会把我老爸逮住。”[8]而在小说中,小玉一个为人诟病的重要行为是“乱拜干爹”,在不同男人之间周旋。这看似堕落的行为,其实背后隐含着对“父爱”的寻找意味,是一个从小被边缘化的“孽子”对“安全感”的一种变态寻求。
吴敏对张先生无可奈何的痴恋,实质上是对张先生所能给他的那个“家”的无限珍惜。从小到处漂泊、担惊受怕的生活,让他极度缺乏“安全感”,迫切想要有个“家”安放身体和心灵。在张先生家里,他小心翼翼,生怕犯错被赶出去。“搬进张先生家后,我以为总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所以特别小心,半点错也不敢犯”[9]。因此,在张先生抛弃他的时候,他绝望地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吴敏在自杀被救后对阿青说,“阿青,你知道,我在张先生家也住了一年多了。总是规规矩矩守在家里,一次都没有自己出来野过。张先生的脾气不好,可我总是顺从他的。他爱干净,我天天都拼命擦地板。起初我不会烧菜,常挨骂。后来看食谱,看会了,张先生有次笑着对我说:‘小吴,你的豆瓣鲤鱼跟峨眉的差不多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以为张先生心里很喜欢呢。哪晓得他那天无缘无故发了一顿脾气,便叫我马上搬走,多一天都不许留。我没想到张先生竟是一个那样没有情义的人。”[10]他为了保全那个能收容他的“家”,极尽自己所能讨好张先生,甚至在自杀被救后仍担心张先生是否消气:“阿青,你那天到底见着张先生没有?他还在生气么?”尽管自己被如此对待,他依旧对那个所谓的“家”无比眷恋。因此在张先生半身不遂需要人照顾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回去照顾他。因为对他而言,他又可以暂时地有一个“家”了。
可以说,“家”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家人是唯一能无条件包容自己的人。而这一群被放逐的孩子原本拥有的亲情却缺失了。他们恐惧、彷徨,更加需要家庭的温暖。但是,对他们而言,“家”虽在,“回家”的路又在哪里呢?这些被正常的家庭伦理和社会轨道驱逐出来的“青春鸟”,只能用别的方式作为亲情的“替代品”,以此找到一些所谓的“家”的“安全感”。因此,小玉、阿青、吴敏他们不合“常理”的行为,其实都可以从人类的“常情”中获得解释。
三、同性关系的不稳定性
王夔龙和阿凤的“爱情”是台北新公园一段广为流传的“传奇”。他们“如同天雷勾动地火,一发不可收拾”的爱情,开始热烈,但激情过后,阿凤却开始逃离龙子为他布置的“家”。“我要离开他了,我再不离开他,我要活活地给他烧死了。我问他,你到底要我什么?他说,我要你那颗心。我说我生下来就没有那颗东西。”[11]龙子和阿凤这一段惊天动地的“爱情”以悲剧收场,表明了同性恋者之间“爱情”的不稳定性。这类同性相爱的悲剧,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如在情人结婚那天跳河自杀的桃太郎、苦等美国情人而精神失常的涂小福等。
可以说,同性恋者之间“爱情”的不稳定性是小说人物难有“安全感”的重要原因。对于这一点,其实作家是有所认知的。在《写给阿青的一封信》中,白先勇对这种不稳定性的缘由进行了阐述:
异性情侣,有社会的支持、家庭的鼓励、法律的保障,他们结成夫妻后,生儿育女、建立家园,白头偕老的机会当然大得多——即使如此,天下怨偶还比比皆是,加州的离婚率竟达百分之五十。而同性情侣一无所恃,互相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彼此的一颗心,而人心唯危,瞬息万变,一辈子长相厮守,要经过多大的考验及修为,才能参成正果。[12]
同性情侣,没有法律的保障,没有社会的认可,得不到家人的祝福,甚至不可能建立稳定的家庭。可以说,这样的关系是脆弱、不堪一击的。因此对于同性恋者,在恋情中的摇摆、不安,似乎成了同性恋者“爱情”关系的常态。这正是造成《孽子》小说人物“不安全感”的重要原因。
四、“家”的设置和“安全感”的渴望
《孽子》全文基调比较压抑,但从一些细节处不难发现作者仍抱有积极的态度。比如全文后半段作者安排了傅老爷子这个角色。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他引以为豪的儿子被他发现是同性恋者之后,傅老爷子无法原谅儿子。得不到父亲谅解的儿子傅卫,用手枪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傅老爷子悲痛万分。这个事件在日后激发了傅老爷子广大的悲悯之情。在得知阿凤横死后,那份对儿子的救赎激发了他对新公园这些同性恋少年的关怀。他变卖了自己的家产,救济这些与自己儿子相同命运的孩子,成了他们的救星。这是傅老爷子认定的为亡子弥补父爱的方式。傅老爷子同时也成为这些被放逐的心灵一个找到“安全感”的“家”。《孽子》中描述傅老爷子对于这些“孽子”,完全出于一片爱心,“默默行善,本人甚少出面,所以我们圈子里只听闻有这样一位活菩萨。”“孽子”们闹事被警察拘捕后,傅老爷子“老着脸,把一个多年没有来往的老同僚抬出来”[13],才把他们具保出来。“孽子”们在事后拜访傅老爷子,傅老爷子“询问我们各人的姓名、年岁以及生活起居,每个人都问得相当详细,师傅一一作答时,傅老爷子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却一直瞅着我们,佝着背不住的点头。”[14]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俨然把这些孩子视如己出。
小说中傅老爷子和孽子们之间的“父子”亲情,这种超越传统认知的“家”的关系设置,显示了孽子们对“安全感”的无比渴望,也正表达了白先勇对这些社会边缘人命运的关怀和祝愿。
结语:《孽子》是白先勇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这个作品中所体现的社会边缘人物的挣扎、彷徨,在他的很多作品中也有体现。笔者认为,《孽子》中形形色色的角色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寻找“家”的“安全感”。这个“家”也许不仅仅是社会学对它的通常定义,不是一个确切的地方。它也许只是一种生命的感觉,是一个能给他们“安全感”的所在。可以说,白先勇小说对人物“不安全感”的反复书写,是白先勇本人生命境遇的反映,更深刻体现了作家对人类生命本身的悲悯和关怀。
注释:
[1] 林怀民:《白先勇回家》,《幼狮文艺》,1967年。
[2] 李苓等编著:《大众传播学通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7-268页。
[3] 白先勇:《孽子》,桂林:广西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4] 白先勇:《给阿青的一封信》,《人间》1986年第7期。
[5] 白先勇:《孽子》,桂林:广西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6] 白先勇:《孽子》,桂林:广西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
[7] 白先勇:《孽子》,桂林:广西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8] 白先勇:《孽子》,桂林:广西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23页。
[9] 白先勇:《孽子》,桂林:广西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0页。
[10] 白先勇:《孽子》,桂林:广西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11] 白先勇:《孽子》,桂林:广西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115页。
[12] 白先勇:《给阿青的一封信》,《人间》1986年第7期。
[13] 白先勇:《孽子》,桂林:广西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0页。
[14] 白先勇:《孽子》,桂林:广西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