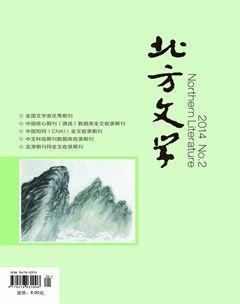从传统诗歌到大众音乐
张莹
摘 要:从古至今,文学与音乐作为两个独立的艺术门类一直在相互影响着,从吟游诗人口中的口传诗歌,到消费主义下的市场传播,文学与音乐一直面临着相似的处境。本文截取音乐与文学发展历史上的三个时间段,具体分析当它们去掉自身信息流通与文明传承的属性之后,我们如何面对与欣赏它们。
关键词:口传文学;民歌运动;消费主义;多元化
一.口传诗歌的新生——个人化表达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诞生于人类文明之初。在文字诞生前,口传文学曾经是承载人类文明与发展的唯一途径。然而,口口相传的原始叙事是不稳定也不牢靠的,在其传播过程中,会不断地丢失原有信息,并被编入新的含义,这也就成了隐喻的最初来源。为了弥补口传信息的不足,也为了挽救集体记忆,人类从原始的语言中发掘出其音韵特质,创造韵文以便记忆,而这也就是诗歌这一最为古老的文学形式的原型。
维柯曾在《新科学》中写道:“各原始民族用英雄诗律来说话,这也是自然本性的必然结果。这里我们也应赞赏天意安排,在共同的书写文字还未发明以前,就安排好各族人民用诗律来说话,使他们的记忆借音步和节奏的帮助能较容易地把他们的家族和城市的历史保存下来。”[1]如此一来,我们可以认为早期的人类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建立于诗歌文学之上的,诗歌在那时便相当于我们今日所说的文化,囊括了基本上所有的人类知识与存在方式。而在上古时期,韵文的存在及传播方式往往并非单一,枯燥的讲述,它通常与音乐、舞蹈相结合,例如《诗经》中重章叠句的程式化技法,以及六首有目无辞的笙诗存在。文学与音乐在当时便是一体而两面的,而其结合生成的口传文学则在内容上同时具备了现实性与抒情性,表现手法上也兼有音韵和谐的形式美和自由的个性化表达。
文字发明以后,人类有了新的记录与传播媒介,但受限于生产力的落后,口传文学仍在相当一部分时间里承担文化火种的功能,它们那原始艺术混沌的美感,融合音乐、文学、表演于一体。可在近代以来,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口传文学已越来越不受到重视,口传文学的社会功能逐渐被拆解的七零八落,而现代诗歌则逐渐剥离了音乐性,音韵美这一概念似乎也变成了空壳子,只在评论家们的笔下闪烁着苍白的微光。
然而,只要人类还活着,他们就必须要说话,每个人都渴望被听见,也因此每个人都是诗人。这是我们基本的能力,也是我们基本的需要,当口传诗歌不再承担记叙历史这一责任的时候,古老的传统便在它身上死去了。可这并不是结束,反而是一次辉煌新生的开始,诗歌通过死亡回归到了它的根本——个人化表达。
二.音乐与文学的再次结合——纯审美文本的衰落
音乐与歌曲相比,音乐更接近于一种概念,而歌曲则是这种概念投射的具体表达。由此来看,音乐与文学是歌曲共同的“立法”,而歌曲则是音乐与文学共同结构下的文本,这两者的关系正像语言和言语,二元对立又不可区分。
而诗歌,或者扩大范围至整个文学,在现代性语境下也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与变革。虽然在物理层面上,人类正前所未有得接近彼此。可同时出现的还有另一个问题,即文化与族群的问题,彼此接近的距离带来了文化族群间广泛的交流,而这交流也同时蕴含着文化场间的交换,冲突,合作。人类正在以数年的时间完成以往千年方可完成的工作,在这过程中,国家政权——各文化场——个人三者间形成了相互蕴含与冲突的关系范式,当摆在人们面前的母题从命运,爱情转向无数截然不同的民族,宗教与国家时,纯审美文本的时代就结束了。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在个人化表达兴起的最初,文本与音乐是相互区隔的,虽然诗歌还保留着韵文的形式特点,可其流传方式却早已被文字统治,个人化的表达虽然已在现代主义的萌发中逐渐被世界接受,可话语却依然在少数诗人的手中。个人化是要让每个人成为自己的上帝,让所有人都能发出声音,它天生便蕴含着自由的精神,如果诗歌仅仅被少数人所掌握,那自由表达变成了个笑话,也正因此,另一条道路出现了,这便是民歌的道路。
近代意义上的民歌应该是始于美国的布鲁斯,即使后来在各个国家有了各种不同的演变,如爵士,摇滚等,但从它们身上依然能看到布鲁斯的影子,而现代歌曲的抒情性大于叙事性,一方面是因为受制于传播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布鲁斯本身的特质所决定的。初期的布鲁斯传播非常狭窄,基本局限于口耳相传,直到“铅肚”(胡迪•莱德贝特),杰西•弗勒,鲍勃•迪伦乃至于帕蒂•史密斯等“音乐诗人”的出现,布鲁斯这一音乐形式才产生了一系列分化,并在世界范围内演化出了整个现代流行音乐的基本轮廓。
时至今日,当年的那批“歌者”,如今也都成为了各个音乐流派的“开山宗师”。而受到他们影响,或者说与他们共同成长的现代及后现代文学,也早已取代了曾经辉煌的古典主义文学,“垮掉的一派”更是作为那整个时代的象征被列为世界文化演进史的一部分,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伯格,这些名字和他们所代表的诗歌只要是对世界文学稍有了解的人们便绝不陌生。而在距离他们遥远的大洋彼岸,当西方反抗的精神已被商品世界异化为庞大体制的一部分时,台湾的音乐诗人正刚刚喊出“我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歌!”
三.音乐与文学的第三次结合——台湾民谣的社会作用
台湾的民歌运动,是以“家”这一意象作为发展线索的,70年代,那是台湾社会最为动荡的年代,彼时的台湾经济刚刚起飞,但从政治环境来说,一系列的外交失败却使得民族主义运动空前激烈,从人民的角度来看,经历过当年战争与逃亡的一辈逐渐从伤痛中走出,并重新反思那场战争的意义以及自身与大陆的情感联系,原住民对新移民的态度也慢慢从抵抗转向温和,而在战后出生并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则面临着另一个最为严重的问题:我究竟是谁。
70年代的台湾还处在戒严之中,年轻人所能听到的声音,除了被当权者一再指责的“靡靡之音”,就是来自西方或日本的歌曲。后来,台湾在越战期间和美国的交好,来自大洋彼岸的抗议民谣及嬉皮士精神才得以在台湾岛播下根苗。
在台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节节败退的背景下,台湾青年对自我身份的探寻中,一直夹杂着恐慌的情绪。1973年,杨弦和他当时的战友们,李双泽,胡德夫等人就开始创作歌曲并举行了很多小型演唱会,可影响却一直有限,直到1975年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杨弦演唱了根据诗人余光中《白玉苦瓜》诗集中作品而创作的民谣——《乡愁四韵》、《民歌》等后,才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对于青年人来说,这也让他们开始反思自身,而反思,正是追寻自我的开始。
而这种情绪和文学的个人化表达是一脉相承的,世界变小了,我们看到的越多便越发想要了解自己,而这也正是杨弦以及当时所有的台湾青年们想要通过对音乐道路的探寻中得到的东西。对自身文化的想象与创造将他们联系起来,和既有的“混血文化”一起深深烙印于他们的表达当中。因为离开,才有认识,而对于台湾的青年,正因为无家,所以他们对于文化的追寻,便是寻根,便是归家。
到了八十年代,民歌已经成为了台湾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这一点上来说,杨弦等人的努力成功了,他们让表达成为了自由的让流淌于自身的文化通过比喻来与众不同,使民族的文化变成拥有活力的我的文化,从而把“我”烙印于文化之上,达成文化与自我个体间的流动,这构成了个人化的另一层意义,即 “我”所表达的,在“我”之前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是“错误”的,而在“我”之后的文化则深深烙印于原有文化当中,并以此达成对自身所属文化的创造与复归。
总体说来,在文学基本依靠文字传播的今天,去掉了传播信息的累赘属性的音乐或许将重新担负起口传文学的角色,在英雄主义之外,重建人类关于美的认识。未来的音乐,文化市场或许将逐渐与国际形势接轨,变得更加地开放化,多元化,而音乐与文学的联手也必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注释:
[1]维柯:《新科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2页。